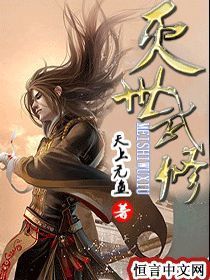展示人物的办法有好几百种,最坏的就是平铺直叙。
——琼·艾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情节产生于人物,还是人物产生于情节?这个问题令大多数作家感到眩晕,小说的基本元素:情节、人物和发展经常扭结在一起,奋力地挣扎着。
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说:“什么是人物,除了对事件的决定之外?什么是事件,除了解释人物?”奥尔德·马斯特在几页之后补充说,“故事与小说,思想与形式,就好比针与线。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裁缝用线不需针,用针不要线。”
完全正确,在你开始之前二者都要存在。但是如果你只有二者之一呢?
总的来说人物是个问题。情节事件俯拾皆是,在报纸上就可每天读到。一位母亲,甚至在多年以后,依然认定她的十几岁的儿子不是自杀。但每当她调查时,就会发生无法解释的死亡2一个芝加哥流氓的宠物卷毛狗被偷;情报局造了一个假的海洋工程工厂努力打捞苏联的潜水艇;一位中年妇女要盛气凌人的丈夫每天写一封情书;波士顿“废糖蜜之害”中21位受害者之一的后代仍在觅求赔偿;魔术师大会在印度某村庄举行,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
上面的事件,都是从每日的出版物中摘抄的,每个事件都可能造就一个故事,当不同的元素相互作用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时,就会让作家产生奇妙、愉快的感觉。当然最好的情节要造就奇特的人物。比如那位跋扈的妻子,逼迫丈夫每天晚上写出一首爱情诗,我们立刻可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那伪装懦弱的丈夫,俯首于专横,每天得去图书馆找新的韵脚和散文。当他反抗的时刻一旦来临,一定会为你提供一个好故事。那位伤心、沮丧的母亲,一直为儿子的死充满焦虑,后来终于查明了真相。讲她的故事很容易。
但如果你有情节而没有人物呢?
再也没有比这更让读者失望的了,有趣而复杂的故事,曲折和离奇的情节,但其中的人物没有生机,没有特色。按部就班的叙述是阅读的障碍,因为它不可能让你记住谁是谁。米兰达是演员还是秘书?谁的车被偷,是哈里斯的,还是彼得的?文森特是强盗还是百万富翁?凯特为什么恨亨利?
在写谋杀案的神秘小说和写诉讼的侦探小说中,人物刻画没那么重要。读者并不想对受害人和嫌疑人了解很深,而侦探则可能有许多众口皆碑的特色,如:他是西班牙人,穿着优雅的灰色丝绸套服,倒着书写感叹号;或他很胖,每看一页书就饮一口啤酒;或她是女的,练过空手道,她有一个巨大的衣橱,但里面的衣服却很破烂。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像老朋友一样地爱他们。
在悬疑小说中尤其会产生人物问题,这可能是真正的障碍。
悬疑小说当然应该适合大众,但是很难给它下定义。它既不是写谋杀的神秘小说,也不是严肃小说,或是间谍小说,但它注定有令人害怕的事情发生。那是给读者的诺言。夏洛特·阿尔莫斯特朗写的《一瓶蓝毒药》是最好的悬疑小说之一,其中根本没有谋杀案,甚至也没有死亡(除了第一章中自然死亡的那个人,引发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它比其他小说更紧张,更吸引人。
在悬疑小说中,人物确实至关重要。男女主角在抗争,不是与有组织的犯罪或国际恐怖主义,而是与个人,冲突是在个体竞争中进行的。这样,主角和他的敌人都不容易作到有血有肉、性格复杂、有张有弛,于是可信度下降。
在《一瓶蓝毒药》中,所有的矛盾都是由主角的妹妹的到来引起的。她是个可怕的人物,总能解释他人的动机,给别人制造不愉快。她让女主角因自我怀疑而变得毫无力量,让男主角彻底走向自我毁灭。接下来,她想了解他是怎样处理那小瓶毒药时,读者便在紧张的气氛中不断期待,可恨的伊特莱尔妹妹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悬疑小说的情节经常发生在封闭世界里。男女主人公必须在某个环境下与对手战斗,而且不能向外界求援,但要有合理的原因。比如有一场暴风雪,电话线被中断,或恶棍因酗酒。吸毒导致失常等等。厄秀拉·古尔蒂斯对描写这些封闭世界很有天赋,她有关于恶棍的大师级作品。她极会制造令人毛骨惊然的家庭悬疑。她有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非常成功。为什么?正是因为她的人物,有了这些人物,思想充满了生气。她的《楼梯》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书中的恶棍、令人讨厌的科拉非常可信,且情节简单。女主角玛德琳嫁给了斯蒂芬,一个她不能容忍并打算离婚的人,一个恐吓过她儿子的残暴的怪物。斯蒂芬摔到楼下跌断了脖子。贫穷的堂妹科拉,一个可怜的亲戚,故意说是玛德琳把丈夫推下了楼。科拉对家务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一切似乎都做到了,可以呆下来过剩下的岁月了。玛德琳身陷困境,因为她认为科拉推了斯蒂芬,但又不敢背叛她,处于无助的地步。对这些情况冷静思考一下,似乎很难下咽。为什么玛德琳当初要嫁给可怕的斯蒂芬,为什么她会屈从于科拉?科拉写得非常逼真,贪婪的心,苛刻的神气,可怕的服饰,对糖果和翻弄报纸的喜爱。她的所说所做能立刻让人完全相信。
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说,他用一种方式检验人物的可靠性,想象他们处在一个与构思中的剧本场景不同的地方,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是否自然。科拉这个角色是真实可信的,不管她是在病房、超级市场或是在墓地。
《楼梯》是厄秀拉的早期小说,她后来写的《被污染的果园》有同样恐怖、幽闭的特点。她令人信服地塑造了邪恶的女主人公的表妹芬,还有帮凶、清扫女工李斯特小姐,这邪恶的一对把女主人公萨拉控制在股掌之中。尤其是丑陋、武断的芬,总是想方设法使可爱、漂亮的表姐成为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芬和李斯特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读者为萨拉的命运而担忧,他们期望在芬采取行动之前,萨拉就能挫败她们的阴谋。她们会对萨拉做些什么已显得无关紧要,女主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读者急于想知道的是,萨拉将如何战胜她们。芬是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怪物,才思敏捷,厚颜无耻。恐怖是悬疑小说必要的成分,只有让读者彻底同情主人公,充分地相信恶棍无所不能,恐怖才能达到效果。
如果恶棍不是那么让人信服,那么主要人物的效果就会更糟。
迪约克·弗朗西斯,一位写赛马题材的畅销神秘小说的英国作家,早期写过一部故事《神经》,赛场上的所有骑手被一位电视明星所指控。他私下里偷偷地散布流言,阻止骑手准时参赛,并给赛马打麻药。他为什么这样做?原来他是一名赛马主的儿子,害怕马,因而产生了对马业成功者的妒忌心理。
这本书主题荒诞,对邪恶的电视明星莫里斯·坎普洛尔描述粗略,只有他蓄意谋杀的恶梦让读者感觉真实。是什么赋予了这本书生命力,使得它以急速的步伐,带着那些上钩的读者一起前行呢?是对人物的处理。在迪约克·弗朗西斯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用第一人称讲故事。与弗朗西斯的其他主人公相比,《神经》中的主人公‘哦”是一个古怪的人,出身于音乐世家,却是家中惟一不从事音乐的人,被亲戚瞧不起,只好到其他领域调整自己,竟济身于赛马界。将主人公在伦敦节日大厦指挥演奏贝多芬的优雅,与在爱司科特城的赛马疾驰对比,似乎过于古怪而不能令人信服。当他挣扎着与阴谋计划抗争时,我们才充满激情地站在主人公一边。恶棍形象模糊,主角就要占更多的分量。
一些作家是人物的收藏家。不管去哪儿,他们都会观察聆听,录音,记笔记。如:火车站一位穿着黑色条纹服的胖妇人,带着两个文静、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她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外衣,牵着她的手臂。地铁里有位干瘦、身高三英尺的男子,他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未剃须,戴着金耳环。在聚会时遇到一位职业肖像画家,他在20年来每两个月画一幅肖像,有照相机一样的眼力。这位女士,尽管举止得体,风度翩翩,却是一位痴狂的训导师,每听到一句话,她都会插嘴纠正说话人的错误,非常礼貌,可是,呢,那么严肃……
收集角色是个好习惯,迟早有一天你会使用到他们。
你有了强大的人物阵容,但没有情节,那么请广泛地作这方面的笔记,诸如那些人物的爱好、憎恶、习惯、儿童时代。像爱德华·阿尔比那样,把他们放到不同的环境中,让他们面临危机。假如那身穿黑条纹的妇女是一艘沉船上4O名学生的负责人,她该怎么办?让她与家长邂逅。设想画家坐在地铁里,正在画速写,红头发戴耳环的男子对自己被当成写生模特感到气愤,他会抓起速写本在下一站下车吗?人物可以突然出现然后走开,留下许多疑问。假设他们接着不期而遇,又该在哪个地方呢?
设想简·奥斯汀自言自语,“现在,让我们讲一个明智、现实的姐姐和一个放纵、激情的妹妹的故事,她们会爱上哪种类型的男子?”
假设在写《理智与情感》时,她按另外一种方式写她的故事:明智的伊利诺爱上了英俊、浪漫的韦勒比,敏感的玛丽安被可靠平凡的爱德华所征服。但这决不可行。玛丽安不可能爱上爱德华,就是一千年也不可能。简·奥斯汀在她22岁的时候,就已经将她的人物和情节完美地合在一起了,由一个引出另一个,完全没有割裂感。但试探、假设、重新思考是有趣的,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大作家对人物的把握是如此精确。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下笔之前,对这些人物就非常了解。
展示人物的办法有好几百种,最坏的就是平铺直叙。
我最近的小说《背景背后的秘密》讲述了两个人闪电式结婚的浪漫故事。接着,在冬日蜜月里,他们都悬在了真空中。他们发现,尽管两人认识很久,彼此却并不是对方所理想的那种人。为了产生震惊效果,我必须熟知他们童年的故事。为了不至于开始得太早或者用太多的倒叙手法使读者生厌,我让人物A在蜜月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而B的故事则以片断的形式散布于整个小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