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年04月15日 06:02:40分享人:玩具来源:互联网16
秋收前半拉月,是村西头少有的空闲时光。这些天,各家各户都不约而同地打起袼褙来。母亲在世时曾说,打袼褙不是件容易的活儿,它正经八百地算作民间的手工艺呢。那些年,人们脚上穿的布鞋多是自己做的,而那鞋帮鞋底可都是袼褙做出来的。这门手工艺不好做,却也吸引人。你看,前院的李大娘、后院的徐婶儿、东院子的张大嘞嘞老婆、西院子的王二姐,她们不都乐此不疲地忙碌着吗?打袼褙,除了活儿好、————时间充裕外,最重要的是要准备好充足的布头和面糨子。面糨子倒还好说,再穷,一年下来也能攒个一碗半碗的白面来,实在不成,就在前后左右的邻居家借上一点儿,总能打出一盆半盆稀糊糊的糨子。可打袼褙主要材料是布头,没有布头打袼褙无从谈起。要说这些布头来历也不简单,它们或是裁缝剩下来的,或是破旧不堪的衣服撕扯下来的,或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反正是五湖四海各路神仙,比不上现如今打袼褙可以弄上几大块周正的布料省时省力。那时,要能有现在的大块布料早给孩子做件新衣服了,再不济也能做件短裤之类,免得让人家笑话裤子里没裤衩穿。打袼褙的布头要仔细挑选,用剪刀把上面的线头剪掉,再找来一只大盆倒满水,把这些布头搁到里面浸泡半天,好好洗一洗。谁敢保证这些破布头那么干净啊?当然,洗完了就要晾晒。这不,村西头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挂满了参差不齐、五颜六色的布头。每个院子,都像一艘艘挂满万国旗的船只随时准备出港似的。打袼褙可真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儿。脏,所接触的布头又凌乱又埋汰,外加黏糊糊的面糨子,稍微不注意,就将满手满身弄得脏兮兮的;累,就更不用多说了,除了双手不停地在破布头和面糨子之间捯饬外,还要算计袼褙的布局和布头的拼接,怎么粘选什么样的布头粘,不仔细斟酌一番还真不行。而且,袼褙多是要站着打的,当然坐在炕上打也成,母亲就经常这样打袼褙。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反正几张袼褙打下来,不累个腰酸背疼腿抽筋不算完。不管脏还是累,总得打几张袼褙,要不,该用啥做鞋啊?那时,想知道哪家女人勤快不勤快,是不是过日子的人家,看看她家院子里晾晒的袼褙就知道了。要说打袼褙这活儿还真有那么点儿艺术性。首先,你要搬来面板或者小方桌,放在平稳的地方,屋里当然是放在炕上最好,在外面呢,就视情况而定了。是面板,就找来两只板凳,将面板放在板凳上;要是小方桌,那就更好办了,直接放在炕上或是地上就成了。你开始往面板或桌面轻轻刷一层糨子,将一张大黄纸铺到上面粘牢后,往大黄纸上刷一层糨子,就可以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往上面粘破布头。粘满一层后,你再往上面刷一层糨子,如此这般,粘至三五层即可。而后,你将粘满袼褙的面板或方桌挪到阳光好或者温度高的地方去晾晒去烘烤,直到袼褙干了,能顺利从面板上揭下来,袼褙就算打完了。那些年,为了让全家人有充足的做鞋用料,母亲没少打袼褙。母亲真辛苦,除了要给全家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外,还要下地生产,饲养家畜、烧火做饭,整天家里家外不停地忙碌着。在村西头,我家打袼褙的时间总要比别人家提前那么几天,而所打的袼褙也比别人家多比别人家好。一到这个时期,母亲整天系个围裙,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着袼褙。方桌上、面板上,母亲一张一张地精心制作,就像制作一张张精美的图画。经母亲一粘,那原本零散的布头就一下子集中在一起,相互粘得既得体又牢靠,就像全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坚强地走下去。在岁月的长河中,村西头打袼褙的生动场景早已成为历史,但那些在打袼褙中呈现的鲜活的人鲜活的事却印刻在我的记忆中。东院张大嘞嘞的袼褙打得是鸡飞狗跳。本来,张大嘞嘞东拼西凑弄来不少布头,装了满满一大筐,还没等清洗呢,就被他的傻儿子连筐带布头一起卖给收破烂的了。那个收破烂的欺负傻子无知,只付给傻子几粒糖球。精明惯了的张大嘞嘞哪吃过这样的亏啊,用了三天时间总算找到了那个收破烂的,上前就是一顿理论。那个收破烂的是老江湖了,根本不在乎谁来找后账。反正一个傻子说不清道不明,根本无法对质。所以,任凭张大嘞嘞吐沫星子乱飞,收破烂的头还是摇得像他手中的拨浪鼓似的。无奈之下,张大嘞嘞又拽着哭哭啼啼的傻子过来。而傻子一见收破烂的却破涕为笑,连连喊“糖!糖!甜!甜!”除此以外,就啥也说不清楚了。张大嘞嘞又急又气,对傻子挥手就是两个耳光。张大嘞嘞老婆在院里喊:“大嘞嘞,你个没用的东西!你看人家西院老朱家打了那么多张袼褙了,你不想办法弄布头光顾打傻子有个屁用?”张大嘞嘞一听更来气了,站在原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对收破烂的和傻子怒目而视。收破烂的只管收破烂,哪管你瞪眼不瞪眼,他一面晃悠着拨浪鼓喊“破烂换糖球,破烂换钱那”,一面推着车向村东头走去。余怒之下,张大嘞嘞不由分说把傻子身上那件脏兮兮的衣服扒了下来,嘁哩喀喳就将衣服撕成了一堆碎布头。光着膀子的傻子一见又有了布头就嘻嘻笑了:“换糖!换!”傻子这一嚷嚷不要紧,张大嘞嘞对傻子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我让你换糖!换你妈了个X!”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指责张大嘞嘞犯傻劲。母亲闻讯赶来,把傻子护在身后:“大嘞嘞,孩子傻不懂事,你还不懂事?”“我就是打这个傻东西,看他以后还犯傻不犯傻?”“你这样打他,他不更傻了吗?”平时能说会道的张大嘞嘞被母亲质问得没了词,索性一下子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大哭起来。母亲将傻子领到院子,给傻子洗了脸,又将哥哥换洗的衣服找来穿到傻子身上。哥哥有些不高兴,在一旁噘着嘴直嘟囔。母亲说:“傻子没衣服穿,咱不能看着不管。等过年时,妈再给你做件新的。”哥哥这才不再撅嘴,可傻子还是长一声短一声哭着。母亲到碗橱里摸来一个大饼子给傻子。一见到大饼子,傻子顿时不哭了,接过后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边不哭了,那边张大嘞嘞和他老婆却吵了起来。张大嘞嘞:“让你不锁好,看你这回打个屁袼褙。”张大嘞嘞老婆嘴从不让人:“你就没责任那,钥匙一直把在你手里,你咋不锁好?”“我要死了,你还不打袼褙啦?”“你要死了,俺就改嫁,谁稀罕你。”“你个山东娘们,年底老子要穿不上棉鞋,非打死你不可。”“俺就不给你做鞋,你打死俺吧。”越说越离谱,越说越激动。母亲又上东院劝张大嘞嘞两口子,劝了一会儿后,母亲转身回到家中,把几张晾干了的袼褙卷起来,送给张大嘞嘞老婆。张大嘞嘞老婆一见连连推让:“他婶子,这是你辛苦打出来的,俺咋好意思要呢?”张大嘞嘞也说:“嫂子咋这样客气,让我们咋好意思呢。再说啦,你们家也要做鞋呀?”母亲说:“不碍事不碍事,家里还有些布头,我再打就是。只要你们两口子和和美美的就成。”打袼褙是女人的活计,当然,对老光棍徐大个儿而言就另当别论了。徐大个儿一年到头除了早年买的一双干农活儿的破胶鞋外,剩下的都是别人穿剩下送给他的,这两年再也没穿过新鞋了。没新鞋穿,自己还不能试着做?徐大个儿这个人平素就很喜欢女人活儿,比如,织毛衣。自己身上穿的这件毛衣,就是他看妇女们织毛衣后,反复织了拆拆了织而成的。虽然松松垮垮,但毕竟是自己织的啊。至于打袼褙,估计也没什么难的。有了这个想法后,徐大个儿就开始积攒破布头。不管哪来的不管什么样的,只要和布有关,他都捡来洗吧洗吧,晾晒一下。这样下来,一年不到布头就攒了一大堆。勤快是勤快,可这个徐大个儿喜好小人书外加嘴也馋,兜里没钱那,最后只好打这堆布头的主意了。收破烂的在村西头一吆喝,徐大个儿就抱着大筐布头跑出了家门。这倒好,他跟张大嘞嘞的傻儿子犯了同一个毛病。换了几角钱后,徐大个儿就喜滋滋地到供销社买了半斤槽子糕、一本小人书,解馋加过瘾,倒使徐大个儿开心了几天。等看到别人家打袼褙了,徐大个儿这才想起自己那过冬的棉鞋还没着落呢。再去捡也来不及了,徐大个儿只好灰头土脸地到各家乱转。看看也好,也算过过打袼褙的瘾不是。自从车老板子马二贵死了以后,他媳妇就成了寡妇。寡妇拉扯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苦熬度日,苦楚不说也能明白个七八分。不知不觉,徐大个儿就转到了马寡妇家门前,见马寡妇在院子里正低头打袼褙,就壮着胆儿走了进来。“妹子,一个人忙活呢?”徐大个儿没话找话。“不一个人忙活,你还能帮我咋的?”马寡妇连头都没抬。“能能能,我能帮你!”徐大个儿一听就来劲儿了,伸手刚要去帮忙,马寡妇那10多岁的儿子从屋里跑出来:“我家不用你搀和,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徐大个儿脸通红:“你这孩子咋这样说话呢,是你妈让我帮的,又不是我主动的。”马寡妇一听就急眼了,抬起头冲着徐大个儿就喊:“你个光棍也敢欺负起我们孤儿寡母的,你还是不是人啦?”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徐大个儿一见慌了手脚,赶紧往院外走。正好,张大嘞嘞挑水打门前路过,见徐大个儿慌里慌张从马寡妇家出来,又见院里马寡妇在哭,就好奇地放下挑子:“哎呀,大个儿,你这是咋地啦?咋给人家造哭了呢?”徐大个儿哪有心思和张大嘞嘞斗嘴,三步并两步跑开了。张大嘞嘞望了一眼徐大个儿的背影,又回过头向马寡妇家院里望了一会儿,这才一脸坏笑地跳起水桶往家走去。在中国,流行病和绯闻传播的速度最快。没过几天,徐大个儿调戏马寡妇的谣言在村西头不胫而走。老海叔站在队部门前大骂了好一通儿,还是感到有些不解渴,就喊:“刘瘸子!刘瘸子!”刘瘸子打队部里面一瘸一拐地晃了出来:“啥事,队长?”“你去!去把徐大个儿给我喊来!”老海叔吩咐道。“喊他干啥?”刘瘸子明知故问。“妈了个巴子!让你喊就去喊,啰嗦个屁!”老海叔把火气往刘瘸子身上撒。“喊就喊呗,骂啥人呢?真是的。”刘瘸子嘟嘟囔囔地走了。老海叔瞪着眼睛看着刘瘸子远去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徐大个儿屁颠屁颠地来了,身后不远处跟着幸灾乐祸的刘瘸子。“你妈了个巴子的徐大个儿,你发骚发大发了吧?娶不到老婆就撩骚人家寡妇?还他妈的是人吗?”老海叔没等徐大个儿发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徐大个儿一脸委屈:“队长,谁说我撩骚马寡妇了?人得有点儿良心,我徐大个儿娶不到老婆不假,可我绝不干那磕碜事儿。”说完,徐大个儿就回头瞪了一眼刘瘸子。刘瘸子赶紧说:“别看我,和我没关系。”老海叔:“你别他妈的七月半的鸭子——嘴硬!你要是不往人家那儿瞎转悠瞎撩骚,谁能议论你?”徐大个儿说:“队长,话可不能这样说。谁去她家谁就是撩骚啦?你还去过她家呢,那能说是撩骚?”徐大个儿叭叭地说着,刘瘸子在一旁捂着嘴直乐。老海叔哪受过这种奚落啊,上去就给徐大个儿一个嘴巴,嘴里骂道:“妈了个巴子的徐大个儿,我他妈的还管不了你啦,竟然反咬一口诬陷起我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徐大个儿捂着脸喊:“你是队长就可以打人啊?凭啥说我撩骚,就想帮打个袼褙,就成了撩骚,还有没有天理啦?谁要是撩骚,天打五雷轰!”说完,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老海叔这个人向来是怕软不怕硬,一见徐大个儿哭了,反倒没了主意。他定了定神说:“妈了个巴子,挺大一个男人像个娘们似的还哭上了,行啦,别哭了。刘瘸子,你把他拉起来。”刘瘸子会意,强拉硬扯把徐大个儿拽了起来。老海叔说:“走,到队部里说。”三个人这才走进屋里。老海叔一屁股坐到队部那把他专用了几年的靠椅上:“大个儿,你给我详细说说,你到马寡妇家到底干啥去了?要照直说,别弯弯绕。态度好了,再大的事我都帮你顶着;态度要是不好,那可就别怪我啦。说吧。”徐大个儿抹了两把眼泪,甩了一把鼻涕,这才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如何讨好马寡妇如何想混张袼褙做双鞋的行为向老海叔叙说了一遍。一旁的刘瘸子一听有些急了:“哎呀妈呀,这张大嘞嘞也太他妈的不是玩意了,怎么随便编排人家大个儿呢?我就说嘛,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咋能撩骚马寡妇呢?”“刘瘸子,你说这事儿是张大嘞嘞造的谣?”老海叔“腾”地一下从靠椅站了起来。刘瘸子自知说走了嘴,支支吾吾地转身晃了出去。“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从马寡妇家出来,就碰到了张大嘞嘞了。这大嘞嘞真是个冤家!”徐大个儿恍然大悟,老海叔也什么都明白了。第八生产队以前从未开过批斗会,这倒不是说第八生产队组织不起来,也不能说社员们的觉悟低,主要是老海叔这个人心地善良,比较宽容,不是那种对上谄媚对下蛮横的人。但今天晚上第八生产队召开的批斗会,却是老海叔提议并主持召开的。队部里黑压压地坐满了社员,老海叔坐在前面的靠椅上表情十分严肃。副队长梁翠花、会计李眼镜、记工员孙四喜、民兵连长张二愣、看青的宝叔都坐在第一排,第二排依次是10个小组的组长,第三排,那就随便坐了。大家伙只知道开批斗会,却不知道批斗谁,都窃窃私语在那里瞎猜。见大家伙都到齐了,老海叔就清了清嗓子站起身直奔主题:“咱也别称什么社员什么同志,今晚我就称呼大家伙为老少爷们。村西头这个地方自打存在的那一天开始,老少爷们就在一起生活,有的都是几辈子的交情。叫什么来着,对,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咋样谁什么德性,都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做人得有良心,没有良心猪狗不如。徐大个儿多好的人那,乐观向上,没抱过谁家的孩子跳井,也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为了让马寡妇帮打一张袼褙,好做一双过冬的棉鞋,可是却被一个没了人味儿的东西泼了脏水,造谣和污蔑人家撩骚马寡妇。这还是个人吗?”老海叔这一顿演说,大家伙一下子就明白了,都齐刷刷将目光转向蹲在墙角处的张大嘞嘞。此时的张大嘞嘞满脸羞愧耷拉着脑袋,要是有个地缝,他都能立马钻进去。老海叔厉声喊道:“张大嘞嘞!”张大嘞嘞一激灵,连忙站起身。“你说说你还是人吗?你干啥要陷害人家徐大个儿,说!”老海叔愤怒之火都要把头发顶了起来,社员们也跟着喊:“快说!”张大嘞嘞带着哭腔:“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啊。”屋里这下子开了锅,不少人都站起身来骂张大嘞嘞缺德做损。有的还要冲上前去揍张大嘞嘞,就连喜欢和老海叔唱反调的梁副队长也忍不住骂道:“好你个张大嘞嘞,你可真是缺德带冒烟了,难怪你家出了个傻儿子,原来是你缺德缺的啊!”张二愣义愤填膺,站起身挥着拳头喊:“打倒坏分子张大嘞嘞!”很多社员也挥着拳头跟着喊:“打倒坏分子张大嘞嘞!”第八生产队队部顿时群情激奋。等大家伙喊完了,老海叔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坐到靠椅上,点了一支旱烟,狠狠地吸了两口,问张大嘞嘞:“张大嘞嘞,你还有什么说的?”此时的张大嘞嘞早已浑身发抖,不知所措。他连声哀求:“队长,老少爷们,我知错了,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我以后再也不敢胡咧咧了!”“那你说说,该咋样补偿人家徐大个儿的损失?”老海叔趁热打铁。“我向徐大个儿赔礼,过年请他吃杀猪菜,还帮他找老婆。”张大嘞嘞把能想到的好话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少扯犊子,谁吃你家的杀猪菜,我怕你家的猪也坏透腔了,有痘。”徐大个儿在人群中说道,有几个社员跟着说:“对,不吃他家那玩意,埋汰。”五六他爹说:“大个儿,你不去吃杀猪菜,你还不让人家帮你找老婆吗?”“我嫌他歹毒,怕整个烂屁眼的脏婆娘来。”徐大个儿刚说完,一屋子人包括老海叔都乐了。在老海叔的提议下,第八生产队对张大嘞嘞做出了如下处理:1.张大嘞嘞给徐大个儿公开赔礼道歉;2.张大嘞嘞向全体社员作检讨;3.扣罚张大嘞嘞10天的工分合计100工分;4.张大嘞嘞给马寡妇家挑三天水,每天不少于6桶。5.张大嘞嘞给徐大个儿打一张足够做两双棉鞋的袼褙。打袼褙的故事讲到这里,忽然想起母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没鞋穿,打千张袼褙都不累;有鞋穿,打一张袼褙都很难。母亲啊,您总能对生活中的简单事寻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追求多么简单,多么轻松。他们所打出来的袼褙虽然上不了亮光光的生活台面,却在艰难的日子里护住了所有人的双脚。从艰辛到富裕,打袼褙的活计已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而这活计也成为一门即将失传的手艺了。走进大鞋城,面对材质各异、款式繁多的鞋子,我感慨万千。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谁也不会再为穿鞋而发愁了,也不会再煞费苦心地收集布头打什么袼褙了。可这些鞋,真的比不上母亲用打出的袼褙制作而成的鞋子那样舒适,那样接地气。阳光洒满街头,街头开始打一张张金黄的袼褙,好为这个世界做双特大的鞋子。散淡地走在路上,眼前忽然一亮:不远处,母亲正微笑地打着袼褙,准备为全家人做一双双温暖而结实的鞋子。穿上她老人家做出的鞋,全家人所走的路真的很直很正……
2014年9月13日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25101016/316404.html
更多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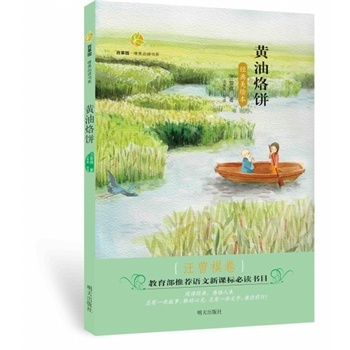
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去。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他爸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一会儿修水库啦,一会儿大炼钢铁啦。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

今天的博有点长,但故事多,一波三折有点像小说。昨晚夜宿在五道梁兵站门口。早晨是被寒冷和头疼叫醒的,其实夜里经常醒来,这次只不过是最新的一次。头疼从昨晚睡觉前就开始了,虽不很厉害但很影响情绪,让人烦躁没精神,懒得写博了,不洗就睡了

袼褙是制作中国传统布鞋的特有材料,也许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袼褙是何物,甚至不知道其读音。翻阅字典或上网查询得到这样答案:袼褙,用纸或布裱糊成的厚片,多用来做纸盒、布鞋等。解释很笼统,很轻巧,实际做起来很难。难就难在这纸或布不是整张整

雅虎的杨致远、软银的孙正义,都曾是马云阿里巴巴创业路上的贵人,也都曾是相互信任的朋友。这出支付宝转让风波,还会让他们彼此信赖吗? 里巴巴融资及股权变更行程至少在2011年之前,马云和他一手缔造的阿里巴巴帝国,都是中国为数不多

原文地址:【全台词本】《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全人物对白整理_明空手打·妃雪阁出品作者:妃雪阁官网本台词本由妃雪阁_明空 手打,转载请注明出处!首发地址:http://www.feixuege.com/thread-27288-1-1.html第一集逝者如川岁月沉淀,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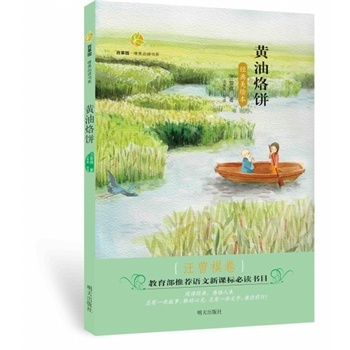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