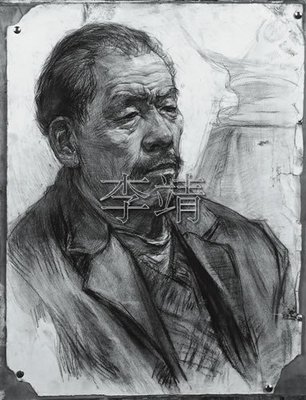赵牧
蔡翔老师在讲八十年代。他是八十年代的亲历者,一个活跃的批评家,介入了很多文学事件。于是学生们在听他讲八十年代的时候,就不仅仅对他的深入的洞见感兴趣,还喜欢听他说说一些有关的八卦。比如,说到现代派的时候他提到李陀,说到寻根的时候,他又提到李陀,于是就有同学提议,蔡老师您给我们说说李陀这个人吧。
蔡老师笑了。他说好吧,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说说八卦,李陀的八卦。蔡老师说我跟李陀太熟悉了,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让我说他反而不好说。看来蔡老师也是一个信奉距离美学的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观察,是需要距离的,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或者心理的距离等等。但蔡老师还是说起了李陀,这个被他很认真地唤作“老大”的人。我听过蔡老师不少节课了,蔡老师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用的都是学术语言,间或开几句玩笑,为把一些深刻的理论通俗化,也都是文学性学术味比较浓的。而平白地用老大这个词语,却很突兀的有种江湖气息。就这一声老大,我似乎发觉了理解蔡老师的另外一种视角。而这个视角用来理解八十年代,或许是更为恰当的。八十年代的文学圈子以及在这个圈子中非常活跃的李陀也应该是很有江湖气的吧。
蔡老师从李陀的身世讲起。他在讲的时候,特别关注我们不要记,他姑妄言之,而我等只能姑妄听之。尤其是,蔡老师以为讲一个人的身世关乎到隐私的层面,这似乎不是蔡老师所为人做事的风格。但实际上,在李劼的一篇文章中,李陀的身世已经不是谜了。李劼在这篇题为《边缘人李陀的中心话语情结》中,还提到一本书,叫做《山水相依——一个异国家庭的悲欢离合》,这本书是一个有着显赫的红色革命家庭背景的女人写的,在书中,她很亲切地称李陀为小哥哥。而这个当年的小哥哥乃她家的女佣人的儿子。李陀九岁的时候,跟母亲来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已经“解放”,他们母子应该翻身成为主人了,然而作母亲的唯一的出路,却只有到红色革命家里去帮佣。这个红色革命家庭的主人对李陀母女不错。因为这样的机缘,李陀在从很小的时候就混迹于那些国家高级公仆才有机会出没的深宅大院,并跟随他们的子女在红色贵族学校里完成了中小学教育。
这在李劼看来,象李陀这种底层的边缘化的身份,却置身于红色政权的核心地带,不知道是幸抑或不幸,因为这导致李陀“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李劼的话说得有些尖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海子是被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所谋杀的一样,李陀被这个他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逻辑给困惑至今,如今好像依然活在这个逻辑的困扰里”。这个逻辑被李劼说得非常拗口,他的意思是李陀母子作为劳苦大众的一份子,在革命后的新中国应该被视为国家的主人,而其所帮佣的主人,按照政策宣传中的人民公仆的说法,则应当被当作仆人才对。一个是现实的身份,一个是意识形态宣传的身份,难道聪明的李陀还分不清哪一项具有切切实实的决定意义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劼似乎有些强作解人了。其实,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也许决定了李陀既骄傲又自卑的情结。他在逻辑上没有一点困惑,他的困惑应该来自他在生活中的真切感受才对。
蔡老师对这一点没作任何评价,好像八卦就是八卦。但蔡老师和李劼一样高度评价了李陀之于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一个不能忽视的强悍存在,一种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巨大成就。的确,我也觉得八十年代的李陀确实值得研究。他是一个对文艺那么热爱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地搞创作,或者多写批评文字。然而他却热衷于活跃在各种文学聚会上,满足于作一个发言人,鼓吹者的角色?王蒙说,一个人没有一本书竟然被尊称为著名作家,这样的情况只有中国才有,也只有发生在李陀身上。这或者是一个俏皮话。不过李陀确实是如此,一本书没有,却绕不过他。他的艺术感觉应该很好很好,不然不会发现那么多好的作品。但是这也许和他的一味追新逐奇有关,和八十年代的那种西方想象有关。李陀在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推崇西方的人,认同西方的现代主义观念,而八十年代的作家,谁能把握或者切实地学会西方的文学路子,谁就占据了文学的制高点,而李陀就在这个制高点上给你伸手了。所以他成了八十年代的伯乐。
不过,雨打风吹,落花流水,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些八十年代的新潮作家已经乖巧地意识到西方化在市场的环境中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所以他们要告别,于是骄傲又自卑的李陀被他们抛弃了。而李陀也不见得不是主动地抛弃了他们。他比他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以及文学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来是老生常谈,但是因为李陀的叛逆心理在作怪,他到了美国必须反对美国,正如他的朋友中,谁当官他给谁疏远一样。因为这样的叛逆,这样的堂吉诃德,所以我觉得李劼虽然把李陀从神话的主人公位置上拉了下来,却更加地让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李陀,真的是一个蛮可爱的人,一个值得探讨的人,他的自卑与高傲,他的边缘与中心等等矛盾,是构成他的可爱的元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