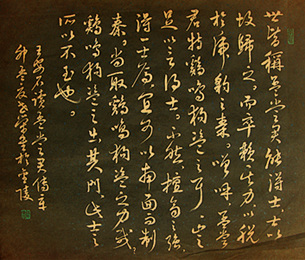【摘要】当代杰出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通过对主人公阿三与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人的故事的描述,表现了阿三在多元文化中孤独的无根漂流,流露出作者的悲伤情绪,同时体现了现代女性在爱情中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使她们 丧失了自我,最终逃离不了悲剧命运。
【关键词】王安忆、《我爱比尔》、女性、爱情、悲剧命运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四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并在2002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在国内、国际文坛均有较大的影响。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我爱比尔》直接回应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凝聚了王安忆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在上海这样一个经历了传统文明,殖民地文化和现代多元文化会合的地方, 我们如何把握自己的文化根基,这似乎是王安忆想借助这个故事所传达的。故事中说阿三之所以叫阿三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三,其实我们隐隐也能感到阿三就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她无根的漂流, 企图得到来自第一世界的比尔和第二世界的马丁的接纳,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阿三是孤独的。她孤独的根源就在于她思想上的无根及由此带来的漂泊感。她一直试图脱离她深深植根的本民族文化传统而归附于西方文化,这就使她处于一种文化归属的缺失状态, 造成了思想上的无根及行为上的摇摆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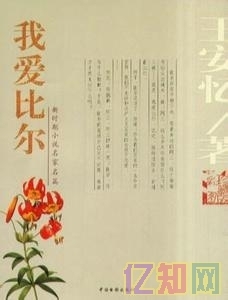
在阿三与比尔的关系中, “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 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而比尔的爱中国,喜欢阿三的“特别”与神秘,都是由于差异的存在。“阿三就像是一个未发育的小女孩,胳膊和腿纤细得一折就断似的。脖子也是细细的,皮肤薄得就像一张纸。可比尔知道,这个小纸人儿的芯子里,有着极大的热情,这就是叫比尔无从释手的地方。比尔摸着阿三的头发,稀薄,柔软,滑得像丝一样,喃喃地说:你是多么的不同啊!这就好像是用另一种材料制作出来的人体,那么轻而弱的材料,能量却一点不减,简直是奇迹。阿三看比尔,就想起小时候曾看过一个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叫做《第八个是铜像》。比尔就是“铜像”。阿尔巴尼亚电影是那个年代里惟一的西方电影,所以阿三印象深刻。她摸摸比尔,真是钢筋铁骨一般。可她也知道,这铜像的芯子里,是很柔软的温情,那是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他们两人互相看着,都觉着不像人,离现实很远的,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从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奇怪的,他们对彼此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当阿三对比尔说:我爱比尔时, 她其实是在做一次求证,求证她是否已经被接纳进“他们”的行列,因为他是多么“喜欢”她啊!但当比尔说:“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 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时,已经把阿三的位置做以界定: 猎奇的、神秘的、具观赏价值的, 同时也就宣告了阿三融入理想的彻底破灭。
在阿三与马丁的交往中,马丁作为一个画商, 虽没有相中阿三的画,却在一些关于艺术的最基本的问题上和阿三有深入的交流。他们直接认识到隔膜的存在并触碰到隔膜的本质与核心——上帝。触碰到却并无法超越,阿三再努力也无法想象出“上帝的本来”, 如果说比尔代表着政治上的西方, 那马丁则无疑象征着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显然“接近它的道路更为曲折”。随着马丁的离去, 阿三在政治上、文化上归附西方的努力均告失败, 为了继续梦幻般的生活,为了真实生活中的不真实, 她浸染在一种“大堂情结”中无法自拔, 寻找安慰, 但心中有着难以挥去的孤独。
到了劳改农场,被禁于一个幽闭的天地整日劳作,阿三才结束了幻梦般的生活, 开始有了正常生活的可能。一直以来, 阿三只是将目光投向外,努力追赶与弥合与西方的差距, 几乎从未将目光投向这些底层的民众。来到这里, 阿三开始与下层女性的接触,将目光投向自己的这些本国姐妹。严格地说, 即使同为“妓女”, 阿三与阳春面她们也是有差距的,阿三的世界远非阳春面们所能理解。她们之间的间隙并不见得比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小。所以, 阿三一直逃脱不了孤独与苦闷。
《我爱比尔》塑造了一个具有与男性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利受到高等教育的现代大学生。阿三与两个既是朋友也是师长的男性画家共同举办了画展,却并不以他们作画是为了宣泄和批判的观点左右自己, 怯生生却是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经济和生活空间上更是自由的,更具有现代女性的特点, 即使是靠绘丝巾和带家教挣房租也好, 她从未因为是为了与比尔约会而向比尔提出要求, 而在被学校开除之后,她也未向家人或比尔透露丝毫。阿三的独立意识十分明显, 是现代拥有政治与经济双重独立的女性代表。另一方面,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她似乎有着比传统女性更“前卫”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却也仍旧未逃离悲剧的命运,是因为在后来相处的时间,她专心于取悦比尔, 忽视自我, 放弃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利与要求,阿三已在爱比尔中失落了自己,她不再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个体,“没有比尔就没有阿三, 阿三为比尔存在并快乐着”。阿三对比尔的爱使有可能让比尔不高兴的事乃至想法,在阿三看来都是对比尔的冒犯, 阿三在爱中神化了比尔, 顺从、克己、奉献、隐藏自我似乎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从阿三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追求爱的本能使之放弃了一切, 一再地弱化自我,对男性存在精神依附的特点。丧失自我作为一种千年以来形成的自我定位时表现出的退缩性, 根源在于传统中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处于爱情的等待者的历史已经深深嵌入女性群体的潜意识。当她在与马丁交往过程中的她把期望放在了马丁身上,希望马丁能带她到法国去,阿三始终把自己寄予在男性的臂膀之下,她原本拥有和男性平分秋色的文化和经济地位, 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她对男人的依附性,女人将择偶或爱情看作是一种寻求人生保障的根本性力量的必由之路仍然是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历史积淀导致女性生命中深厚的依附性使阿三再次重复她的“爱情规则”;也再次把自己置于虚妄的期待之中。如小说中这样的描述“他抱着阿三,阿三也抱着他,两人都十分动情,所为的理由却不同。马丁是抱着他的一瞬间,阿三却是抱着她的一生。马丁想,这个中国女孩给了他如此巨大的感动,虽然她画得一点也不对头。阿三想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尽管他摧毁了她对绘画的看法,她可以不再画画。一个是知道一切终于要结束,一个是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能开始,心中的凄惶是同等的。马丁看阿三,觉着她离他越来越远,如同幻觉一样,捉也捉不住了。阿三看马丁,却将他越看越近,看进她的生活,没有他真的不行。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他们彼此都有些听不懂对方的话,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被自己的心情苦恼着。”终于,阿三在大堂宾馆里似乎放弃了爱情,但她还是在期待男性救世主的出现, 阿三与各种外国人周旋着, 即使如此, 在他们身上,她还是产生着同样的遐想——阿三在刚刚对一个比利时人产生了一些幻想, 将人家的公寓看成了自己的家, 还自己掏出了钱为它添置一些东西时,就在她以为这会是一场正式恋爱, 能够实现了自己的期望时, 比利时人却告诉她自己的女友要来了, 叫她不要再来了……
小说的结尾寓意深长,逃跑途中的阿三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处女蛋,“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小说在此处戛然而止,阿三最后是否逃出, 并不是作者所关心的, 作者所要表达的到此已经足够了。小母鸡的形象无疑是中国传统贞操观的象征,这不由使读者联想到阿三将自己献给比尔后对处女血的弃置不顾。在追逐西方梦的过程中, 她无根地漂流,这只蛋提醒着她这最初的底线从何时崩溃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