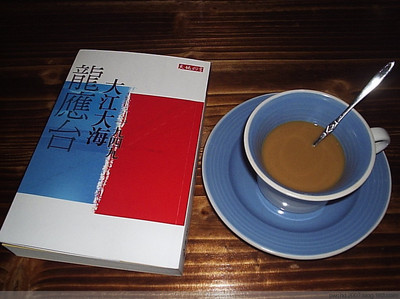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十七岁龙应台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汨汨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他看着我。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做‘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
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给儿子的信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 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经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 挪威 0.92
2 丹麦 0.84
3 荷兰 0.81
4 卢森堡 0.8
5 瑞典 0.7
6 比利时 0.61
7 爱尔兰 0.41
8 法国 0.41
9 瑞士 0.38
10 英国 0.34
11 芬兰 0,34
12 德国 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 0.25
16 纽西兰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腊 0.21
19 日本 0.2
20 奥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国 0.14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对话龙应台
人物周刊:家庭对你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扫墓,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知识分子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我们所谈的知识分子,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主责是批评。
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贻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你关注较多的是文物古迹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历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车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国人修的,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你怎么看?
龙应 台:台北市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日本人建的,我当文化局长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但是台湾银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楼──那个地皮太贵了。他们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法院竟然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论上他们当天晚上就可以连夜拆除。我要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它被重新认定为古迹,但是这要经过很多程序。我就在当天夜里12点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后来它被保护下来。
而当时文物保护的最高母法,文资法的总则第一条,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为了避免以后还有这样民族主义的文化判决,我决定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
古迹的保护从来就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因为你做了保存,活着的人得以理解过去。理解过去,是为了让他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所以在我看来保留在台湾的日本人的遗迹,甚至更早以前的荷兰人的遗迹,西班牙人的遗迹,清朝的遗迹,同样重要。这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条件。
人物周刊:你没有接受就任台湾“监察委员”的邀请,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独立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件具体的事情出来后,我都要具体去衡量,怎么样才叫独立性。监察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是台湾政治里的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弹劾政府官员的,也可以弹劾“总统”。可后来我发现,它是“合议制”的,就是说,你提出的弹劾,必须得到院内大多数“委员”的同意才有效。相衡之下,我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如我站在写作的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别费案”为马英九辩护,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独立的笔”?
龙应台:写这个文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