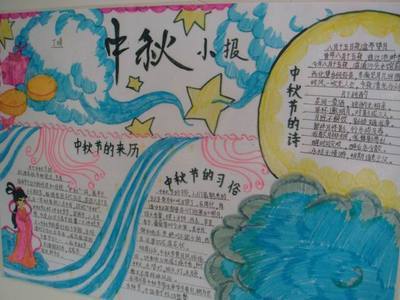东荡子诗选36首
暮年
唱完最后一首歌
我就可以走了
我跟我的马,点了点头
拍了拍它颤动的肩膀
黄昏朝它的眼里奔来
犹如我的青春驰入湖底
我想我就要走了
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
伐木者
伐木场的工人并不聪明,他们的斧头
闪着寒光,只砍倒
一棵年老的朽木
伐木场的工人并不 知道伐木场
需要堆放什么
斧头为什么闪光
朽木为什么不朽
朋友
朋友离去草地已经很久
他带着他的瓢,去了大海
他要在大海里盗取海水
远方的火焰正把守海水
他带着他的伤
他要在火焰中盗取海水
天暗下来,朋友要一生才能回来
寓言
他们看见黄昏在收拢翅羽
他们也看见自己坠入黑洞
仿佛脚步停在了脸上
他们看见万物在沉没
他们看见呼救的辉煌闪过沉没无言的万物
他们仿佛长久地坐在废墟上
一切都在过去,要在寓言中消亡
但蓝宝石梦幻的街道和市井小巷
还有人在躲闪,他们好像对黑夜充满恐惧
又像是敬畏白昼的来临
王冠
把金子打成王冠戴在蚂蚁的头上
事情会怎么样。如果那只王冠
用红糖做成,蚂蚁会怎么样
蚂蚁是完美的
蚂蚁有一个大脑袋有过多的智慧
它们一生都这样奔波,穿梭往返
忙碌着它们细小的事业
即便是空手而归也一声不吭,马不停蹄
应该为它们加冕
为具有人类的真诚和勤劳为蚂蚁加冕
为蚂蚁有忙不完的事业和默默的骄傲
请大地为它们戴上精制的王冠
黑色
我从未遇见过神秘的事物
我从未遇见奇异的光,照耀我
或在我身上发出。我从未遇见过神
我从未因此而忧伤
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
神也恐惧,从不看我
凝成黑色的一团。在我和光明之间
神在奔跑,模糊一片
牧场
你来时马正在饮水
马在桶里饮着你的头
这样你不会呆得很久
我躲在牧场的草堆里
看见马在摇尾巴
马的尾巴摇得很厉害
这回你去了,不会再来
木马
一匹好的木马需要一个好的匠人小心细细地雕呀
一匹好的木马不比奔跑的马在草原把它的雄姿展现
但一匹好的木马曾经是狂奔天空的树木
它的奔跑同时也不断地朝着地心远去
它是真正击痛天空和大地的马
它的蹄音与嘶鸣是神的耳朵
但是神害怕了,神因为抓不住木马的尾巴而彻底暴怒
它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揭去遮掩他的绿树叶
神的失望在匠人的眼睛里停滞下来
木马击痛天空和大地的过程如树叶已经散落
木马在匠人的手中停顿下来
树叶曾经在高处
密不透风的城堡里闪动的光的碎片
并非为落叶而哀伤
它闪耀,照亮着叶子的归去
一个季节的迟到并未带来钟声的晚点
笨拙而木讷的拉动钟绳的动作
也不能挽留树叶的掉落。你见证了死亡
或你已经看见所有生命归去的踪迹
它是距离或速度的消逝,是钟声
敲钟的拉绳和手的消逝。大地并非沉睡
眼睛已经睁开,它伸长了耳朵
躁动并在喧哗的生命,不要继续让自己迷失
大地将把一切呼唤回来
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曾经在高处
现在回到了地上
灰烬是幸福的
光阴在这里停顿,希望是静止的
和昔日的阳光停在窗台
假使你们感到愉悦而不能说出
就应该停下,感到十分的累
也应该停下来
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
灰烬是幸福的,如那宽阔而深远的乡村
野草的睡眠因恬谧而无比满足
即使那顶尖的梦泄露
我们的欢快与战栗,使我们跌入
不朽的黑暗,犹如大海的尽头
人们永远追赶却始终还未君临
人们跟前的灯火
我们将在黑暗中归于它
世界上只有一个
什么是新的思想,什么是旧的
当你把这些带到农民兄弟的餐桌上
他们会怎样说。如果是干旱
它应当是及时的雨水和甘露
如果是水灾,它应当是
一部更加迅速而有力的排水的机器
所有的历史,都游泳在修辞中
所有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人
诗人呵,世界上只有一个
黎明
在黎明
没有风吹进笑脸的房间,诗歌
还徘徊的山巅,因恋爱而相忘的丁香花窥视
正在插进西服口袋的玫瑰
早晨的窗户已经打开,翅膀重又回来
蜜蜂在堆集的石子上凝视庭院的一角
水池里的鱼把最早的空气呼吸
水池那样浅,它们的嘴像深渊
空中的梦想
那些在田野里起早摸黑的劳动者他们为什么呢
那些工匠在炭火里炼打刀剑和镣铐为什么呢
那些写诗的诗人们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那些出水芙蓉为什么还要梳妆打扮为什么呢
那些少妇和成年男子在街头为什么要左顾右盼
那些老人们为什么不出门远游
那些小孩建筑自己的高楼自己没法住进去呀
群峰已经低头,天空已经低头,河流带走了时光
手隔着手,眼睛看不到眼睛为什么呢
蜘蛛没有翅膀,也没有梯子和脚手架
它却造出了空中的梦想
英雄
欢呼的声浪远去
寂静啊,鲜花般放开的寂静
美酒一样迷醉的寂静
我的手
你为什么颤抖,我的英雄
你为何把喜悦深藏
什么东西打湿了你的泪水
又有什么高过了你的光荣
杜若之歌
我说那洲子。我应该去往那里
那里四面环水
那里已被人们忘记
那里有一株花草芬芳四溢
我说那洲子。我当立即前往
不带船只和金币
那里一尘不染
那里有一株花草在哭泣
我说那洲子。我已闻到甜美的气息
我知道是她在那里把我呼唤
去那里歌唱
或在那里安息
旅途
大地啊
你容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
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
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
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
阻止我的心奔入大海
我何时才能甩开这爱情的包袱
我何时才能打破一场场美梦
我要在水中看清我自己

哪怕最丑陋,我也要彻底看清
水波啊,你平静我求你平静
我要你熄灭我心上的火焰
我要你最后熄灭我站在高空的心
它站得高,它看得远
它倾向花朵一样飘逝的美人
它知道它的痛苦随美到来
它知道它将为美而痛苦一生
水波啊,你平静我求你平静
请你在每一个入口,阻止我的心奔入大海
也别让我的心,在黑暗中发出光明
在它还没有诞生
把它熄灭在怀中
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该降临的会如期到来
花朵充分开放,种子落泥生根
多少颜色,都陶醉其中,你不必退缩
你追逐过,和我阿斯加同样的青春
写在纸上的,必从心里流出
放在心上的,请在睡眠时取下
一个人的一生将在他人那里重现
你呀,和我阿斯加走进了同一片树林
趁河边的树叶还没有闪亮
洪水还没有袭击我阿斯加的村庄
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失败者举起酒杯,和胜利的喜悦一样
倘使你继续迟疑
你把脸深埋在脚窝里
楼塔会在你低头的时刻消失
果子会自行落下,腐烂在泥土中
一旦死去的人,翻身站起,又从墓地里回来
赶往秋天的路,你将无法前往
时间也不再成为你的兄弟,倘使你继续迟疑
那日子一天天溜走
我曾在废墟的棚架下昏睡
野草从我脚底冒出,一个劲地疯长
它们歪着身体,很快就掩没了我的膝盖
这一切多么相似,它们不分昼夜,而今又把你追赶
跟你说起这些,并非我有复苏他人的能力,也并非懊悔
只因那日子一天天溜走,经过我心头,好似疾病在蔓延
把剩下的一半分给他
你可见过身后的光荣
那跑在最前面的已回过头来
天使逗留的地方,魔鬼也曾驻足
带上你的朋友一起走吧,阿斯加
和他同步,不落下一粒尘埃
天边的晚霞依然绚丽,虽万千变幻
仍回映你早晨出发的地方
你一路享饮,那里的牛奶和佳酿
把剩下的一半分给他,阿斯加
和他同醉,不要另外收藏
喧嚣为何停止
喧嚣为何停止,听不见异样的声音
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层一层
山水无痕,万物寂静
该不是圣者已诞生
他却独来独往
没有人看见他和谁拥抱,把酒言欢
也不见他发号施令,给你盛大的承诺
待你辽阔,一片欢呼,把各路嘉宾迎接
他却独来独往,总在筵席散尽才大驾光临
伤痕
院墙高垒,沟壑纵深
你能唤回羔羊,也能遗忘狼群
浮萍飘零于水上,已索取时间
应当感激万物卷入漩涡,为你缔造了伤痕
芦笛
我用一种声音,造出了她的形象
在东荡洲,人人都有这个本领
用一种声音,造出他所爱的人
这里芦苇茂密,柳絮飞扬
人人都会削制芦笛,人人都会吹奏
人人的手指,都要留下几道刀伤
小屋
何必去寻找百灵,它在哪里
山雀所到之处,皆能尽情歌唱
你呀,你没有好名声,也要活在世上
还让我紧紧跟随,在蜗居的小屋
将一具烛灯和木偶安放
异类
今天我会走得更远一些
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异域
你们没有言论过的话,叫异议
你们没有采取过的行动,叫异端
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
叫我异类吧
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
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
水波
我在岸上坐了一个下午,正要起身
忽然就有些不安。莫非黄昏从芦苇中冒出
受你指使,让我说出此刻的感慨?你不用躲藏
水波还在闪耀,可现在,我已对它无望
相信你终会行将就木
为什么我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在心心相印的高粱地
不把生米煮成熟饭的人,是可耻的人
在泅渡的海上
放弃稻草和呼救的人,是可耻的人
为什么是你说出,他们与你不共戴天
难道他们相信你终会行将就木
不能拔剑高歌
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什么偏偏是你,奄奄一息,还不松手
把他们搂在枕边
人为何物
远处的阴影再度垂临
要宣判这个死而复活的人
他若视大地为仓库
也必将法则取代
可他仍然冥顽,不在落水中进取
不聚敛岸边的财富
一生逗留,两袖清风
在缝隙中幻想爱情和友谊
不会结在树上
他不知人为何物
诗为何物
不知蚁穴已空大,帝国将倾
容器
容器噢,你也是容器
把他们笼罩,不放过一切
死去要留下尸体
腐烂要入地为泥
你没有底,没有边
没有具体地爱过,没有光荣
抚摸一张恍惚下坠的脸
但丁千变万化,也未能从你的掌心逃出
他和他们一起,不断地飘忽,往下掉
困在莫名的深渊
我这样比喻你和一个世界
你既已沉默,那谁还会开口
流水无声无浪,满面灰尘
也必从你那里而来
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
鱼池是危险的,堤坝在分崩离析
小心点,不要喊,不要惊扰
走远,或者过来
修理工喜欢庭院里的生活
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吧
那里,有一根木条的确已断裂
哪怕不再醒来
这里多美妙。或许他们根本就不这么认为
或许不久,你也会自己从这里离开
不要带他们到这里来,也不要指引
蚂蚁常常被迫迁徙,但仍归于洞穴
我已疲倦。你会这样说,因为你在创造
劳动并非新鲜,就像血液,循环在你的肌体
它若喧哗,便奔涌在体外
要打盹,就随地倒下,哪怕不再醒来
他就这么看
这个人十分老土,他想把你带到旧时
他想把你从木房里拖出,重新扔回石洞
不想让你闪光,迷人,有着百样的色泽
一顶帽子无论怎样变化,即使如夜莺把夜统领
都只是戴在头顶。是的,他就这么看
这个老土的家伙已跟不上大家的脚步
他在挖掘坟墓,搂着一堆朽烂的尸骨
还想充饥,还想从细嚼中嗅出橄榄的气味
小鸟总要学着高飞,成为大鸟把天空追赶
但都飞不出鸟巢。是的,他就这么看
他已落入井底,捧着树叶像抱住森林
从一滴水里走出,便以为逃离了大海
他耳聋目盲,困在迷途,不辨声音和形状
若是把核桃砸开,他说这里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颗粉碎的脑袋。是的,他就这么看
夏日真的来了
夏日真的来了
孩子们有了新发现,一齐走进了芦苇丛
他们跑着,采摘芦苇
他们追着,抱着芦苇
两枝芦苇,择取一枝
三枝芦苇,择取一枝
秋天近了,你差一点在喊
黑夜尚未打扮,新娘就要出发
一片树叶离去
土地丰厚,自有它的主宰
牲畜有自己的胃,早已降临生活
他是一个不婚的人,生来就已为敌
站在陌生的门前
明天在前进,他依然陌生
摸着的那么遥远,遥远的却在召唤
仿佛晴空垂首,一片树叶离去
也会带走一个囚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