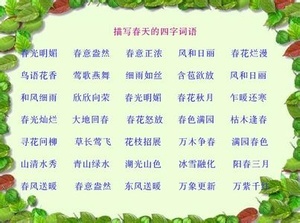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唐王维《田园乐七首(之六)》
春晴闻桃腻,梨雨堕素尘。最为伤怀者,莫过于春芳犹盛时,春阴乍来,漫天飞扬的雪片砌山砌壑。细看这纷纷扬扬的雪片,不是雪片,它们竟然是一片一片薄胜纸绢的春花。
而这时的人,却在异乡异域。
异乡异域,有酒有友,三杯两盏相劝,长歌短调相戏,却尽作思乡之结。一调萨克斯,听去呜呜咽咽如万马千军悲泣,又似凄凄唉唉冷雨成冻。此时,洒洒飘飘而来者,非情非绪,究竟为何物,拾来莫能言其状。亦未知何时何刻,酒饮于何处。次日人醒,恍然如一梦,已然不知昨聚者皆何人,何又客醒于床。数日复忆, 得某人者,询问之,乃大笑:
“醉也,真大醉也!”
人生有春,春在何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归何处,寂寞无行处。若有人知春去处,唤起归来同住。”春不仅有了知觉,还是有了具体形态的形体。“柳绿更带春烟”,“一笔云垂露”处,不是春又是什么?先不要去触碰它,它一触碰便什么都没有了。远远望去,尽作生机之趣,你待要寻它时,它便无处可寻,你要不寻它处,它又无处不在。这便是物与心之间的距离,有了这距离,便什么都有了。意韵之美,也便溶入了物与情的方方面面。
“柳绿更带春烟”,其美者非为柳,也非为绿,更非为春之烟(其实春无烟,春之烟者,也为人的幻觉罢了。当视线模糊时,什么都成了诗意,什么都成了美的向往。一笑),而在微之又微,妙之又妙的一个带字。这一“带”,便什么都出来了,什么都被激活了。而这一切,却缘自一夜无人知晓处的雨,也或无知无觉处的风,或者什么都没有过,只是生命真的走到某一步,已经无能再走的动了,花也就成了落花。
天地间最自然而然的落花,被诗者的情趣生出若干的意象。落花以一种不想让人知晓的方式自故枝落下,化为泥,化为土,化为天地间的一缕香魂。“不是桃花贪结子,叫人误恨五更风”!生命,各自有各自的机缘,一切无知者,皆自作了情多物。我佩服人的想象。情多处只自伤,自伤处,便生出来许多天地绝叹。
落红非为无情物,也非为有情物。情者,唯观者之情致也。花落不盼人扫,自纷自没自没;清风本自无心,亦无傍花四落。生与灭者,亦为天地万物的生命机缘。菩提原无树,明镜亦非台,花落未扫,也正好是心的常态。心之无动,亦无不安处,这便是诗者心的澹然。其实,要扫,真的扫的了么?生命有喜有忧,有歌有泣,醉也是生命的常态,酒不过是佐醉之物罢了。“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知道吗,知道吗,应该是绿的肥红的瘦呀?
一夜落花,它也不过完成了物与物自然秩序的流程。
人生大乐是清欢,人世清欢本一梦。
“莺啼山客犹眠。”只有这自然之态,才是真正的禅境。心自有住处,不向物外求。外物再好,它毕竟只是外物,它终究与本体隔了一段距离。睏则眠,醒则歌,宿雨桃红减几多;柳烟绿处正酣睡,人生如梦梦犹何。春山如画,人已在画中;人生在闲,闲不分季。只要能够达到饥时餐,渴时饮,人生便达到了生命情态的大自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