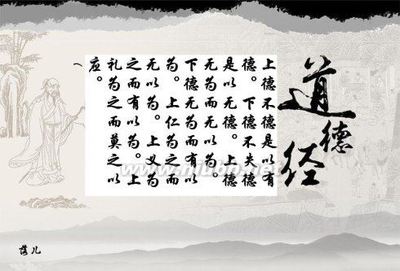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薄视时贤第三章是将天地自然的法则,引申应用到人世间的治道的发挥。这章的文字,明白畅晓,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释。但其中有三个要点,须特别注意,那便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读秦汉以上的书,有关于这个“民”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为“民”字就是老百姓,联想到现代语中“国民”的涵义。如果这样认定,观念就完全错了。古书上的“民”,就是现代语的“人们”,或者是“人类”的意思。那个时候辞汇不多,每有转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实“民”字是代表所有人们的一个代号。如果对这个观念认识不清,就很容易误会是上对下的一种称谓,而变成古代帝王统治者的口气了。
第二章讲到我们做人处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辞劳瘁。但是自己却绝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人们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风范。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有辞于劳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于这一原理的发挥运用,而讲到人世间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原则。但我们须要了解,在老子那个时候,是春秋时代,那时的社会形态在改变。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适应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争权夺利,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我们研究历史,很明显地看出,每当在乱变时代中的社会,所谓道德仁义,这些人伦的规范,必然会受影响,而惨遭破坏。相反地,乱世也是人才辈出,孕育学术思想的摇篮。拿西方的名辞来说,所谓“哲学家”与“思想家”,也都在这种变乱时代中产生,这几乎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的通例。
同时,正当大动乱如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的诸侯,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随时随地都在网罗人才,起用贤士,作为争权夺利,称王称霸的资本。所以那个时候的“士之贤者”——有才能、有学识、有了不起本领的人,当然受人重视。“尚”,就是重视推崇的意思。“贤”,就是才、德、学三者兼备的通称。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虽然不特别推重贤者,但却标榜“君于”。孔子笔下的“君子”观念,是否概括贤者,即难以遽下定论。但后来的孟子,非常明显地提出贤者与能者的重要。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便是他的名
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主张?我们如果了解秦汉以上与道家、儒家并列的墨翟 ——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领会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都知道,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想,是特别强调“尚贤”的。主张起用贤人来主政、当政。因为他所看到当时社会的衰乱,处处霸道横行,争权夺利而胡作非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统领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张要“尚贤”与“尚同”。他这个“同”,又与孔子记述在《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同”不尽相关,但也略有连带关系。他的“同”,与后世所讲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现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张,在中国上古文化中,战国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释迦牟尼则更早提出了一切众生平等的理论。
现在我们不是讨论墨子这个主题,而是在这里特别注意墨子的“尚贤”主张,为什么也与儒家孟子的观念很相近,而与道家老子的思想却完全相反呢?这就是因历史时代的演变,而刺激思想学术的异同。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而且以墨子当时宋国的国情来看,比照一般诸侯之国的衰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所以造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变乱,在许多锗综复杂的原因当中。最大的乱源,便是人为的人事问题。尤其是主政或当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么天下事,不问便可知矣。
此所以后世诗人有“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的深长叹息了!鲁国潸然,是指孔子眼见由三代而到“郁郁乎文哉”周代的中国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鲁国,已经开始变质而衰败,周公后裔的鲁国政权,又都操在奸党的手里,因此他无可奈何潸然含泪而身离祖国,远游他方。自此以后的历史,再也不能恢复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样地,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的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他所立身处地所知、所见、所感受到的结论,而大声疾呼要“尚贤”与“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贤与不贤的君子小人之辨讲到这里,让我们暂时推开老子,而另外介绍后世的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拭)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拭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
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少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家串(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廷、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亲自出京去游览求证。但所得的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拭(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脑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此外,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它与老庄思想,也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相同于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观念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则比周而相誉,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诽誉交争,则主威惑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叫做“比”。“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的,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说:“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诽誉交争”,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牵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姊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人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道家与法家的辨贤人文历史的演变,与学术思想相互并行,看来非常有趣,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有正必有反,有是就有非。正反是非,统统因时间、空间加上人事演变的不同而互有出入。同样也属于道家的鬻子——鬻熊,如果只依照传统的说法而不谈考证他的生平,那么,他比老子还要老了,应该属于周文王时代,与姜太公——吕尚齐名并驾的人物,也是周文王的军师或政略咨议的角色。但他却主张需要起用贤者,而且提出贤士的重要性。如说:“圣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犹无有也。王道衰,千里有一士,则犹比肩也。”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古的时代,人心都很朴实,不需要标榜什么道理等等名号。上古时代,圣王在位,纵然百里之内,有一个道德学问很好的人,也是枉自虚生,好比没有用的人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差不多,又何必特地请一些贤人来治世呢!好比说,一个社会,完全安分守法,既无作奸犯科的人和事,便不需要有防止、管理作奸犯科的警察了。但他又说,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千里之外如有一贤士,也要立刻找来,与他并肩同事以治天下。
从鬻子的理论观点来看历史,一点也不错。例如生在盛唐时代的赵蕤,也是道家人物。他纵有一肚子的谋略学问,但生在升平时代,又有什么用处?只有著书立说,写了一部《长短经》传世,自己去修道当隐士。虽受朝廷征召,始终不肯出山,因此在历史上,称他赵征君。他虽然传了一个徒弟李白——诗人李太白,晚年用非其时,又用得不得当,结果几遭身首异处之祸。好在他年轻时帮忙过危难中的郭子仪,因此后来得郭子仪力保,才得不死。如果再迟一点,在安禄山、史思明以后的乱局,也许李白可与中唐拨乱反正的名相李泌并驾齐驱,各展所长,在历史上便不只属于诗人文士之流,或者可有名臣大臣的辉煌功业呢!
鬻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臣已老矣。坐策国事,臣年尚少。
其实,文王说的“老矣”,是一句故意说的笑话,而且也有些为自己感慨的味道。文王用姜太公时,吕尚的年龄,已过了八十岁。他与武王的年龄不相上下。当然,九十岁以外的人,明知兴邦大业,已非自己的年龄所能做到,有如清人赵翼的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因此对鬻子开了一句玩笑——“嘻!老矣”。是鬻子老了?还是他感慨自己也老了?只有他自心知之。可是鬻子的答案,也正合文王的心意,彼此知心,一拍即合,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贤良待沽,因此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岂不是“尚贤”的明证?况且法家如韩非,他虽然主张法治而不重人治,但用法者是人,不是法。人不用法,法是废物。韩非自荐,正是自认为是贤才,因此而求鬻卖于帝王。如果人主不“尚贤”,韩非又向哪里去卖弄他自己的贤能呢?
且让我们再来看看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他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乌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
淮南子这里所提出的相反道理,正如老子所说:“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的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穷则诈”,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如法家的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道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而又否定法治的功能,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地太平。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数计,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了,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再回过来讲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那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是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如果拿世界宝石标准来评定,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的道理,对大家研究老子这句话的内涵,相信会更有帮助。
现代化好人与老人的表扬法老子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经人重新整理过,但大体上,已整理得很好,把每一句话的含义性质分别归类。如果各抒己见,认为它原文排列有错误,那就各成一家之言,很难下一定论。--
我在介绍第一章的时候,曾首先指出,老子往往将道的体相与作用,混合在一起讨论。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谓老庄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掺杂,应用无方,妙用无穷,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读老庄如读《孙子兵法》一样,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那么,要想把《老子》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是很费事的。尤其在入世应用之道方面,常常牵涉到许多历史哲学。利用史实,加以选择,透过超越事实的表面层,寻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讨论。这在一般学府中应该属于一门专门课程。但是许多地方,牵涉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了。比如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句话,尚贤与不尚贤怎样才对,就很难定论。换一句话说,一个真正太平的盛世,就没有什么标榜好人的必要,我们只列举现代化的一两个故事,大概可以增加些许“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趣味性。
几年前,台湾社会上发起一个“敬老会”,对老人,表扬其年高德劭。第一次举办时,我就发现,这简直是在玩弄老人,为老人早点送终的办法。叫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坐在那儿听训、领奖,还要带去各地游览。实际上,对于老人是一种辛苦的负担,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坏了,而且更因为这种风气一开之后,就有许多人也不免想进入被“敬老”的行列,这样就变成有所争了。岂不见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吗?又如,我们标榜好人,让好人受奖,开始动机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形成风气后,社会上就有人想办法去争取表扬。那么,表扬好人的原意,也就变质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荐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来,好人好事太多,推荐谁去好呢?而且征求一下,大家只对我一笑,摇摇头,摆摆手,谁也不肯接受推荐。我常常笑着说:有两个好人,我想推荐,可惜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未投生。大概我还勉强像小半个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样,讨厌人家推荐我,更怕自己推荐自己。还是相应不理,让贤去吧(一笑)。我们由这两个故事,大概就可以知道,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在老子当时的社会,在那个历史政治的形态中,“尚贤”已经是一种毛病,因此他提出这句话来。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其实,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作人与做事两个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在纯粹哲学的角度来看,很难下一确切的定论。如果单从用人行政的立场来讲,清初名臣孙嘉涂的“三习一弊”奏疏中,已经讲得相当透彻了!其中如说:
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们),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都是贤者)。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扶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