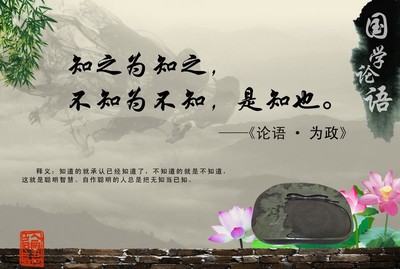我们心中存着某些目的,看到任何东西都会从有用与无用的角度来判断。但是,有用与无用真的是二分法吗?随着我们目的的改变,时间的延长,空间的扩大,所谓的有用与无用很可能换了位置。
对于世俗的单一价值观,就是认为取得有形可见的成就(如名利权位)才算是有用人才的看法,庄子向来抱着批判的态度。他是故意与世人唱反调呢?还是期许世人不要执着于此而忽略生命的更高价值?
庄子与惠施多次辩论,主题经常环绕着「有用与无用」。从表面看来,惠施得君行道,应该算是有用的人才;庄子一生穷困,似乎毫无用处。这是最后的定论吗?仔细研究他们的辩论,就会找到明确的答案了。
1.「无用之用」的文本
庄子与惠施关于「无用」的辩论不只一次,我们先从最简明扼要的谈起。在〈外物〉中,惠施直接发难。原文大意如后:
惠施对庄子说:「你的言论都是无用的。」

庄子说:「懂得无用的人,才可以同他谈有用。譬如地,不能不说是既广且大,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而已。但是,如果把立足之地以外的地方都挖掘直到黄泉,那么人的立足之地还有用处吗?」
惠施说:「无用。」
庄子说:「那么无用的用处也就很清楚了。」
以上这段数据在说什么?譬如一个年轻人在学校念书,这时学校以外的世界各地对他都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无用之地都消除的话,他在学校念书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原本以为有用的学校至此也变成无用了。换言之,有用与无用之间不可采取二分法去切割,因为它们是相互为用的。
因此,任何东西都有用,就看是否用对地方。庄子在〈逍遥游〉与惠施再度谈到类似的题材。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我大葫芦的种子,我把他栽植成长,结出的葫芦有五石的容量。用它来装满水,则它不够坚固,无法负荷本身的重量。把它剖开做成瓢,它又宽大得没有水缸容得下。这葫芦不可说不大,我却因为它没有用而打碎他。」
庄子说:「先生真是不善于使用大东西啊!宋国有个擅长调制不让手龟裂的药物,世世代代都以漂洗丝絮为职业。有一位路过的客人听说这件事。愿意出一百金购买他的药方。他召集全家人来商量说:『我们世世代代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而已,现在一旦卖出药方就可以赚到一百金,就卖给他吧!』这位客人拿了药方,便去游说吴王。正好越国兴兵来犯,吴王派他担任将领,冬天与越人在江上作战,结果大败越人,并因而得到封地做为奖赏。」
他接着说:「能够不让手龟裂,所用的药方是一样的;但是有人获赏封地,有人不得不继续漂洗丝絮,这是因为所用之处不同啊!现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芦,为什么不绑在身上当成腰舟,让自己浮游于江湖之上,却还要担心水缸容不下它呢?可见先生的心思还是不够通达啊!」
对这段故事的总结思考可以用〈徐无鬼〉的一句话来说:「譬如药材,乌头、桔梗、鸡头草、猪零根这些药草,在需要用它做主药的时候,就珍贵了。」今天我们知道,连垃圾也可以变成黄金,就看你如何运用了。
《世说新语》记载一则轶事。
陶侃个性谨慎而严肃,做事也认真负责。他担任荆州主管时,命令船官把锯木所留的碎屑全部收集保存起来。大家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在元旦集 会那天,正好遇上雪后初晴,大堂前的台阶上融雪还很湿,他吩咐洒上木屑覆盖,让大家进出都很方便。另外,官府购用竹子时,他每次都命人收集旧竹头,堆起来像座小山。后来桓温进攻蜀地装配船只时,就用这些厚竹头做了竹钉。
西方学者指出:「自然界不跳跃。」意即自然界所形成的整体是完整而没有空隙的,其中的每一样东西,连空气在内,都是不可少的。这种连续性与整体性,就是「不跳跃」,不会错过任何一样东西。亦即没有任何东西是全然无用的。你若是真的取消其中一物,则后续的演变将难以想象。所谓「蝴蝶效应」,就是指类似「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连锁反应。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细节」,甚至喊出「细节决定一切」的口号。谁还会认为细节无所谓呢?焦点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不只是励志格言,而是客观的事实,就看你是否能够拓宽「有用」的领域,从整体与长期来看待自己,再从外在转向内在,培养正确的观念,懂得「平安就是福」的道理,有时不妨学习庄子所说的「使用大葫芦」的方法,浮游于人间。
2.自处之道
当庄子自己受到「无用」的质疑时,他会如何辩白呢?这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自处之道。在〈逍遥游〉的结尾部分,有底下一段数据。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称它为樗。它的树干臃肿而不合于绳墨,它的树枝卷曲而不合于规矩。就是把它种在路旁,木匠也不屑一顾。现在你所说的话,内容广博而毫无用处,大家都会弃之不顾的。」
庄子说:「你难道没有看过野猫与黄鼠狼吗?牠们弯曲身子埋伏起来,等着要抓出游的小动物;东跳西跃地追捕,不管位置是高是低;最后都中了机关,死在陷阱中。再看那牦牛,牠的身躯大得像天边的云朵。这可以说是够大了,但却没办法捉老鼠。」
他接着说:「现在你有一棵大树,担心它没有用,那么为何不把它种在空虚无物的地方,广阔无边的旷野,再无所事事地徘徊在树旁,逍遥自在地躺卧在树下。它不会被斧头砍伐,也不会被外物伤害,没有任何可用之处,又会有什么困难苦恼呢?」
庄子使用语言的奥妙能力,可谓出神入化。惠施将他比拟为无用的大树,他在回答时,先指出「有用」的限制与危险,也说明「无用」的平安与趣味。但是读到最后,他好像结合了大树与人,认为两者都可以得到保全,并化解一切烦恼。是大树让人摆脱了烦恼,而大树自身也解消了一切烦恼。
惠施听了庄子这番回答,到底能不能觉悟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在庄子心目中,惠施扮演了什么角色?〈徐无鬼〉有一则轶事,提供了最直接的答案。当然,庄子说的还是寓言。其文大意如后:
庄子有一次送葬到墓区,经过惠子的坟墓。他回头对跟随的人说:「郢地有个人把石灰抹在鼻尖上,薄得像苍蝇的翅膀,再请石匠替他削去。石匠运起斧来轮转生风,顺手砍下,把石灰完全削去,而鼻子毫无损伤。郢地这个人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就召石匠来说:『请你做给寡人看看。』石匠说:『我还是能用斧头削去鼻尖上的石灰,但是,能与我搭配的对手已经死去很久了。』自从先生去世以后,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可以谈话的人了。」
根据历史资料,惠施在公元前310年去世,庄子比他多活了二十几年,所以这则轶事相当可靠。庄子有自知之明。〈天下〉的作者不论是否庄子本人,在描写庄子时说:「他谈到本源,说得弘广而通达,深远而博大:他谈到根基,可以说是和谐适宜,抵达最高境界了。虽然如此,他还是顺应变化而解消物累,他的道理无从竭尽,他的说法无迹可寻,茫茫然昧昧然,真是深不可测。」
像庄子这样的思想层次,惠施实在难以望其项背。于是,庄子把惠施比拟为他自己(石匠)表演绝技时的郢人(有如配角,甚至像是道具),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请勿小看这个配角,自从惠施死后,庄子因为少了他而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了。惠施再怎么不济事,也是个用功念书而口才便给的名家领袖。〈天下〉谈到惠施时,一开头就说:「惠施研究多种学问,他的著作多达五车。」
庄子在〈德充符〉明白警告过惠施,他说:「现在你放纵你的心神,消耗你的精力,倚着树干就高谈阔论,靠着桌子就闭目昏睡。自然给了你形体,你却以坚白之论到处张扬!」
惠施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应该是有用的人才,但是在庄子心目中,则他无异于「野猫与黄鼠狼」,「担任配角兼道具的郢人」,然后只知外放而不知内敛,以致白白消耗了可贵的生命。他的有用显然是得不偿失。
那么,学习庄子一定要变成像巨大的牦牛一样,连捕捉老鼠也办不到吗?当然不是如此。学习庄子,要分辨大用与小用,随时采取合宜的自处之道。
3.人生启发
谈到庄子的自处之道,在〈山木〉一开头就有一段非常具体的故事可供参考。其文大意如后:
庄子在山中行走时,看见一棵大树,枝叶十分茂盛,伐木的工人在树旁休息,却不砍伐这树。庄子问他什么缘 故,工人说:「这棵树没有任何用处。」庄子对弟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得以过完自然的寿命。」
庄子一行人从山里出来后,借住在朋友家中。朋友很高兴,吩咐童仆杀鹅来款待客人。童仆请示说:「一只鹅会叫,另一只不会叫,请问该杀哪一只?」主人说:「杀不会叫的那只。」
第二天,弟子请教庄子说:「昨天山中的树木,因为不成材得以过完自然的寿命;现在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老师打算如何自处呢?」
庄子笑着说:「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
由此可知,成材(有用)与不成材(无用),也许是外界所设的标准在决定,但是这两者同样可能遇到危险(被伐或被杀)。因此,与其计较有用或无用,不如分辨现实中的危险何在。譬如,庄子认为,儒家教人孝悌忠信,这固然是出于善意,但是如果只知固守这些「教条」或别人设定的规范,而无法先求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么结果可能是上当受骗或被人利用了。
一般研究庄子的学者,如苏东坡,大都认为〈盗跖〉这样的内容诋毁儒家太甚,必定是伪作的。但事实上,盗跖批评儒家推崇的贤者,也说出一番道理,不可一笔抹杀。尤其是底下一段。盗跖告诉孔子说:
「你用来劝说我的如果是鬼界的事,那么我无法知道真假;如果是人间的事,也不过如此罢了。这些都是我听过的。现在我来告诉你人的实况。眼睛想看到色彩,耳朵想听到声音,嘴巴想尝到味道,志气想得到满足。人生在世,上寿一百岁,中寿八十岁,下寿六十岁,除了病痛、死伤、忧患之外,其中开口欢笑的时刻,一个月里面也不过四、五天而已。」
他接着说:「天地的存在无穷无尽,人的生死却有时限;以有时限的身体,寄托于无穷尽的天地之间,匆促的情况无异于快马闪过空隙一样。凡是不能让自己的心思与情意觉得畅快,好好保养自己寿命的人,都不是通晓大道的人。」
由此可见,庄子立说的目的,不在质疑、批判或诋毁儒家所设定的道德理想,而在确定「本末轻重」,尤其要先认清客观的现实处境。如果人生只有「道德」二字,而道德又无法脱离既定的社会与人群,那么试问人活着还有多少乐趣?当然,儒家会认为行善最乐,因为那是出于真诚所引发的力量,是自我要求去行善的。但是,多少人在行善之时完全出于真诚之心呢?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行善只是考虑外在的利害:或者受到人群的压力,或者碍于名声与情面,或者只是随俗浮沉、虚应故事。
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经常「开口而笑」呢?为何不让自己「悦其志意、养其寿命」呢?为何不在选择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危与苦乐呢?庄子从不主张「损人利己」,他是希望我们善待自己,可以「安其天年」,这有什么不对呢?人人如此,天下又会有什么纷争呢?
不仅如此,「活着」本身并非庄子的目的。人与万物的差异,在于他有可能领悟「活着」有何意义。简单说来,人要活着而免于烦恼与痛苦,只有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觉悟」万物皆来自于道,最后也将回归于道。这种觉悟在人身上所引起的作用,就是肯定人的本性与禀赋来自于道,因而是无所欠缺的,只需善加保存即可。对外界的一切,可以「无待」;对内在的一切,则须珍惜。处于世间,尤其是乱世,难免危机四伏,那么我们要让自己「有用」还是「无用」呢?庄子选择处于二者之间,要视情况而定;我们不是也可以由此得到启发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