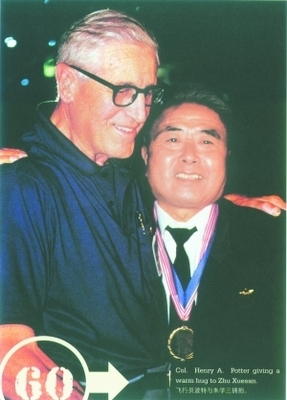那年,我读了李存葆的报告文学《祖槐》,记述的是明初朝廷策划的一次以山西洪洞大槐树为出发地的大移民行动。那是一次致使无数百姓家族离散、背井离乡的真实故事。2009年,我曾去到过大槐树遗址公园,同行者们纷纷进入设在公园内的好像是什么“认祖堂”的一处建筑里去,据说那里有几乎中国所有姓氏的祖先以及所有姓氏的来龙去脉。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进去认祖?我说我是蒙古族,我的祖先不在这里。
那么,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好像应该在辽宁义州,因为察哈尔部族就是从义州西迁而来的。然而,记得我的祖母曾告诉我说:咱们是布里亚特人。这样,我的祖先应该在贝加尔湖呀!到底在哪里?我一时说不明白。
我对我的家族史知之甚少。这大概与蒙古民族不兴家族谱不无关系吧?当然,蒙古族中的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人家受汉文化影响修家谱者也不在少数,但蒙古平民百姓就没有这个传统了,他们的家族史像民间文学一样,靠的是口耳相传、世代承接,没有碑刻,没有卷册。这样的传承,往往会因某一代或两代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原因就会断续,后辈就接不下去了。
我想,我的家族史一定是在某一代断了线的,只留下一句:“我们是布里亚特人”让后辈去猜测或寻根。然而,从我向上起码五代人没有去进行考察,更没有去寻根,好在他们还记着“我们是布里亚特人”。
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条大河,源源不断地流淌。每一个家族都是某一条大河的支流。家族谱就是对这些大河或支流的记录。读家族谱,就像在读郦道元的《水经注》一样,从一条支流去认识一条大河,进而认识一个水系。然而,如果某一条小小支流因断流而使你不能深入下去的时候,那是很扫兴的事。不过,也许有人会查阅史料,乃至实地勘察,力图找到断流之处,探清源头。
我想做探清源头的工作,但工程量太大了,无力实施。我只能做一些依据零散的资料进行推测的工作。首先,我假设自己是察哈尔人去探清这一条大河。布延斯沁汗之长孙、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孙林丹汗是蒙古元帝国走向衰败时出现的一代英雄,他率察哈尔部先是抗明,继而反清。1623年他兵败归化,西渡黄河,后客死青海。察哈尔所属地域被清军占领,部众降清。1675年,林丹汗之重孙布尔尼、罗卜藏兄弟又一次发动了反清战争。康熙帝调动科尔沁等部蒙古军队讨伐察哈尔部,布尔尼战死,罗卜藏因寡不敌众率残部再次降清。从此,康熙帝对察哈尔部有了戒心、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御笔下旨将察哈尔驻牧地义州收回“犁其牧地为牧场,归内务府太仆寺管辖,移其余众到宣化、大同边外驻牧”,并废止了察哈尔部王公札萨克旗制,改为总管旗制。就这样,康熙帝像抓起一把沙子随手一扬,察哈尔部众便散落在陌生广袤的宣化、大同边外了。

这是一次大流放,是一次部族大迁徙。一定也像洪洞大移民一样察哈尔部众背井离乡,扶老携幼,撵牛赶羊,成群结队地一直向西而去。这一路有多少故事、多少血泪是可以想象到的。
到达流放地后,我的祖先被划归在察哈尔八旗的镶蓝旗。该旗东界镶红旗,西界归化,南界山西大同,北界四子部落。广110里,袤160里。
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布里亚特人,那么,为什么会跟着察哈尔部西迁呢?
原来,康熙帝在大迁徙察哈尔部时,掺和进去了蒙古的其他部落民众,这种“掺沙子”的做法就是使原先的察哈尔部不再纯净,成分不再单一,向心力和凝聚力会大大减弱。康熙帝用心良苦啊!于是,我的家族就这样掺和进了察哈尔部中来了?
仔细查阅手头有限的资料,在镶蓝旗掺进来的“沙子”有来自新疆伊犁的“额拉得”姓氏,有来自呼盟的“巴尔虎”人,有来自兴安盟的“科尔通得”姓氏和“韩锦”姓氏,有来自青海海西的“和和塔娜”姓氏等,唯独没有“布里亚特”。
布里亚特民族从种族上是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其祖先原游牧于外贝加尔湖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与当地居民混合而形成现代的布里亚特人。1207年,成吉思汗命儿子术赤率军西征,布里亚特部遂成部属。到蒙古帝国时代,被蒙古化,说蒙古语。
1631年,俄罗斯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25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被完全压服,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一部分反抗俄国到底,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另外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国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巴尔虎人”,意思是虎一样的人。“巴尔虎”被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
原来“巴尔虎人”就是从俄国的统治下投向中国清朝的布里亚特人!康熙帝在流放察哈尔部时没有忘记他们,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也当作“沙子”掺进了西迁的队列,让他们也到大同边外驻牧去了。
这样说来,我大体上理清了我们家族的来龙去脉啦!
显然,我们这个家族早已融入了察哈尔部,从感情上说,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察哈尔人。但,要说“根”,我是布里亚特人!这就像一个被抱养的孩子,从感情上讲,他更愿意承认他是养父母的儿子,但,他的根在亲生父母那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