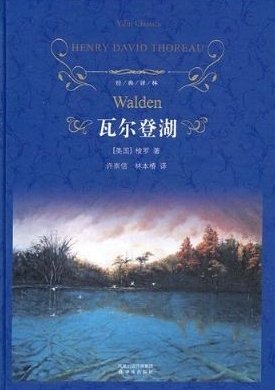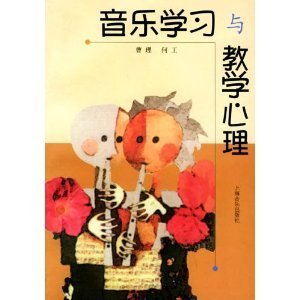丹娃摄于书房
我读加缪《局外人》
胡丹娃
1957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国作家阿兰贝·加缪,因其在小说《局外人》、《鼠疫》中“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种种问题”。
1999年,有一天我打开了《局外人》,开头的叙述就将我吸引。“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因为喜欢,我读了那个年代所能读到的他的全部作品,《局外人》读了不止一遍。就在昨天,我还在翻阅《局外人》,译林出版社1998年5月版,郭宏安的译本。坐在常去的肯德基快餐店里读,周围是现实中的嘈杂之音,窗外是默尔索受刑前最后一次看到的“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心是又一次的不平静,为局外人、荒诞人默尔索的命运。
这里,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局外人》。三十岁的默尔索爱母亲,因无暇照顾母亲,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他来到养老院。在母亲的棺材前,他没哭,也不想再看母亲一眼。他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他抽烟、喝咖啡,母亲刚下葬他就与女同事去游泳,看喜剧片,做爱,没有人不怀疑他对他母亲的感情。后来他因帮助人,稀里糊涂地成了杀人犯,本可减轻罪行,检察官却指控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法官对陪审团的先生们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默而索被判了死刑。小说全文在默尔索走向断头台前夕结束。
“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加缪这样为《局外人》概括主题。
小说里隐藏着一个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弃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惩处之列,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引自郭宏安译序《多余人?抑或理性人?》)
就是这个脑袋被人“要了去”的死囚墨而索,临刑前拒绝接待指导神甫,平静地在监舍里睡着了。醒来时,长夜将近。“很久以来,我第一想起了妈妈。妈妈该是感到了解脱。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面对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留下了最后的话——“我觉得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这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决别词隐喻的是觉醒了的默而索抛弃了世界,如此地,令人悲伤地。
加缪打动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委们,也一次次地打动了我。
每一次,都因《局外人》而感动,打动我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还有加缪本人。我看到一位伟大作家的非凡胆识,看到他如何在小说中体现“我反抗,故我在”的思想理念,并使这理念化为血液流淌在小说之中,使其呈现出“诗与思”的对话之美。整个小说是那么好读,即便是重读,也能一口气读下去。我看到他怎样在小说中展示荒诞的种种表现,看到他如何表现人与社会制度的冲突,表现人的弱小与无奈,生存处境与困顿,直至抵达他的小说乃至整个西方小说勤于表现的大主题——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样的关注,正是中国小说所缺乏的。
在我的阅读记忆里,“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词组清晰地出现,是在《局外人》里。仍然是郭宏安先生的序言中,他说道:《局外人》“以自身的独立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以如此地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晦涩的,还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可理喻的?人在这个世界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还是分裂矛盾的?……《局外人》的读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么模样,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他们不可能不记住他,不可能不在许多场合想到他。默而索像幽灵一样,在许多国家游荡,在许多读者的脑海里游荡。如果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际关系变了,那他们可以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法国或类似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个默而索……”
这段话帮助我很好地理解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今天,谈《局外人》,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书写“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范本。当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外延无法通过一部作品尽涵,但这部作品无疑使我看到了通向更多此类关系的路径。
生活中,我常常会想到“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关系无处不在,几乎只要出门,也几乎都不用出门,看到的全是这种关系——
挣扎在生存贫困线上的人们。
下岗。失业。待业。
猛涨的房价。拼死买房、卖房的人。
为房屋拆迁问题上访、自焚。
医疗费。
职场上变味的用人方式。暧昧的升迁。变相的剥削。
超级市场的出门“验章”。
大街上的磕磕碰碰。
频繁的车祸。
每一声电钻都可能引起的装修中的楼房倒塌。
地震。海啸。气候剧变可能引起的再一次全球生物大灭绝。
……
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脱人与世界之间的相生相克,而几乎所有的关系都与制度发生着联系,这制度既包含了法定的社会制度,也包含了大大小小的自产制度,其中无疑包含了黑暗的非合理、非人性的制度,更多是由人的伦理观念衍生出的基本法则,这些制度和法则足以将一个人送上“绞刑架”。“一旦你违反了社会的基本法则,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 个人的脑袋。’”就如同默而索。
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哪个国家都没法避开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明天就成为默而索。
今天,身处荒谬的世界,我们的反抗如加缪一样积极吗?
“在悲观中乐观地生存”是加缪的又一思想理念。在悲惨的生存世界中,我们乐观吗?
反抗?妥协?
觉醒?麻木?
默而索这个人物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居然敢在母亲棺材前不掉泪,居然敢在母亲棺材前抽烟、喝咖啡,这顶棺材简直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影射,影射的是制度,嘲讽的是常规。
小说中的默而索也是一个善良到糊涂的人,别人为了报复自己的女朋友,请他帮忙写信,他居然就写了,没料想日后成为他自己的“罪行”之一。别人请他帮忙收拾几个人,他居然就答应了,以至于稀里糊涂地杀了人,将自己送上绝境。总之,他除了无视常规无视制度,绝对是个好人。这个无视制度的好人最终被制度送上了绞刑架,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我在默而索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荒谬,即“人对人本身所散发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引自郭宏安译序),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自身的荒谬性。今天,我们面对自身的荒谬,是否如默而索一样漠然?
我们有自省精神吗?
2003年,我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活在福地》里写了一组人物,其中有位建筑设计师林知柏,写他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多么像一个局外人,这个人既有着无视常规的胆略,又有着漠视自身荒谬的麻木。在小说里,没人来要他的脑袋,但他的脑袋有读者来向我要,小说出版后,有多位读者对他的一系列行为表示了质疑,当然也有不少读者喜欢他。我在不知不觉中打造了一个局外人,也许是在表达我心中的感受——今天,局外人还很多,而且他就是我们的同类,他不但存在于他者中,也常常就是我们自己。这种局外人的根基很可能从我们年少时就种下了。例如,在遥远的年代里,我在父亲病重时还在忙自己的事。父亲死后,我也没有哭,哭声在我心里,没人听得见。没有人来要我的脑袋,但我早已向我自己要了我的脑袋。哦,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局外人》的原因之一。
今天,乐于表现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国小说,肯定应当不再仅是表现加缪式的反抗,还应当表现人与自身荒谬的对抗,体现出自省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们通常在西方作家、特别是德国作家作品中看到的。不仅应当看到制度中的“严酷的逻辑”,更应关注人被置于制度中的精神危机。小说家应当帮助人们看到自己在走向“诗意地安居”的路途中过好每一天的可能性。最后是小说的艺术问题。加缪在《局外人》中以一种平实的笔调、正常的叙述秩序完成了一次形而上的思考,形式上几乎没有任何“噱头”——有的人可能还会以为这是一本平淡的书而随手丢了它——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令阅者忘食的哲学意趣,那令人震撼的荒诞感。再次读《局外人》,坐在肯德基快餐店里,忘了时间,忘了面前的饮料,直到窗外“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来到。
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世界观、生命观总是解决得比一般作家要好,这两大“观”直接关系到他对世界、对人的认识、理解。当然,有时候,一个作家,或者一位思想家,其作品可能深刻,却不一定通达,此类人物在法国作家中就能找到几位。有的人最终没能摆脱死亡的诱惑,采取了自杀行为,此类作家的例子也不难举。加缪不是这样,他是深刻而通达的,他一生都在与荒谬反抗,“反抗——荒诞——幸福”可以构成他的一条生命线和创作线。要了解他的深刻与通达,还要去读他的其他作品,例如小说《鼠疫》、《堕落》,哲学笔记《西绪福斯的神话》、《反抗者》,等等,尤其是《西绪福斯的神话》,这篇哲学论文使加缪成为全世界青年的精神导师,也曾经是我、今天也依然是我所热爱的名篇之一。
加缪说:“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它对人提出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家每一次写作所经受的考验,都那么富有意义,包括对自身的考验。
长篇小说《局外人》/阿尔贝·加缪著/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5月版/定价:14.50元
2010年5月8日金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