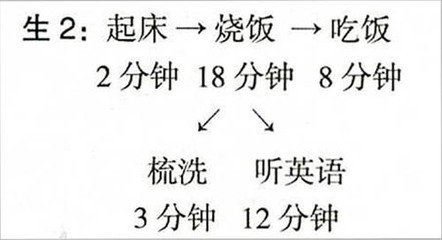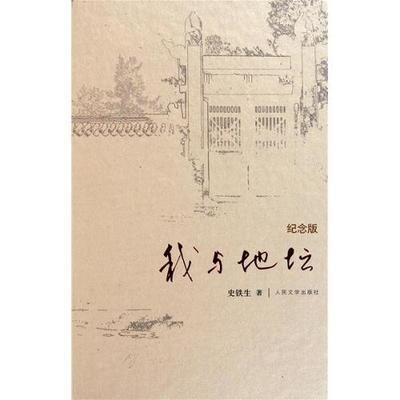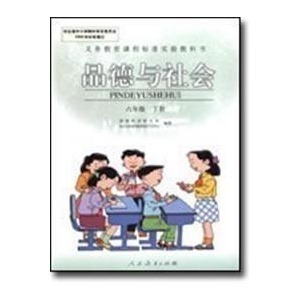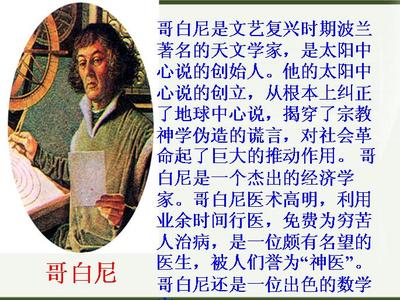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评论
作为一本典型的大部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内容浩博,结构庞大,讨论的问题众多且相互纠结,此外,语言的晦涩,用词的“新颖”,所有这些都给初学者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巨大困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存在与时间》的线索是格外清晰的,虽然重要的线索也绝不仅只一两条。我认为,《存在与时间》的结构性的大线索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对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和历史梳理,第二条是对人的生存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实际上,这两条线索是紧扣海德格尔写作此书的理论动机的:海德格尔希望,通过对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进行现象学的、也就是存在论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追问西方哲学最古老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地基,并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答案。虽然关于存在问题(“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最终没有建立起他的“一般存在论”,然而,本来是打算用作准备的“人的存在论”却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从以上两个结构性线索着眼,《存在与时间》作为一部不完整的存在论,却是一部完整的人的存在论。
从第二条,也就是相对完整的那条线索入手理解《存在与时间》,把这本书看作海德格尔对于人的生存经验的现象学分析,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集中在一对重要的概念之上:本真和非本真。本真和非本真这一对概念,以及海德格尔对于这两个概念所意指的两种不同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区分,无疑是贯穿全部人的存在论分析的关键线索。从这组概念出发,我们能够找到理解全书思想的切入点。那么,在《存在与时间》中,本真和非本真作为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在海德格尔看来,什么叫做本真的,什么叫做非本真的?
这对概念在全书正文部分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在第9节(前8节是导论)中,海德格尔指出了人这种存在者的特殊性,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性,对人的存在论分析才可能成为解答一般存在问题的准备。人的特殊性有两点:首先人的存在是“生存”,其次人的生存是“向来我属”的。人的“生存”主要是和“现成存在”相对立的,即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是什么,而是他如何去是。“向来我属”说的是,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他的生存,在任何时候都是属于他自己的。每个人都不可“被把捉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的样本或一员”。紧接着,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作为向来我属的生存,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中的,人的可能性并不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属性”,毋宁说人就是他的可能性。而这就意味着,人可能“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海德格尔说,选择了自身和获得自身,这种人的存在可能性、存在方式,就是生存的本真状态,相反,失去自身的存在可能性和存在方式,就是生存的非本真状态。这就是本真和非本真这对概念的意义,它们是用来规定人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在刚提出这对概念的时候,海德格尔就已经率先指出了本真和非本真之间的关系:首先,相比之下,本真状态是更为源始的,非本真状态唯有基于本真状态才是可能的,只有当人“就其本质而言可能是本真的存在者时……它才可能已经失去自身”;其次,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间不存在价值的高低,“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并不意味着‘较少’存在或‘较低’存在”,相反,人“首先和通常”就处于他的非本真状态中,受着非本真状态的规定,并且,这种人“首先和通常”所处的非本真状态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而不是消极的、欠批判的现象。可以说,《存在与时间》整本书的内容,就是把第8节所说的这种人的特殊“本质” 充分展开:详细阐释什么叫做选择了、获得了向来我属的生存的自己本身,什么叫做失去了这个自己本身,人如何在日常状态中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生存,同时又时刻具备着本真地实现自我的可能性。由此看来,本真和非本真这一对概念的确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然而,如果我们要沿着本真和非本真这组概念所指明的线索来理解《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话,那么,海德格尔赋予这组概念之区分的意义就必须首先得到理解。海德格尔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做出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它是一种道德的区分,还是一种纯粹现象的区分?正如上文提到的,海德格尔否认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具有任何道德意义。然而海德格尔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否认这一点?如果承认这个区分没有道德的含义,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它没有反映出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取舍和判断?价值取舍和判断不一定径直就是道德的,而非道德或超道德的价值取舍和判断毕竟也不同于绝对中立的、纯粹现象上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像区分两种颜色一样的区分。如果海德格尔对于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毕竟还是带着,甚至是不自觉地带着某种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又该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这个价值倾向?以上的所有问题都是本文要加以回答的。按照顺序,我们首先来看,海德格尔自己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是不包含任何道德意义的。
在提出人的“本质”之后,海德格尔详尽地呈现、解释了人的各种存在现象,分析了人的诸“存在论环节”,最终得出了能够把这些存在论环节统一起来的、“源始地给出了此在的存在整体”的“操心”现象。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各种存在现象和诸存在论环节都根源于操心现象,必须在操心的基础上理解每一个环节,才能将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因此,想要理解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我们就要首先理解什么叫操心。
根据海德格尔,操心是指人的这样一种规定性,即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 的存在。“先行于自身”所说的是人的“去存在”的可能性,人面向他的可能性而筹划自己。任何人在他“还未是……”的时候,总已经“可能是”那个他还未是的东西,并且他筹划着要去成为那个他“还未是”的东西。而“先行于自身”的“先”说的就是,人即使尚未“完成”他“去是”的筹划,甚至即使他永远地失败了,或永无希望“真正成为”他的某种可能性,他却毕竟时时刻刻“向这可能性的筹划着”,并因此就“是”他的可能性。很明显,先行说的是人的生存,人的选择和人的自由。
同时,海德格尔强调,人的自由不是“异想天开”和毫无约束的。根据操心,人在先行筹划着的同时就“已经在世界中了”,而这是人无法选择的。人无法选择他存不存在,因为他已经存在;人也无法选择他存在于怎样一个世界,因为他已经“被抛”给了他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被抛性”意味着,尽管人就是他的可能性,然而,他同时不得不承载着同样多的不可能性。他不可能不在他所在的时代,不可能不经历他经历着的历史,不可能不生于特定的身世,操劳特定的事情,和特定的人群共处、操持。已经在世界中的被抛性和先行于自身的生存性是相互纠缠的,人“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先行于自身”。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他的生存在于他的选择,然而时时刻刻有一个他无可选择的世界摆在他面前。
海德格尔称这种既自由又被决定的纠缠状态为“实际的生存”。人的实际性也就是他的被抛性,他总已经被抛给了一个实际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中,他有所筹划、有所选择地自由生存着。在我看来,“实际的生存”就是海德格尔眼中的人的“本质”。然而,把人的“本质”说成实际的生存,是不是漏掉了操心结构的最后一个环节——“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操心作为整体当然不容任何一个环节的遗漏,而如何看待最后一个环节,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要追问的,海德格尔的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的意义。
人的“本质”在于实际的生存,而人在去“是”他的本质的时候,可以以本真的方式去是,也可以以非本真的方式去是。人可以本真地存在,也可以非本真地存在。那么什么叫做本真地存在,什么叫做非本真地存在?
先行的生存性在于人是他的可能性,而人最极端的可能性是死亡。海德格尔说,死亡并非存在的终结,而是向着终结的存在。把死亡理解为存在的终结,是把死亡理解成了某种现成的现象,也就是非本真地理解死亡。本真的死亡不是现成现象,而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的死亡是“向死而存”。另外,死亡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每个人必须自己向着自己的死而存在。显然,被本真地理解的死亡和第8节所揭示的人的“本质”具有密切的关系,死亡现象直接显示出人的“本质”:“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因此,人要想本真地存在,就必须本真地理解和面对死亡,也就是要向着自己的死亡,将自己筹划到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中去。实际上,正是因为人具有死亡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正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向死而存的存在者,所以他才能够向着可能性筹划自身,才能够生存而不是仅仅现成存在。相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就是不去面对死亡,歪曲地理解死亡。海德格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让自己消散在周围来照面的事物中,让自己混迹于常人中,以逃避死亡,由此也逃避最本己的自身。消散于周围来照面的事物,就是从世界和世内存在者出发理解人,也就是把人理解为他所从事的、他为之操劳和奋斗的——“人做什么,他就是什么”。常人通过诱惑、安定,以及把人同他本真的死亡之畏相疏远,来逃避死亡。
被抛性作为人生存的实际性,也有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分。根据海德格尔,人的被抛性意味着他“始终不是另一种可能性”。人不仅对于他已经被抛入的那个世界,对于他的时代和历史、身世和伙伴无法加以选择,而且,在人能够自由选择之处,他也毕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把不曾也不能选择其它可能性这回事承担起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被抛性,勇敢地直面这种被抛性,承负被抛性而筹划着生存,就是本真地作为实际性而生存。海德格尔称这种对被抛性的本真的理解和面对为“良知”。海德格尔进一步说,人的良知告诉他,他是有“罪责”的存在。实际上,这里说的罪责,就是得到了本真的理解的被抛性,海德格尔又称其为“不性”,也就是人的生存本质上的有限性。相反,非本真地面对被抛性,和非本真地面对生存性一样,是消散于世内存在者,逃逸到常人那里去。无良知的常人不去看生存之根本的有限和罪责,而是事先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本分的、什么是认可或不认可之事、什么是允许人成功或不成功之事,等等。总之,常人营造出一种“平均状态”,从而在本真的被抛性面前逃避。
综上所述,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于实际的生存,那么,本真的生存性就是向着死亡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筹划自身,而本真的实际性就是直面被抛的罪责。关于向死而存的先行与直面罪责的良知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专门用了一节加以讨论。简单地说,罪责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死亡。罪责是人的生存的不性或有限性,而人最根本的有限性就是死亡,“本真地想到死便是在生存上达乎透彻的愿有良知”。
由此看来,即使把人的“本质”看作生存性和实际性的统一,我们也不会遗漏操心结构的任何一个环节。这是因为,这一本质的本真的实现方式是向死而存的先行和直面罪责的良知的统一,而“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也就是人的沉沦,只不过是这一本质的非本真的实现方式:消散于世界和常人,逃避本真的死亡和本真的罪责。当然并不是说,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就不是生存性和实际性的统一,实际上它仍基于这个统一,只不过它以一种非本真地方式实现了这个统一,并“首先和通常”规定着人的存在方式。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都是人源始的存在方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论上的。比如,在面对死亡的态度方面,正如我们提到的,处于非本真状态中的人,即常人,往往把人同他对死亡的本真畏惧相疏离:“对于公众意见来说,‘想到死’就已经算胆小多惧,算此在的不可靠和阴暗的遁世。常人不让畏死的勇气浮现”。这种疏离当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那种“不怕死的精神”倒是最符合道德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面对死亡的非本真态度,其问题不在于道德上的不可取,而在于生存论层次上不够本真:它把死亡理解为某种现成的状态,从而把对死亡之“畏”和对世内存在者的“怕”相混淆,进而用一种看似优越的“淡漠的教养”使人疏离于“其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能在”。可以说,本真和非本真之分不涉及道德对错,只关乎境界高低。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在什么意义上区分本真的存在和非本真的存在,并且何以这种区分是不含有任何道德含义的。人的本质在于实际性和生存性的统一,并且人总是以要么本真,要么非本真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统一的。无论是本真的存在方式,还是非本真的存在方式,都是人独特的、源始的存在方式,无论人处于本真状态中,还是像他首先和通常的那样处于非本真状态中,总之他都不是某种现成的存在者。我们已经说过,操心现象是理解人的所有生存论环节的基础。生存性必须在操心的基础上加以理解,正因为人本质上是操心的存在,“先行”是操心结构的重要环节,他才可能向死而行,才可能筹划自身,进而他才可能或本真地“先行进入向死而存的筹划”,或非本真地逃避这种筹划而沉沦;实际性必须在操心的基础上加以理解,正是基于操心固有的“已经在世界中的”环节,正是因为人总是有世界的人而非“无世界”的主体,人才有他的被抛和罪责,进而才可能或本真地直面他的被抛性和罪责,或非本真地无视良知。总之,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唯有基于操心的结构整体才是可以理解的,而本真和非本真之所以不具有任何善恶两别的伦理学意义,其根源正是在于它们都根植于同一个操心。
理解了海德格尔划分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的意义,以及他何以能够否认这个区分有任何道德含义,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即使承认这个区分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然而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它没有反映出任何意义上的价值取舍?首先,有必要在更为广义的层面上理解这里说的“价值取舍”。虽然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价值,但是价值并非只有伦理意义,一种价值取舍所取的不一定就是伦理上善的和道德的,所舍的也不一定就是恶的和不道德的,毋宁说伦理道德在更深处奠基于根本性的价值取舍。进一步讲,价值取舍不仅仅是在善恶之外或之前规定着善恶的,它不仅事关“善”的世界,而且还是“真”和“美”的源头。一个文明所追求的“至善”,对她而言的“真实”,她心目中的“绝美”,无不奠基于那个根源性的价值取舍。她在源头处的取舍决定了,她将选择什么东西为善,认为什么东西为真,接受什么东西为美。从这个意义上讲,纵使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强调其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的中立性,他也逃不出某些根本性的取舍和倾向。这些取舍和倾向决定了,他的现象学将把何种人类生存经验作为不证自明的“现象”,他会赋予这种生存经验以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他能够为处于这种生存经验中的人们指出什么样的出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他的被抛性。而我们要追问的,就是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这一问题上面,被抛的海德格尔如何被抛。
前面已经提到,如何看待操心结构的第三个环节,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本真和非本真区分是非常关键的。实际上,人的非本真状态就表现为操心结构的第三个环节:人“作为已经寓于世内存在者的”的存在,首先和通常消散于周围来照面的、他所操劳的世界,并在常人中沉沦。我们说人的“本质”是实际的生存,这样是不是把“三位一体”的操心结构人为地割裂了,只取其前两个环节作为人的“本质”而忽略了第三个环节呢?海德格尔不是说人的本质在于操心结构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不容割裂的吗?必须承认,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实际性和生存性的统一,把操心结构的第三个环节,即人的沉沦,说成人的“本质”的非本真的实现方式,这里的确有割裂操心的结构整体之嫌。然而,这一结论却不是完全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本意的,相反却是他自己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试问,虽然人之为人,不可一刻不是实际的生存(否则他就沦为了现成存在),然而,人是否可以不是“寓于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呢?他是否可以不是常人、并未沉沦呢?根据海德格尔,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人“首先和通常”是沉沦着的常人,但是经由“良知”的呼唤和“愿有良知”的决心,人毕竟能够从常人那里“回到”最本己的自身中去,作为最本真的自己承担起生存的罪责,先行面对死亡而筹划。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人应该这样做。在这个意义上,操心结构的第三个环节就大可不必是人的“本质”,它只是人首先和通常所处的非本真状态。若非要把常人的沉沦也说成是人的“本质”,就无法面对人竟能完全不沉沦、完全不是常人的事实。倘若海德格尔毕竟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沉沦就不是人的“本质”。当然,这并不是说,沉沦着的常人就没有人的“本质”了,而是说,作为常人的沉沦,这种存在方式确实不是人的“本质”的本真的实现方式,在这种非本真状态中,人丧失了他自己。至此,海德格尔的取舍和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间,前者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
然而,对于我们追问的东西来说,这个结论是不是过于贫瘠了?试问又有哪个文明不把本真状态取为人生更高的境界,把非本真状态舍为人生的日常平均状态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区分本真和非本真的思维方式本身。沿着这种二元区分的思维方式前进,必然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本性的思维方式问题,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即使承认任何文明所追求的都是本真状态,然而对于不同的文明来说,什么才是她的本真状态,她要以什么方式实现她的本真状态?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实现他的本真状态的关键是向死先行、愿有良知和承负罪责,而这三件事说的不过是一个意思:人要回到那个“无所关联”的、孤独的自我。死亡所显示的就是这个孤独的自我。作为人最极端的可能性,死亡规定人的存在为能在的生存,从而人才可能先行地筹划自身;作为人生在世最根本的有限性,死亡是人最根本的被抛性:生存是被抛入死的生存,以此为基础,人才是有其“处境”的,才是有其不性和罪责的。如此这般的死亡着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在对死亡的畏惧中,人看到他只能自己承担他的死,他看到在这令他成为人的死亡中,他是绝对孤独的。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就是要求人首先回到这样一个绝对孤独的自我那里去,进入最本真的“展开状态”,再以本真的现身领会重新投入于世界的操劳,投入于和他人的共处。这时候,世界和共处将“改变样式……领会着操劳着向上手事物的存在和操持着共他人的存在现在都从其最本己的能本身存在方面得以规定了”,这时候,人就摆脱了常人的沉沦,进入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根据海德格尔,本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回到孤独的自我。那么,这种绝对孤独、无所关联的“自我”是人类至始至终的、普遍自明的“现象”吗?在古代世界,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这种绝对孤独和无所关联的自我都是很难成立的。在古希腊,人唯有在城邦政治中才有其作为人的存在,所以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古希腊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恰恰不是无所关联的存在,而是城邦人、政治人的有所关联的存在。古希腊人的死亡,要放在他的本真存在,也就是城邦政治生活中才能得到理解,而不是相反,通过死亡来理解他的本真存在。在古代中国,不仅同样不存在如此一个绝对孤独和无所关联的自我,而且,恰恰是被海德格尔贬为非本真的常人和日常的“常”,在古代中国,却可能是最为本真的存在。当然,礼法伦常的常肯定不同于沉沦的常人的常,然而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不必那么直接和执着地谈论死亡,更不必回归孤独的自我,只要以某种特定的理路构建这个常,以某种特定的境界面对这个常,就能够把这个常从常人之常上升到伦常之常,并且就在这个常自身之中安顿最高的价值。至于本来在城邦政治中有所关联、并不孤独的古代西方人,如何由于这种政治在内外两个方向上的瓦解——在外,大帝国政治逐渐取代了小城邦政治,而在内,一种高于政治的理念接替了政治对于至善的追求,从而使政治成为相对的——而变成无所关联和孤独的现代西方人,以及中国人如何也被卷入这个巨大的孤独化进程,这些都是远远超出了本文任务的课题。本文只需指出,海德格尔的绝对孤独、无所关联的自我,以及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我去实现的那种本真的生存状态,不过是现代西方,确切地说,也就是基督教的西方的产物。而之所以我们中国人在阅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也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经验上的共鸣,首先是因为,它的绝大部分内容毕竟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经验,其次,在最深刻和关键之处,这种共鸣恰恰基于我们已经是而且不得不是现代人——现代不是“后基督教时代”,相反,它是“基督教的现代”。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虽然已经是,而且不得不是现代人,然而我们毕竟曾经是,从而注定永远是中国人。海德格尔所描绘的人类生存经验绝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适用于中国人的生存感觉,即便是现代中国人,也必然带着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国人独有的心性结构和思维方式。因此,阅读海德格尔的意义绝不在于照搬他的思想来解释我们自身,而是在于参考他的思想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而这就要求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存经验在什么意义,以及何种程度上能够符合于《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在何处又绝不并且绝对不可能和它相一致。
然而,把海德格尔的思想说成是基督教的产物,把他说成基督教思想家,这是不是恰好违背了海德格尔的原意?尤其是考虑到,实际上,海德格尔处处表明他和神学的区别,以及他和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差异。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对于传统基督教思想来说,海德格尔是反思者和批判者,但是作为基督教文明的成员,他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批判注定是基督教文明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我们也绝非简单地把海德格尔说成基督教思想家、神学家,把他的思想同传统神学进行牵强的比附。毋宁说,我们的意见在于,即便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想要反思和批判传统基督教思想和神学思想对于人的解说,但是在很多关键之处,他不得不接受传统基督教思想的思维方式、基本前提和基本观念。海德格尔对于孤独的体验和解释,将死亡作为根本性的罪责,以及对于良知和决心的讨论,都带着强烈的基督教色彩。
诸如此类的实例在《存在与时间》中比比皆是,但是最为根本性的有两点,第一,海德格尔赋予日常此在的地位和传统基督教对于尘世生活的看法之间的关系。虽然,海德格尔力图化解传统基督教思想在尘世生活和灵魂救赎之间做出的、带着强烈的价值倾向的二元划分,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的超验神性来保障这种此岸和彼岸的对立,而人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存在方式,都只在操心的在世之中。然而,海德格尔还是做出了自己的二元划分,只不过所依循的标准不再是神圣和世俗的对立,而是基于此岸的尘世生活的操心在世的人的生存的本真和非本真。在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无神论和世俗化的反叛,然而这种划分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圣俗之分的思维方式是连贯一致的,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海德格尔还是把日常的尘世生活定为终究需要被超越的“非本真状态”,而把此在看作在“本质上”并不日常的、孤独的和无所关联的存在。只有在一个上帝面前,无论这个上帝是自觉地摆在明处,还是不自觉地藏在暗处,人才可能如此本真地孤独。
第二,海德格尔极其深刻地洞察到了时间性和人的存在意义之间的关联,并且从时间性出发对人的生存论分析进行了重新梳理。简单地说,操心结构中的“先行”环节所对应的时间性是未来,“被抛”环节是过去,“沉沦”环节是现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将来、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现成的时间分段,而是使得生存得以可能的源始时间性的各环节。现成的时间性和源始的时间性区别何在?时间性问题和本真与非本真的区分之意义问题又有什么联系?
现成的时间性是以“现在”为基础的,它是“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过去”是曾经存在但已经不在的现在,“将来”是尚未存在但终将到来的现在,只有“现在”本身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时间本身是无始无终的,立足于每一个现在向前后两头望去,过去永远无穷无尽,而将来永远遥遥无期。源始的时间性则不是这种线性的时间之流,而是“出离自身的绽出”。首先,根据操心的结构,人是生存着的,是先行筹划着的,而先行就是先行到某种“将来”的可能性中去,筹划就是面向某种“将来”的筹划。“将来”的时间性和先行的生存性之间的联系究竟何在?人的生存性说的是,人之为人不在于他已经具有的某种现成本质,而在于他如何去是他的“本质”,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根据如下情况才是可能的:人不是任何一种现成的他自身,他总是面向可能性筹划着自身,并不断让自身来到自身。海德格尔说,将来就是让自身来到自身中的那个“来”。“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这就是将来的源始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讲,将来现象是人的生存性的前提。
相应的,源始的过去现象,海德格尔又称之为“曾在”,则是人的被抛性的前提。人的被抛性说的是,人总已经不得不处于一定的世界和处境中了。而这种“总已经”却不能在现成的意义上理解为,人曾经是如此这般的,相反要理解为,人是他的如此这般的曾经。曾在和将来是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的,从而人才可能是生存性和实际性的统一。本真的生存状态是背负着罪责、先行筹划着的存在,也就是说“此在本真地从将来而是曾在”。
最后,现在的时间性即“当前”,所对应的就是沉沦,即非本真状态。与传统的现成时间性观念相反,海德格尔认为,现在非但不是构成时间性的源始现象,反而是最不源始的时间性。对于人来说,仅当他同时是他的将来和曾在,仅当他承负着罪责的同时面向他的可能性先行筹划着自身,他才能够“活在现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
在“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的结构中,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统一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源始的时间性,他称之为“绽出”。正是时间性的绽出,使得操心的结构整体得以可能。显然,在这一时间性结构中,虽然在任何时候,将来、曾在和当前作为统一的整体都是“同时绽出”的,然而从理路的逻辑上讲,将来和曾在的时间性要比当前的时间性更为源始,也就是更为本真。而与曾在相比,将来显示自身为“在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绽出的统一性中拥有优先地位”,是“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
由此看来,海德格尔之前的生存论分析,以及他所得出的操心结构中的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自有其时间性的根据。落实在时间性的层面,人的本真和非本真状态之分就是在时间性的绽出中,将来、曾在和当前之分。而海德格尔之所以赋予将来的时间性以最源始、最本真的地位,与基督教文明的根本性的时间感是深刻相关的。“将来”这个时间性维度,无论在古希腊世界还是在古代中国世界,都从未被上升到这么高的规定性的地位。没有基督教思想带来的超时间的神的理念,以及以末日审判这种神话语言的方式所道出的“期待式”的时间存在方式,“将来”这一时间维度对于起码的思维方式和根源性的生存感觉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将来为本真的基督教时间感和中国古人尚古的时间感的差别是明显的,虽然具体的理路之分绝不简单。在西方文明内部,奥古斯丁应该是第一个集中讨论时间问题的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分析和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之间应该存在意义深刻的联系和区别。然而无论是中西方时间感的对比,还是对西方思想史上,奥古斯丁到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之流变的讨论,都远远超出了笔者的学术功底,文本只能放弃这个课题。虽然要真的说清楚海德格尔的本真和非本真的区分,理解海德格尔在什么意义上是对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反思和反叛,在什么意义上与之一脉相承,时间问题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本文只能满足于草草地勾画出海德格尔在本真和非本真之区分这个问题上透露出的基督教思想背景,而这就是所谓海德格尔自己的被抛性。当然,一个被抛的海德格尔绝不因此就不那么深刻,实际上,越是能够背负被抛性,就越是能够把自己被抛入的那种可能性挖掘得更深。一个作为基督教的一丘之貉的海德格尔是肤浅的,一个作为基督教的反思者的海德格尔是更高的,一个重又作为基督教文明的承负者的海德格尔才是最深的。而如何承负起我们自己的被抛性,并在这种承负中展开我们更深的、更为本己的可能性,也许这才是海德格尔留给我们的永恒的问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