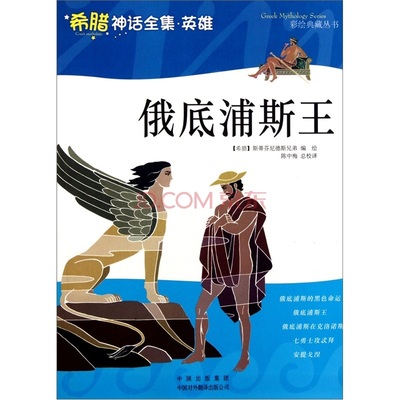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
及其作者辨伪综析
〔一〕
赵福坛
摘要本文主要综述和分析自1995年以来有人否认《二十四诗品》作者司空图的辨伪争论,认为陈尚君、汪涌豪提出《二十四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证据尚欠充足。张健指出《诗品》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是错误的”,言之有据。但他说《二十四诗品》作者可能是元人虞集似乎无充足理由可以肯定,而虞侍所编的《虞侍书诗法》只收《二十四诗品》中的十六品。由此可见,元明有关《诗法》、《一指》之类的书,并非某作者所撰着,而是用以指导学诗的编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所说的一段话,可证《二十四诗品》出自司空图之手。
关键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诗家一指;作者;辨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鸣集
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下简称《诗品》)经久不息,过去对《诗品》的作者毫无怀疑。1995年上海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二教授因辑唐代诗文检索典籍时发现:自司空图以后到明末长达700多年间,无人提及司空图着《诗品》,故认为《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诗品》的作者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下简称《一指》),明末作伪者从《一指》中析出二十四品,托名司空图。
陈、汪教授对《诗品》作者的否定,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陈尚君教授于1995年8月19日在上海《作家报》发表《〈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文章否定《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一指》。1995年9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陈、汪在会上宣读了其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全文3万字),成为大会专题讨论的主要内容。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张健博士的《诗家一指的产生年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并把论文带到江西南昌在大会上发言,指出《诗品》作者怀悦及《诗品》出自《一指》的错误。
1996年3月16日,《文汇报》又披露了陈、汪二人的观点,而且当时又在浙江新昌召开的国际唐代文学年会上展开讨论,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转载,1996年第1期《中国古籍研究》刊载陈、汪合写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其观点影响逐日扩大,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1996年,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了汪泓先生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和汪涌豪先生的《〈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的异趣》,前者客观地综述了陈、汪二人的观点及南昌研讨会上各家的看法,后者从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去否定司空图撰写《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1996年,《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载祖保泉、陶礼天先生合写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对陈、汪所论进行反驳。
1997年,《中国诗学》第五辑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专栏:载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之我见》;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王步高《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汪涌豪《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张伯伟《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张健《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蒋寅《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束景南《王希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考辨》;陈尚君《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这些文章各有见解,各有所据,把辨伪推向深入,无疑是好事。
这些文章的发表,以及研讨会的研究,对《诗品》作者“真伪”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期待这场辨伪早日有个可信的结论。我80年代初曾涉猎过司空图《诗品》,并着有《诗品新释》(1996年花城出版社),后又撰写过几篇论文,但由于地处南方,图书数据欠缺,其研究应是肤浅的。但作为《诗品》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对于《诗品》的内涵及其作者的真伪,这里应说点什么?况又参加过1995年和1997年两届分别在南昌、桂林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故为斯文,请教大方之家。
一、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

在陈、汪教授未提出《诗品》作者不是唐代司空图,而是明代怀悦之前,所有研究《诗品》的学者,尚未提及对《诗品》作者的怀疑。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陈国球先生所收录的专辑《司空图研究论着目录》(1931—1986),共132项,在132项论着中,标题均以司空图或司空表圣题为《诗品》作者,从未有人对《诗品》作者司空图提出怀疑。这些作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学者。众所周知1986年以后近10年间对《诗品》的研究,亦未有人提出异议。直到1995年陈、汪二人提出对《诗品》作者的质疑,才引起对司空图《诗品》作者真伪的争论。
陈、汪认为《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代的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所编的《诗家一指》。他们的立论根据是:
1、司空图传世诗文中,无着此书之迹,今人据其中有诗论赏诗之说,谓《诗品》为其晚年之作,仅属揣度;
2、自五代至元末,司空图传记有7种,如《旧唐书·文苑传》等或不云著作,或仅记文,而《本事诗》、《北梦琐言》等60多种唐宋笔记只载其事,“无及《诗品》者”;
3、今存宋元公私杂志,如《崇文总目》等,均载其文集,“不及是书”。明人编《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仍无其迹。其见书志着录,始于清中叶《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
4、因辑唐代诗文,于宋元类书、地志、诗话、笔记等曾予通检,“未见引录之迹”。近年苏州、河南编纂《全唐五代诗》,检宋元旧籍逾千种,凡引唐诗制卡,“仍未见此书片言只语”;
5、明高木秉《唐诗品汇》和胡震亨《唐音戊签》司空图小传,“仍不及《诗品》”,后者及秀振宜《全唐诗稿本》,“均不载此书”。杨慎《升庵诗话》有司空图论书一节,所举仅其论诗二书及《诗赋》,胡应麟《诗薮》和胡震亨《唐人葵签》均曾列所知全部“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李山乔《评诗格》以降,逾20种,“均不及司空图《诗品》”,《葵签》及许学夷《诗源辨体》均述及司空图诗说,“亦不涉《诗品》”,明代典籍浩瀚,无以通检,然以上诸位皆博洽之士,于唐诗研究颇深,“足证其时《诗品》尚未出世”。
6,苏拭所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陈、汪认为:这里所说“二十四韵”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所举的二十四联诗,而不是指“二十四诗品。
(以上六点均摘引自陈、汪先生提交1995年南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因篇幅关系摘引时稍加删减,致歉)
从上面陈、汪先生否定《诗品》作者司空图的六点依据看,二人的确做了大量的考检工作,其得出的结果应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将这六点概括起来一句话是:从晚唐至明的大量的有关记载司空图及其作品的史籍中,均未见有记载司空图《诗品》的文字,或者说“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因此,可断《诗品》在司空图死后700多年间尚未出世,因而《诗品》不是司空图所著;而最早刊载《诗品》是明人怀悦的《诗家一指》,因而《诗品》作者是怀悦。
从上述检索看,这些检索有些是作者因辑唐代诗文而亲自检索的,有些是借助他人检索的结果来作左证的,我认为这都有相当充足的根据的,但问题是这些检索是否齐全?是否有千检之一漏之嫌呢?对此,似乎难于回答。如果单从史籍无及《诗品》,就把《诗品》从司空图手中分出来,这未免有点过急或武断。因此,在南昌的学术讨论会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就提出异议,他说:“《魏文帝诗格》书名是伪的,材料是唐代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宋元没有人提及是否就一定是伪书,这个结论不是唯一的。”(转引自汪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下同)江西师范大学陈良运教授亦举出论据说:“有些书,如汉代的《焦氏易林》、班固的《汉书》及隋唐以前的文献都无记载的,但在《隋书经籍志》上又出现,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部《崔氏易林》在旧、新《唐书》和《宋史》都有书目,与《崔氏易林》并存,但到元代又不见了。《诗品》的左证,很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国文化之迷。(同上引)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提出另一疑点,“明末清初各大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袁枚等均不怀疑《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唐人诗格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唯此一编真出图手。’他们是否都是对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误解所致,也值得怀疑。《诗家一指》有很多版本,并被收入《格致丛书》不是难见之书,他们不会都没有看见”。
我认为这三位教授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们觉得在所检索的史籍中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就不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难于肯定。陈、汪教授用反推理方法来否定《诗品》作者,若在绝对的大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在尚未确定,甚至有疏漏的前提下就不一定准确了。比如说,他们所检索过的史籍是否齐全?即使自认齐全,是否有失佚呢?或者说,除了与司空图《诗品》有关的典籍外,其它非有关的典籍,是否有记载的版本也已失传而“未见引录”呢?这种种可能是存在的。这些前提还未弄明白之前,而单凭“不及是书”,就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历史古远,很多典籍在流传过程散失或版本失传,这是常有之事,一些典籍在其它版本中能找到,但在一些版本也永远找不到了,这也是事实。陈良运教授所举的例子,就是个说明。张少康教授提出的,钱、王诸学者确认《诗品》作者是司空图,不会因看了苏轼的话而误导,而恰恰相反,他们不会不见《一指》的。只因为《一指》这一类的书是编集,是教人学写诗的,属于教材,编集者很多,所收集的材料有些标明来源,有些则不标出处,这样你引我引,你编我编,广泛流传,作者就不为人注目了。钱、王诸学者只标司空图是《诗品》作者而无视《一指》中的《诗品》著作权,不无道理的。
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三十二种,其中有《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在出版说明中该社特别说明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据为原书,由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提供底本。同时又说明宋蜀唐人集丛刊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区的刻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蜀刻本六十家”之说,认为此与北图藏本为同一刻本。可证明,这个版本是宋人刻本,也是至今流传下来的较早版本。但这个版本只有十卷,有文无诗,标《一鸣集》并有司空图自序。序说:“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前集,庶警子孙耳。”司空图序中说得清清楚楚,集中有诗,而为什么只有文无诗呢?显然是“序”不对“文”的。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宋蜀唐人刻本《司空表圣文集》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故在跋中加以说明之。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这段文字,我把它抄录下来,供参考。其原文如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说:“蜀本有杂着,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所说蜀本当即为此《司空表圣文集》。全书计收杂着八卷,碑二卷,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录相同。但四库馆臣误以为此书即是《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一鸣集》,实际上二书有所不同。《四库表圣文集》前有司空图自序,其云:“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孙耳。”然而本书所收皆文,并无诗论,故序言显然非为此书而作。由此可见《司空表圣文集》并非出自唐时的旧本,而是宋人编辑而成。《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记录的《一鸣集》,内容均为三十卷,乃是司空图诗文的合集。《司空表圣文集》的序文,即或取自这个旧本。可是三十集的旧本流传绝少,宋代就已罕见。元代辛文房所编《唐才子传》说“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似乎他当时还曾见过全本。至明代以后,三十卷《一鸣集》再不见有人提及,恐怕早已湮没不存了。《直斋诗论解题》还记有《司空表圣文集》诗集十卷,可惜也未见流传下来。
这段跋文说得很清楚,《一鸣集》有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还有宋以前的唐编《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本。《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郡斋当时志》记录的《一鸣集》三十卷诗文合集,就是全本。
又据史载,雕版印刷术始于唐,盛于宋,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很发达,以浙本、蜀本、建本为最佳。宋蜀刻本是指成都、眉山地区之刻本。宋蜀刻本唐人集有60家之说。宋人陈振孙《直斋诗论解题》记有“蜀刻六十家”。但现传至今只有23家 。这23家是宋蜀所刻,由北宋起至南宋止,所刻唐人文、诗集有:骆宾王、李白、王维、孟浩然、孟东野、刘子房、刘梦得……李长吉、司空图、韩愈、柳宗元等。已散佚了不少,60家只剩下23家。在这宋蜀刻本中《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只有文而无诗。而且所用的序言是《一鸣集》三十卷的序。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宋蜀人刻《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时,已找不到《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全本,或已散佚部分,而采用三十卷本的序言,抑或有意将三十卷本文、诗和诗格分开刊行而采用同一序言呢?从陈振孙着录看,后者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看到“自有诗十卷,别行。”即有《司空表圣诗集》十卷,另刊行于世。那么诗格虽然没有说怎么行世,但其分别刊刻可见。
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收《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作者小传谓“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今存五卷。”说明胡氏还见到《一鸣集》三十卷本,但已残缺不全,诗集已散佚,只残留五卷了。诗格部分他没有提及,但不等于没有存在,正如他没有提及诗论文,但不等于没有诗论文一样。而且诗格已为人袭用成习,提与不提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张少康教授在前文中认为:“(《诗品》)作为二十四首四言诗存在于诗集中的话,那书志中没有着录,有关司空图传记中没有提及,也是并不奇怪的。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司空图诗文集今存已不全,《一鸣集》的真实面貌已见不到了。(此点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卷第449页已说到)。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三十卷本《一鸣集》和十卷本《文集》(蜀本无诗)、十卷本《诗集》并存。三十卷本《一鸣集》明代尚见着录,但是否还存全本,则目前尚无法断定。诗集至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为五卷本已是残存之本,散佚了近半,文集恐怕也难有完壁。明代前期是否还有十卷本诗集也已不可考。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三十卷本《一鸣集》原本或十卷本《诗集》中有《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以上引述和意见,我只提醒读者,研究司空图著作,首先要研究其行世版本,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说及就等于其作品不存在。
〔下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