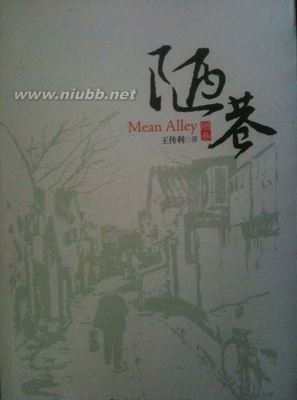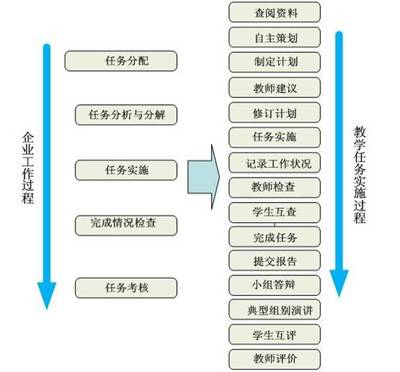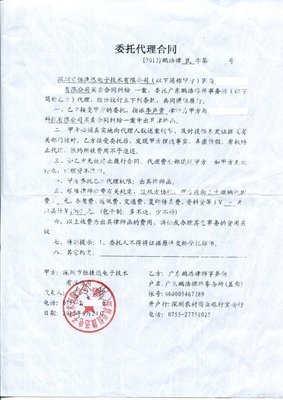金圣叹(公元1608-1661年)本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明亡以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批书时用的笔名,江苏吴县人。明诸生,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平素为人“倜傥高奇”,“好评论奇书小说”,曾将《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称施耐庵为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之后的第五才子,表现出离经叛道的思想。
金圣叹的思想存在着深刻复杂的矛盾。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下层地主阶级家庭,又适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动乱年代,个人的困苦生活和卑微地位,使他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但佛道两家对他也有深刻的影响。这使他时而愤世疾俗、关心时事,时而又自觉浮生若梦,怪诞不羁。他同情人民的遭遇,大声疾呼“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唱经堂语录纂》卷二),但又坚决反对“犯上作乱”,不准人民自己“出头”。这些思想矛盾,鲜明体现在他对《水浒》的评论上。
金圣叹在他三十岁左右时着手评点《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等书。他把在他以前流行的《忠义水浒全传》七十一回以后的内容全部删去,使故事在梁山大聚义结束,并加写了一个卢俊义惊梦的结尾,还去掉了书名上的“忠义”二字,这就抹去了宋江等人投降打方腊的历史。同时他还在批语中强调宋江企盼招安的言论为权作之词,从而使《水浒》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都面貌一新,成为在人民群众中最流行的一个版本。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主要反映在他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的序和批语,以及《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对《水浒》的态度,总的来说是矛盾的。他自幼喜读《水浒》,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但对《水浒》中鼓吹“犯上作乱”的内容,却又明确加以否定。他评点《水浒》的最初动机,就是因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但由于个人阅历的加深,生活处境的不堪,使他从对《水浒》艺术成就的欣赏,逐渐发展到对其中批判现实、同情人民的内容产生共鸣。他的基本立场虽然是反对人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但他又认识到黑暗政治必然引起“官逼民反”、“破国亡家”,因而在对《水浒》的具体评点中,表现出某些进步观点。
首先,金圣叹肯定了《水浒》暴露黑暗、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他在《楔子》总批中说∶
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言?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其次,金圣叹指出宋江等人的“犯上作乱”,是在无道之世中被高俅之辈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为此,他特意把高俅出场移作第一回,并在这一回的总批中指出∶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再次,金圣叹在对《水浒》的具体评点中,对受迫害人民及其某些反抗斗争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赞美。如第十回写林冲感叹自己被高俅陷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得不上梁山落草,金圣叹批道∶“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第十四回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都吃尽了,又要盘缠打发他。”金圣叹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这表明金圣叹对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是抱有同情和好感的。《楔子》批“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一语道:“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他虽然在根本立场上对人民起义持反对态度,但在具体批语中又时常情不自禁地对水浒英雄的反抗言行表示赞扬。如对他十分讨厌的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一事,他在批语中就多次赞美道:“突兀淋漓之极!”“突兀淋漓之笔!”后来,宋江被捕下狱,李逵说:“吟了反诗,打甚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金圣叹批道:“骇人语!快绝,快绝!”这些大胆的言论,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基于把《水浒》看作包有“一切书之法”的认识,金圣叹对《水浒》的艺术成就评价最高,评点时也下力最多。首先,他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塑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读第五才子书法》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他分析《水浒》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点说∶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金圣叹在分析《水浒》人物的个性化特点的同时,又注意到个别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共性特征。如他评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中张顺的形象时就说:“直写出豪杰朋友神理。”正因为《水浒》中的许多人物既有其鲜明的个性,又体现了生活中某一类人的共性,所以金圣叹指出,《水浒》塑造人物达到了“任凭提起一箇,都似旧时熟识”的境界。这话与近代俄国别林斯基所谓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十分相似,说明金圣叹已接触到艺术创作中的典型问题。
对于《水浒传》能把人物性格写得“同而不同”的原因,金圣叹也做了较为精细的分析。第二十五回的总评把武松同鲁达、林冲、杨志三个军官出身的英雄作了比较,指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之形状与如鲁如林如杨之结束也。”也就是说,《水浒》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是从内心到外貌,全面地写出人物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是由于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造成的。如他说∶“写杨志便有旧家子弟体,便有官体。”评论“东郭比武”一节说:“每一等人有一等人身份,如梁中书看呆了,是文官身份;众军官喝采,是个众官身份;军士们便说出许多话,是众人身份。”这些分析,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还着重分析了作品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高超技巧。《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如第十回写林冲请求王伦准其入伙,金圣叹批道∶“林冲语。须知此……虽非世间龌龊人语,然定非鲁达、李逵声口;故写林冲另是一样笔墨。”第五十五回写时迁盗甲偷听徐宁夫妇、使女间的谈话,金评曰:“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是家常语、是恩爱语,是主人语,是使女语,是楼上语,是寒夜语,是当家语,是贪睡语,句句中间有眼,两头有棱,不只死写几句而已。”从中可见金圣叹对《水浒》人物语言研究的细致与深入。
其次,金圣叹通过《水浒》评点,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技巧。如对《水浒》的结构布局作了细致的研究,归纳出十几种他所谓的“文法”,象“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等。他总结的这些“文法”,虽不免有拘泥穿凿的成分,但不少是深得作者之艺术匠心的,是他对中国小说美学的卓越贡献。

金圣叹在对《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注意研究创作过程的奥秘。他在肯定现实生活第一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澄怀格物”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说:
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这里所谓“格物”,就是接触外界事物,这种“格物”的前提是“澄怀”,也就是不带成见,不存杂念,这样才能正确地、客观地“格物”。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物理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琢磨,最终达到了然于胸,才能下笔自如,抒写尽致。
“澄怀格物”是创作的基础,但强调“澄怀格物”不等于要求照搬生活。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这段话,可谓说出了文学创作中艺术虚构的特点。但金圣叹又指出,“因文生事”不等于胡编乱造,艺术虚构也要遵循生活的逻辑,这就是所谓“因缘生法”。第五十五回的总评说∶
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无印板做文字法。因缘生法,一切具足。
“因缘”本是佛教术语,梵文Hetupratyaya的意译。《俱舍论》卷六曰∶“因缘合,诸法即生。”“因”指对生成结果起主要直接作用的条件,“缘”指起辅助间接作用的条件。二者合成一词,指得以形成事物、引起认识和造成“业报”等现象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金圣叹在这里借用这一术语,说明作家创作要依据人物性格与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去描写人物和事件,写出人物行为与事件发展的必然性。这对于提醒作家在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合理地进行想象和虚构,是有指导意义的。
金圣叹在探讨小说创作的奥秘时,还指出作家塑造人 物必须“动心”,即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合到所描写的人物身上,设身处地地体会人物的精神个性,才能使笔下人物活现于纸上。第五十五回的总批说:
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
这些意见,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其启发和参考价值。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