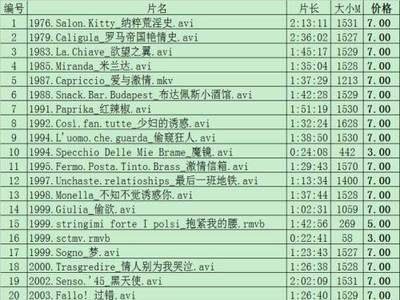博伊斯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点:
首先是博伊斯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
时势造英雄,世间万象总都逃不出一些最简单的逻辑,行动,然后回应,之后是责任,因,然后果,果又成了因。因为战争,因为破坏、屠杀,历史判德国有罪,所以德国需要忏悔,因为战败,亲人离去,流离失所,民众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所以需要抚慰。先有了某种需要,接着一个叫博伊斯的人发现了这种以国家、民族和人之名义进行忏悔的需要,承担了抚慰战后德国民族创伤责任。因为背负了如此之多,约瑟夫·博伊斯成为了大师博伊斯。
博伊斯对自己个人成长经历中诸因素的应用要比之前所有艺术家更直接,他的艺术活动中也更多的反应了个人的成长经验。这些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深层分析他的成长,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艺术实践。

以时间脉络来说(很有可能因受资料的有限性而产生误读),首先要提及的是博伊斯出生在小城Kleve,从小亲近大自然。关于大自然的记忆,如牧羊的经历,对动植物的研究后来直接成为了艺术活动中的要素。我不想简单地说是自然把博伊斯培养成一个有丰富内心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人,然后由热爱这片土地到热爱自己的民族。万事万物在遵循大的规律的同时,其自身且与外界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洞悉的复杂的逻辑链条。然而我相信博伊斯对自然的情感必然是这逻辑链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博伊斯在与动植物的交流中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构成了之后博伊斯艺术活动中对自然,对动物进行解读、应用的前提,而且这一点也秉承了德国艺术家一贯亲近自然的传统。对传统的继承使得博伊斯更容易受到国家的认可,也让他激烈的行为有了某种文化上的延续。
出生并成长在天主教家庭虽然没能让博伊斯一心侍奉上帝,但是一些宗教的伦理,情感等还是对博伊斯产生了影响。博伊斯对自然由热爱到膜拜,还有后期体现在他作品中的神秘感应该与这种宗教家庭背景脱不了关系。
博伊斯中学时曾经离家出走,外出跟随一个马戏团四处游荡,这使我们认识到博伊斯性格中的一些东西。我没有看到过有什么资料说明他出走时的想法,但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中学生来说,出走都不是小事。这似乎是废话,但我想我们应该从中理解到一些如叛逆,热血,冒险,单纯等性情的强度。
战争的经验是任何人在讨论博伊斯时不能不提及的。因为在战争中他向长官学习动、植物学,到柏林大学旁听人类学,参加人类学讨论小组,这些知识的积累是博伊斯战后艺术的主要基础。虽然博伊斯对战争没什么兴趣,但作为一个德国青年,他还是尽职尽责,曾五次负伤。说因为博伊斯没有直接面对敌人或杀戮对象而对战争的残酷性不重视。战争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概念,稍有知觉的人在看到满地废墟都会想到残杀和流离失所,像种族灭绝这种概念听起来就骇人听闻,直到现在到讨论不断,更别说对博伊斯来说事件的制造者就是自己的国家。上面提到了博伊斯爱自然,受天主教家庭背景影响,想想就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不到战争的邪恶呢。
就是因为博伊斯深切的体会到了战争的邪恶,明白战争伤害了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所有人。他才不愿在战后回忆这些,因为要远离恶魔,并不需要了解恶魔的长相,只是靠近天使就行了。所以博伊斯投身到治愈战争伤害的工作中去,投身到远离战争的工作中去。正如在一次行为表演中他用刀划破了自己的手,却拿出绷带为刀包扎。他是要包住伤害的根源,还是在暗示自己的艺术理想——治愈战后德国,或许二者都有。
在博伊斯的经历中最有传奇性的当属他所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后被鞑靼人救下故事了。博伊斯自己的回忆,当时鞑靼人往他的身上涂抹油脂,再用毛毯包住他的身体使他得以存活,看到草原上飞奔的兔子让他觉得兔子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在这暗指一种生命力)。这些生命的体验构成了博伊斯作品中多数的符号。据我判断,鞑靼人的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博伊斯的敌我双方对立的意识。由于原来的博伊斯心中就没有多少诸如民族仇恨之类的想法(以目前所掌握的信息看),所以与鞑靼人友好相处的经历让博伊斯更自然的回避了战争中的对立性,他所关注的问题直接接近了战争的根源。
战后博伊斯从艺的经历已经不能向上面这样简单的分析,可以说他之后的生活就是一件庞大的艺术品,这在后文会做进一步分析。
其次是博伊斯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他超越了绝大多数艺术家成就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博伊斯成长学习的轨迹是这样的:小时候接受传统宗教伦理观,崇拜自然并醉心于研究动植物——中学时期因厌学跟马戏团出走,冒险精神得到张扬——17岁时看到威廉·勒姆步鲁克的雕塑,感受到强烈的认同,开始认为艺术要反映现实,不能逃离到生活之外。整个中学阶段理科和音乐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参军,长官是狂热的生物爱好者,在教授博伊斯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带博伊斯去柏林大学听生物、哲学、人类学等课程,接触人类学群体。开始崇拜斯坦纳的学说——成为德军飞行员,被击落成为俘虏,战后返回德国进入艺术学院学习,之后走上艺术家的道路。
我们可以在上面的整理中看到博伊斯在从事艺术工作前所接触的学科的广泛性。这使艺术语言不再成为博伊斯的唯一视角,让他跳出艺术之外重新审视艺术。
我想也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艺术,才有可能不受旧的艺术规则的限制,提出“社会雕塑”、“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些主张并一再扩大艺术的概念。
博伊斯曾说过自己之所以从事艺术工作是因为艺术为他提供了更好的表达方式。这让我们可以很肯定博伊斯对艺术的选择是极有主动性的与目的性的。当清醒地认识到目的在于表达时,所有艺术规则便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与其说波伊斯是在扩大艺术的概念,还不如说他在把自己的行为冠以艺术的名义。
我是从不相信世上有天才这种东西的。所有的现象必然有因。博伊斯的“天才创造”无非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艺术的方法是什么。他有自己的目的,艺术只是他选择去往目的地的道路,仅此而已。
第三点是一个人对社会形势、历史事件的敏感性,是博伊斯异于其他艺术家的使命感。
敏感与直觉有关,与悟性有关,与文化有关。直觉与悟性人人都有,想来面对战争如此激烈的社会现实,人人的直觉与悟性都足以被激活。文化不是人人有,只有有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更系统的理解事件,把自己的敏感应用在更准确的、更有价值的位置。博伊斯正是这样。
是不是要背负社会,历史的使命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然而要背负这些使命是博伊斯艺术的选择。在上世纪后期,照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更多的是关注艺术内部的问题没错。可总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来考虑艺术语言之外,艺术存在目的的问题,这些人将会被艺术史记住。
抛开艺术,就战后德国的社会现实,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因为身为战败国的德国,要面对的不仅是废墟、不仅是家庭的破裂和国家的衰败,更重要的是由于战败,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消失殆尽。要有人出来重新建构德国的战后精神,而博伊斯选择了以艺术的方式。
这第三点与第二点关于关注角度的问题密不可分,但我把它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非常可贵,这是极强的理性能力加真性情的结果。
清理博伊斯的目标与理想:
第一,民族的救赎与治疗,
在1983年一次记者会上博伊斯答记者的提问中提到自己的艺术是治疗战后德国的精神。
博伊斯医生多数的作品是围绕民族的救赎与治疗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博伊斯针对的问题并不具体指向战争某方面具体的范畴。博伊斯声称自己经历了整个灾难,他所针对的问题是包括文明对人的侵蚀,战争的根源,战争本身及战后问题这些灾难的整体。
(上图为《向死兔子解释艺术》行为过程中的图片,中图为《毛毯西装》,下图为《本质3号》)
《向死兔子解释艺术》是博伊斯1965年的一件行为作品。博伊斯在一个大玻璃柜中手捧一只死兔子喃喃自语,头上抹着蜂蜜和金箔。
好多人认为博伊斯宁愿与死兔子交流也不会选择人类,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博伊斯认为蜂蜜是能自己产生热量的,是暖性的流动的。蜂巢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式,而蜂蜜就是这种社会模式的血液。有此看来,发蜂蜜抹在头上象征作者思考的问题至少是一个社会的问题。金箔则象征着高贵与永恒,高贵代表着作品中所探讨问题的神圣性,而永恒象征着这种思考穿越了生死。兔子又是源于作者自身的经验,原来是生命力的代表,在这里成了死亡,成了需要被救赎者。行为过程中,作者与死兔子都处在玻璃柜中,暗示作者也非普通的生的状态,或许是在说穿越一切困难的决心,或许是寄希望于以某种神秘的宗教感来感召观众。当然,行为的核心还是解释艺术,这是作者为拯救社会业已死亡的生命力所找到的方法。这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对博伊斯毕生工作解释。
1970年的作品《毛毯西装》是较早单纯的,直接的反映博伊斯救赎理念的作品之一。毛毯的应用无疑与战争中被鞑靼人所救,用毛毯包裹他,使他的生命力得到保存的经验有关。
在1970年博伊斯重提这个经验无疑是要保住某种东西。这时战争早已结束35年,虽然德国在7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国力得到恢复,但民族精神上的创伤还未恢复,这一点精神的微弱喘息需要保护,正如当年博伊斯的生命。而之所以选择西装,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在众多服饰中西装最能代表西方主流的,核心的文化。为这个文化量身打造的外衣,自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它。
1979年的作品《本质3号》,几堆堆积物,每堆111张毛毯加一张铜板,放置于走廊之中。
我不太清楚111这个数字的含义。铜在博伊斯的作品中一直扮演一种激进的,能获得某种能量的元素。而毛毯是典型的绝缘体,起保护的作用。这件作品较之前的《毛毯西装》有更明确的指向性。我认为这种指向更多地倾向于青年,革命精神和文化中的激进成分。视觉上如此大量的堆积让人感受到一种历史责任的负重感,同时又有一些决心的东西掺杂在里面。
第二,关于重建欧洲价值观
早年博伊斯很少提及这个话题,但在1978年的一次由当时欧洲最顶尖艺术家的集会上,大家公开讨论了这个内容。其核心就是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欧洲应该找回战前世界文化核心的地位。当时这次集会引起了欧洲思想界,艺术界甚至政界很大的重视。事后有人把集会的内容整理出版,名为《重建大教堂》。
博伊斯的一些作品中隐约透露出了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不懈。著名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中,作者有意回避美国现代文明。虽然表面看不出对美国的轻视,但构思中透漏出来的对美国文化的抵制情绪显而易见。如今在网上还能找到博伊斯当年在美国演讲和答记者问时的视频。其中的博伊斯显得那么高傲,在美国人面前是那么不可一世。
博伊斯的艺术
博伊斯走上艺术家的道路是非常具有主动性的。他期待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改造社会。“让人们达到一种自由是我艺术的目的,因此,艺术对我来说是科学的自由。”"Tomake people free is the aim of art, therefore art for me is thescience of freedom." 这足以说明博伊斯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之于博伊斯只是一种手段。
装置作品
博伊斯的装置作品大概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借物言志。博伊斯亲口提到过:“人们可以用物质材料来表达某种非凡的事物,某种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的事物。整个世界依赖于一块块物质材料的布局安排。依赖于事物所在的位置,场所的格局,往地理上讲,在于事物与其他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布局安排。就这么简单,不必搬弄内容含义。要是能让自己处于这种……被其他事物观照的状态里,自然而然地沉浸到这种状态里……一个人能通过种种形式,创造某种事物。”
博伊斯多数装置作品都属于这一范畴。这类装置从作者的一个想法出发,借由对一种或几种有对应意义的物质处理,让这些物质的形态代替语言,起到表达的作用。这类作品更多的立足于语言,是将语言转换为三维的形式。最典型的作品要数1963——1964年的《油脂椅子系列》,1974年的《导向力》、《本质系列》,1985年的《危机形势》。
以《危机形势》为例。具博伊斯的解释,房间中出现的钢琴象征着艺术。它并不指向于某种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是代表一种整体的,包含社会中每个人的艺术概念。覆盖房间内部墙壁的是一卷卷毛毡,这里的毛毡也是一如既往的传达着保护的概念。博伊斯在这件作品中把两种意义拼装在一起,构成了自己的表达。
第二类装置作品可以说成是博伊斯行为的遗迹,从概念上接近文物的作用。这类中的典型作品是1983年的《二十世纪的终结》,1985年的《皇宫盛宴系列》,还有1997年由学生为他完成的《动物脂》。
这类作品或许有些与第一类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核心不是拼装一种概念,而是要完成某种记录。
以《皇宫盛宴系列》为例,这件作品就是为了记录博伊斯的艺术思想和行为,虽然作品中出现了不少象征物,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拼装某种概念,而是重现博伊斯的艺术记忆和制造博伊斯本人的“在场”,这作品成为了博伊斯艺术行为的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面两种类型作品中出现的象征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博伊斯生活经验的挪用。博伊斯曾经亲口解释过“我没有用这些毛毡制品去代表鞑靼人的什么东西,或者像其他人所说得那样,代表什么集中营心情。灰色的毡子……当然发挥了作用,那是材料本身带来的感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生活经验之于博伊斯只是素材,基于自己所要表达概念的选择才是博伊斯使用材料的准则。
行为作品
博伊斯的行为作品总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原因可能有两点:1德国艺术自古以来倾向于一种神秘自然主义。大家都熟知的《指环王》最初的故事原型就诞生在古代德国。这种神秘自然主义中往往就天然的带有一些神话和原始宗教的色彩。博伊斯在自己的行为中继承了德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作品更具民族性。2博伊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他产生感染。他的行为中有很强的说教和仪式的成分。
《向死兔子解释艺术》是博伊斯代表作之一,它打破了生死的界限。博伊斯在其中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巫师,他的意识穿越了生死的阻隔。《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中博伊斯则更像是一个牧羊人,在遥远的美洲布道。
《我爱美国,美国爱我》是博伊斯一生在美国完成的唯一作品。博伊斯到美国的全部行程不接触美国现代文明,只与代表美洲原始文化的一只小狼在房间里待了一周。博伊斯试图以这个作品来阐释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起初因为互不了解产生隔阂。在把他们强行放置到一个空间中并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处与交流后,两者最终达到一种和谐。在向外界解释这个让作品时,博伊斯说道:“我只专注在野狼身上,自我鼓励及保护,完全只看狼不看美国。”
这件作品中同样出现了博伊斯经常使用的有象征性的物质。如欧亚棒,毛毯。其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如每天十五份美国报纸,代表现代的文明。整个过程中博伊斯对报纸是不予理会的。野狼对报纸的态度更可想而知。
为什么博伊斯抵制现代美国呢,我们不能不想到前面提到过的重建欧洲价值观核心地位的问题。还有博伊斯一贯反对的现代消费文明。至于对野狼所代表的美洲原始文明,博伊斯曾经提到过“人类,肯定必须和他之下的东西接触:动物、植物、自然,和在他之上的天使及灵。”在《我爱美国,美国爱我》中,战后七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轻视、兴趣等复杂情绪展露无疑。
社会行为作为一种艺术
博伊斯的社会行为所讨论的问题是远远超出艺术范畴的,但这些行为被博伊斯冠以艺术的名义,博伊斯把这称为“扩大的艺术概念”。
首先不能不提的是博伊斯的教育工作。他把教育看成是自己理念的实践,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对方案的事施。早在二战之前博伊斯就接触了人类学家斯坦纳的思想,可以说,博伊斯的许多工作就是对于斯坦纳学说的实践。斯坦纳是人智学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提倡用人的本性、心灵感觉和独立于感官的纯思维与理论解释生活。他认为人人天生都具有创造力,都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潜力。博伊斯把这些观点应用于自己的艺术,也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也并不是说人人就真的是艺术家,而是指当任何人参与到艺术行为中来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艺术家。也就是人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
正是基于这种坚定的理念,博伊斯对传统的学院教育模式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接收一切想跟他学习艺术的人。当时在他任教的杜赛道夫艺术学院不断的“兴风作浪”。1966年先是成立学生党,1971年又成立“直接民主组织”。在这期间,他带领自己的学生走上街头,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在学校里大搞政治讨论。1972年他严重超额接收学生。当时通常一名教授带十几名学生,而博伊斯的学生数则超过了四百人。有七十几名学生被学校教务处拒收,博伊斯便带领学生占领了学校教务处,并抢占了教室。这一行为最终导致学校报警,博伊斯被赶出学校,取消教授职务。之后经过近两年的两年的官司,博伊斯复职。复制之后的博伊斯向外界解释道回到学校对他来说有这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这对他而言远不止是一份工作,而是自己理念的一种实践。
这事件的发生使博伊斯在欧洲家喻户晓,他的抗争也得到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及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这之后,博伊斯开始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工作中去。
返校后的博伊斯不被允许参与教学,但保留了工作室。他在这里重新招集学生讨论艺术、政治话题,并在不久后提出了“社会雕塑”这一概念。在之后一次名为“革命是我们”的展览中,博伊斯指出“唯有艺术是革命的”,“唯有革命性的工具是一种整体的艺术观念,他同样提出一种科学新观念的诞生。”
“社会雕塑”这个概念彻底打破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为了实现这个概念,博伊斯在自己的工作室中成立了“自由国际大学”,虽然只有一间屋,一个秘书,一台电脑,但博伊斯的政治工作就此开始了。
之后博伊斯做了越来越多的与政治有关的作品。1979年,他甚至代表绿党参加了大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