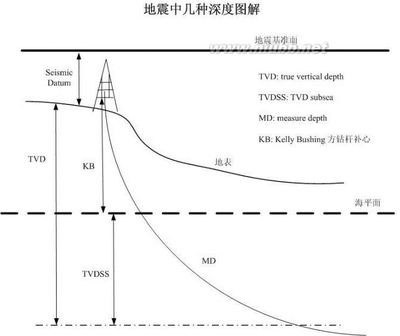摘自:简繁著《沧海》三部曲之三《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十五章:传统的叛徒,世俗的罪人。470页-497页
杨之光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我回中国访问夏伊乔,准备闭关写书的消息,打电话约我过去谈谈。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现代绘画秋季大展”之后,杨之光为他女儿给我的电视专访节目打电话拆台,向我郑重道过歉。而后,我们成了朋友。
杨之光是徐悲鸿的真传弟子。他用中国的毛笔、水墨、宣纸,画西方写实的明暗素描,在中国画界算是一种创造。虽然这种西方意味浓厚的中国画,在真正的西方境遇并不是很好,但是谈起来,杨之光还是难掩对徐悲鸿及其写实主义艺术教育的崇敬。杨之光告诉我,不久前他刚从北京回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为他联合举办了“杨之光艺术回顾展”和“杨之光艺术研讨会”,收藏了他的全部展品,出版了“杨之光艺术研究论文集”。徐悲鸿的长子徐伯阳专程从香港去北京参加他的研讨会。会上,徐伯阳拍着桌子大骂刘海粟无耻,说手里握有许多刘海粟的罪证,会陆陆续续发表出来向世人揭露。
我问:“都是些什么罪证?”
杨之光说:“我不方便代他说。我建议你直接与徐伯阳联系,请他把这些材料提供给你。你写的是历史,应该兼听两方面的说词。”
我接受了杨之光的建议,立即给徐伯阳写了信,与杨之光的推荐信一起,寄去了香港。
徐伯阳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回了信:
简繁先生:
收到你的信,使我很感意外,因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假如你想做第二个李志绥,那么你可以精心去写,而且写出的回忆录,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不会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差。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得那么理智。刘海粟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已经是客观事实,现在要你突然面对它,正视它,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的。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我这里目前存有三部分关于刘海粟的资料:
一,揭露刘海粟青年时代,在上海进入周湘办的“布景画传习所”时,诱奸周湘家的丫环,迷奸周湘的妻子,勾结青、红帮,砸他的学校,毒打他至重伤……这份材料是周湘的外孙根据他外祖母亲口讲的经过写成的(约一万多字)。
二,我父亲早年揭露刘海粟展出的一些油画是抄袭别人的,然后在画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
三,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区的汉奸报上刊登有关刘海粟举行个人画展的消息,上海的日本军、政界上层人士都出席祝贺。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豋出的汉奸名单,第六名是刘海粟。
以上资料目前有一家典藏杂志表示愿意刊登。假如真的发表了,那么我就寄一本给你。假如没有发表,我就将这三部分资料影印一份给你。
关于刘海粟的为人和一生的所作所为,许多老画家是清楚的,也是瞧不起的。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大力的吹捧他。论人品和画品,这个人都站不住,所以我担心你在写回忆录时,可能会很痛苦。但作为一个爱国的、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肩膀上挑着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一付沉重的担子,我们一定要还历史一本来面貌。希望你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预祝你成功。
祝工作顺利
代问杨之光兄好!
徐 伯 阳96.4.10.
我给徐伯阳回信,告诉他,我很希望得到他的资料,因为我和他一样,希望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而且是全面的交待。
徐伯阳立即把资料给我寄来了。他附信说:
简繁先生:
来信收到。看完信后,我就将我手头所有的有关刘海粟的全部资料影印了一份,现随信寄给你。关于刘海粟陷害周湘的事,周湘生前曾写了两封信给我父亲,谈到许多实际事实。可惜这两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西纠”红卫兵抄继母家时被销毁了。例如继母告诉我,当时刘海粟控告周湘败坏他的名誉,要周湘赔偿,结果法院判了周湘要赔偿1000银圆给刘海粟。周湘根本没有钱,只得卖了学校中的一切,勉强凑够了这笔钱。周湘就带着妻女到乡下隐居,不久就死了。
给你的一些照片中,旁边有些墨笔字,那都是父亲的笔迹。因父亲早年对刘海粟的抄袭行为极为愤慨。
希望这些资料能使你对刘海粟此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在写他这个人时更接近他的“真我”。
预祝回忆录顺利完成!
徐 伯 阳 96.4.25.
徐伯阳寄来的材料里,有6张照片。其中4张是把刘海粟的画、文与别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分别是:
一,法国印象派大师塞尚的油画《静物》和刘海粟的油画《静物》;
二,欧洲19世纪的油画作品《狮子》和刘海粟的国画作品《狮子》;
三,法国女画家的油画《马》和刘海粟的油画《马》;
四,中国清朝画家郑板桥的《自序》和刘海粟的《自序》。
看了照片应该承认,刘海粟的画与文,的确都与别人的太相像了。徐悲鸿在塞尚和法国女画家的两张照片边上,各写了一句话:
上面是塞尚的原作,下面是刘海粟盗窃抄袭之作,他还编一套欺人鬼话。
上面是法国19世纪女动物画家所作,下面是刘海粟抄袭之作,竟将白马三只脚抄在一条线上,连远近距离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另外两张照片分别是,1943年11月30日上海《申报》和1945年8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的剪报,可能是因为翻拍再翻拍的缘故,字迹已经很模糊。
《申报》是一则关于刘海粟画展的消息。标题是“刘海粟画展昨预展盛况”,副标题是“到中日各界三百余人,今日起开始正式展览”。消息说:
当代名画家刘海粟氏,近以其名作国画西画百余件,定自今日起至12月11日止,假座成都路静安寺路口中国画苑公开展览,其友人张一鹏林康侯等为刘氏举行预展,特于昨日下午4时至6时,在中国画苑茶点招待各界参观,到有盟邦方面东亚同文会副会长津田中将,海军武官府长近藤少将,盐田大尉,陆军部川本大佐,日大使馆奥村课长,岩井书记官,华中振兴公司高岛总裁,冈部顾问等,中国方面周作民,朱朴之,陈绍妫,赵晋卿,吴湖帆,丁伯雄,潘仰尧,周化人,柳雨生等三百余人,极一时之盛,当由张一鹏,林康侯,陈彬龢等,暨刘海粟亲自招待,巡回观摩,风趣横生,至6时散会,今日起正式展览,欢迎各界欣赏。
《新华日报》就是一直听说的“文化汉奸名录”,辑录了16个人,刘海粟排在第六,被徐伯阳用红笔圈出来:
刘海粟,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的利欲诱引,下了水,公然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名录后的括号里有一句话:
待续。欢迎读者供给材料。
然后有一段以编者名义写的“致读者”:
今天凌照济先生来函,很好地补充了我们21日所发表的汉奸名录,这不但读者感激,也是全国同胞都极注意的。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我们是不允许这些出卖祖国的丑物漏网,也不允许谁对他们伸出“援助”的手的。胜利来了,彻底的人民的胜利还要我们努力,我们盼望读者多给我们下列各类性质的稿件……
徐伯阳还寄给我四份文稿。其中两份是其继母廖静文手书的材料及其附件,另外两份是“周湘孙子”写给刘海粟的信和揭发刘海粟的材料。
廖静文的第一份手稿内容是:
请看有关刘海粟的一份调查材料。这只是刘海粟的劣行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上海沦陷时,中国人民都在浴血抗战,国难深重。梅兰芳留起胡子不唱戏,程砚秋扛起锄头去种地,而刘海粟是怎样的呢?他在上海举行画展,邀请了一大批汉奸和日寇,他“亲自招待”,“风趣横生”。当时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上海人民在凄风苦雨中排队买不到粮食,而刘海粟和夏伊乔却举行有中国和日本来宾数百人参加的盛大婚礼,大排盛宴。稍有爱国心的人都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丧失民族气节是可耻的,但刘海粟至今仍在吹嘘他坚贞不屈。为了端正美术界的风气,我深感有责任再一次将真相写出来,让大家了解。
廖 静 文 1985年5月1日
廖静文随手稿,附了一份打印的揭发材料。材料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刘海粟的政治历史问题”,有四个小节,其中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分别照录《申报》刊登的关于刘海粟画展的消息,以及《新华日报》辑录的“文化汉奸名录”。其它的内容是:
3,据江苏省文联的一份材料揭发:“抗日战争期间,刘海粟和汪伪、日寇勾勾搭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刘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由日本军用飞机把他接回上海,后又用飞机把他爱人接回来,在上海结婚时,由汉奸陈彬龢做主婚人,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有大汉奸特务丁默村、林康侯等,日本军政方面有川本、奥村、高岛等。后来他爱人生小孩时,第二天清早,日本军的清水中将,特地送小孩衣服道喜。”
4,解放前出版的《美术年鉴》上,载有刘海粟1945年11月赠给蒋经国的画,题字为“风雨飘摇同一慨,中流砥柱仗新人”,“此时此画奉赠经国先生”。(见影印件二,刘海粟奉赠蒋经国的画)
(二)关于刘海粟抄袭剽窃问题
美术界对刘海粟某些画中存在着抄袭剽窃问题早有传闻。仅从《刘海粟国画》和《刘海粟油画》两本画集中看,刘的某些作品,其造型、构图确实来自别人的作品。油画集自序的文字显然抄自郑板桥(见影印件四、五、六、七)。
影印件四,上图:塞尚原作。下图:刘海粟画。刘海粟在画上附文:《静物》1922年8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在家没有出去,六龄的儿子,买了一串紫葡萄,四只红柿子,一只莱阳梨,笑嘻嘻的献给我看;放在我桌上一个白石膏型的左右,半面恰巧又衬着一张新作的晚景;他无意给我这般对象,我那里肯放过他去。我就拿他画了!
影印件五,上图:欧洲油画原作。下图:刘海粟画。
影印件六,上图:郑燮自序。下图:刘海粟自序。
影印件七,法国女画家原作。下图:刘海粟画。
廖静文在材料中附的照片,除了刘海粟赠送给蒋经国的画之外,与徐伯阳寄给我的是一样的。
廖静文的第二份手稿比较长,并且加了标题《去伪存真》:
今年10月,我赴香港参加纪念悲鸿百周年诞辰活动,有人示我《大成》262期所载石楠文:《一场波及画坛半个世纪的笔战》。文中涉及的许多事,我是知情者、目睹者,我感到有责任来澄清一些历史事实。
1953年,悲鸿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期间,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将召开之前,他要求谒见周恩来总理,我陪同前往。我在《徐悲鸿一生》的长篇传记中记述这一事实时写道:“周总理在他那间朴素的会客室里和悲鸿亲切交谈。悲鸿谈了美术界的情况,谈了国画的发展、继承和借鉴问题,也谈到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悲鸿又谈到画家的品格问题,他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应为人师表,不能因为有画家的头衔而品德上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时期,画家的民族气节是首要的,因此,悲鸿认为,任命美术院校的领导时,应当考虑德才兼备的人。周总理完全同意悲鸿的意见,频频点头。”我在《徐悲鸿一生》中叙述此事时,善意地避免直接提出刘海粟的名字。事实上是悲鸿向周总理谈到了刘海粟在上海沦陷期间,丧失民族气节之事,对任命刘海粟为“华东艺专”校长,认为不妥。1945年8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文化汉奸名录,刘海粟名列第六,并有文字说明刘海粟也下水了,称颂日本王道。我记得那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不久,我和悲鸿住在重庆的远郊,嘉陵江畔的盘溪,仍过着十分艰苦的战时生活,我们在黯淡的煤油灯下,读到这份报纸。
石楠文中竟引述了捏造的悲鸿谒见周总理的谈话,这样写着:虽说徐悲鸿没有说明中央教育部不该任命刘海粟为华东艺专校长,周总理明白了他所指为谁。他回答说:“徐先生,你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任命美术院校校长之前,就已做过细致调查研究工作了……”,“对某些画家的经历,要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不能只凭道听途说下结论……”上述这些话完全是捏造的。当时,周总理与悲鸿谈话,只有周总理、悲鸿和我三人在座,我作为亲自聆听周总理谈话的见证人,对于这样明目张胆、打着引号捏造周总理的谈话,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捏造者的目的十分明显,企图假造周总理的话来为刘海粟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掩饰。
刘海粟在上海沦陷期间,不仅是像《新华日报》指出的那样,颂扬日本王道,而且还借汉奸头目和日本军官之势,大张旗鼓地举办画展,请汪伪政府的司法部长主持开幕式,邀请了一批汉奸和日本军官为其捧场,而刘海粟得意洋洋,亲自陪同观赏,“风趣横生”(引伪《申报》原文)。伪《申报》还载有那些日本军官的军衔和名字。
刘海粟娶第三个妻子,在沦陷的上海举行中日来宾三百人参加的盛宴,伪《申报》也载有刘夏婚礼盛况的报道。他俩邀请了大批的日本军官和汉奸。当时,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上海市民在凄风苦雨中排队买不到粮食充饥。陈欣大姐曾对我说起在沦陷区的上海去排队买大米,排了很长久,也买不到的悲惨情景。
刘夏二人在国土沦亡、生灵涂炭之际,如此趾高气扬,大排婚宴,与汉奸及日本侵华军官开怀共饮,还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吗?
大家知道,梅兰芳留起胡子不演戏,程砚秋扛起锄头去北京西郊种地,齐白石也在大门上贴上纸条﹕画不卖予日本人。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爱国情操,长久被人们传颂。刘海粟与之相比,能不汗颜?外敌入侵,千千万万爱国同胞宁死不 屈。刘海粟对自己这种行为,能无愧色吗?
后来,华东艺专撤销,合并为南京艺术学院,当时便免去了刘海粟的校长之职,只作为普通教授安排,我认为这便表明了周总理对刘海粟的态度。
石楠文中还说,1953年夏天,周总理邀请刘海粟来北京,在百忙中派人把刘海粟接到他的住处,与刘从晚上8点钟谈到凌晨一点多。周总理拉着刘的手……他们谈了美术方面的许多问题,特别谈到徐刘应该团结的问题,周总理并对刘说:“你的态度很好,我来做这个工作……”以上这些,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首先,周总理从来没有对悲鸿谈过徐刘团结的问题。其次,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次长谈,为什么美术界不知道?连作为全国美协主席的徐悲鸿也不知道?
事实是,1953年夏天,刘海粟来北京求见中央有关领导。当时,郭沫若告诉我,刘海粟要求见他,他拒绝了。周扬接见了刘海粟(周扬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事后,周扬对悲鸿谈及了这次与刘的会见,说刘要求见周总理,周总理没有时间。周扬并说,他对刘海粟的印象不佳。
石楠文中重提早已被人厌弃的所谓师徒之争,说刘是徐的老师。1932年,悲鸿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也无,惟赖北京路旧书店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乃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从这篇启事中,十分清楚说明了悲鸿与刘海粟并无接触。刘海粟虽然也豋了启事,但对此点并未反驳。而在悲鸿逝世数十年后,刘却捏造:“记得那是1912年或1913年吧,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苍白嬴弱的年轻人携同一位中年人一起到我的学校报名就读,那便是徐悲鸿和他的父亲……”1912年至1913年,悲鸿的父亲重病卧床,不能出门,而且他一生从来没有到过上海。刘还捏造:“我很爱护他,我画油画,他跟着临摹,我画水彩,他也跟着画。如此维持了半年左右。有一天,他忽然不见了,实在令人忧愤。过后才知道,他到上海首屈一指的哈同花园,为其主人姬觉弥作人像画去了……”(引自石楠文)。这些都是刘海粟无耻的捏造。悲鸿应哈同花园之聘,为仓圣明智大学画仓颉像,那是1916年夏天,悲鸿当时正在震旦大学学习,我在《徐悲鸿一生》中有详细的叙述,并非刘说的1912或1913年。次年,1917年,悲鸿携哈同花园的稿酬,便赴日本了。刘海粟的捏造,令人失笑。
至于石楠文中所写“艺术观的分野”,谈到悲鸿反对后期印象派的某些画家,及悲鸿与徐志摩的论战,意在说明,此亦不和之因。悲鸿与著名诗人徐志摩论战,我在《徐悲鸿一生》也有叙述。他们彼此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坦诚争论,互不相让,但学术上的争论并未伤害他们之间的友谊,悲鸿与徐志摩仍是好朋友,悲鸿还为志摩的夫人陆小曼画了像。悲鸿一贯倡导写实主义,主张师法造化,中西结合。他既尊敬我国历史上有成就的画家,也崇敬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派、象征派的某些画家。在艺术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悲鸿选择了写实主义,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倡写实主义,以毕生精力,培养了几代功力深厚的美术家,为今日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钟涵所写:“徐悲鸿在倡导中国现代的写实主义方面是功不可没的。问题在于,写实主义不是随便什么人想提倡就能行起来的,它是一种社会时代的精神需要所致的,有客观必然的倾向。处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一种社会公民意识,愿意以自己的才艺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精神武器,而写实主义比较直接地反映生活真实,这种特征有利于发展民智,是人民认识社会现实和变革的道路,从徐悲鸿的老师康有为到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鲁迅,都这样提倡过。”徐悲鸿正是走在旧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行列中的一员,他以炽烈的爱国热情,不畏艰难困苦、诽谤和打击,坚持写实主义的教学和创作,数十年如一日。他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领导地位。
悲鸿逝世已经42年了。漫长的岁月并未淹没悲鸿的业绩。他的艺术主张和他的作品及教学体系仍在闪耀着光辉,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画坛。他的学生们一代一代薪火相传。中国美术事业也在百花齐放中篷勃发展。我在失去悲鸿的沉痛和哀婉中,为此感到欣慰。
执笔写此文时,心情是沉重的,我并不愿重提悲鸿与刘海粟的纠葛,也不想指名道姓地公开提到刘海粟的那些不光彩的事。过去我已发表的文章中都只提事实,不提刘海粟的名字,我是怀着善意那样做的。但是石楠既然在《一场波及画坛半个世纪的笔战》中重提此事,如果我不将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世,我便感到愧对周恩来总理,也愧对长眠在地下的悲鸿。
廖 静 文 1995年12月18日写于布拉格。
廖静文所说的事情,大多数我都知道。虽然角度不同,对徐悲鸿和尔后他的妻儿学生,把刘海粟的一本历史旧账翻了又翻,我自有我的看法,但是我却不能不承认,廖静文的陈述和对石楠的指责,基本上是准确的。石楠的《一场波及画坛半个世纪的笔战》我有,是她送给我的,文章很长,有一万多字,我尚未能耐下心来细读。一是她写的事情我都熟悉,再是对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不以为然。读完廖静文的文章,我把石楠的文章找出来对照。石楠是这样写的:
在完成《沧海人生——刘海粟传》后,我就有个设想,专题写写刘海粟和徐悲鸿两位当代画坛宗师间的关系。
1994年3月16日,是海粟大师百岁华诞,我应邀出席庆典,有机会重逢海翁,曾把这个想法告知他。他未置可否,只是眼里溢淌出一缕近似悲凉的复杂表情。良久之后他说:“我很怀念悲鸿。”接着他又再次重复了对我说过多次的话:“我一向提倡艺术大公,主张多姿多彩的流派共存,我反对宗派。”
一切让历史去说话吧!人的历史是自己写的,都得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不管这个人生前是否得到公允承认和评价,历史和时间总会揭去笼罩的迷雾、虚饰或溢美,还其真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有勇气的卢梭写出了他偷女仆袜带的事,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敢于解剖自己,把自己心灵的暗面呈现在历史的祭坛上,让现代和后代人从中得到启示和镜鉴,才是真正的伟大。如今海粟大师也已作古,我把艺坛上这段讳莫如深的两位大师间的真实关系写出来就有了新的意义。深爱艺术的信徒们啊!艺术需要创新,这样才有青春和生命,艺坛需要多姿多彩的流派,艺术的生命和青春才更显绚丽,屏弃一切宗派和门户吧!我们的艺苑就更加奼紫嫣红,五彩缤纷。
师生情缘未善终
1912年11月,刘海粟逃婚到上海,和盟兄乌始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自任院长,校址定在虹口乍浦路8号。1912年1月28日,在《申报》刊登招生广告称:“专授各种法兰西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30日的再次广告中院长署名乌始光。徐悲鸿长刘海粟一岁,就是循着这则广告来报考上海图画美术院的。1987年7月25日刘海粟在狮城新加坡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记得那是1912年,一位衣衫褴缕、蓬头垢面、苍白嬴弱的年轻人,携同一个中年人一起到我的学校报名就读。那便是徐悲鸿和他的父亲。他和朱屺瞻、王济远同班,当时上课还有一份点名册,朱屺瞻迄今仍健在,充分证明了历史真实。当时在校时,我很喜欢他,他家境虽贫穷,但却非常刻苦用功,勤奋学习,古文根底很好,文章也写得好,我画水彩,他也跟着画。如此维持了半年左右,有一天,他忽然不见了,不告而别,一连三天没音讯,实在令人担心。过后,才知道他到了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哈同花园为其主人姬觉弥做人像画去了。他通过哈同花园主人的桥梁,结识了不少当时文、政界名流,也拜了康有为为师,进入了蒋碧薇家,后又在蔡元培先生鼎力支持协助下,终如愿以偿到法国深造。我所办的《美术》杂志第三期,也曾做出报道。”刘海粟接着感慨地说,“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我并不那么在意名份辈份。也许,彼此的世界观及艺术观不同,胸襟狭窄宽博有别,出身背景有异。故彼此间一段渊源,却发展成了‘冤怨’,这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艺术观的分野
1927年,徐悲鸿先生留学8年学成回国,不久,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刘海粟亦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于1929年初赴欧洲考察艺术,原本定于1928年初冬启程赴欧的,当时他已定购好船票准备起程时,杨杏佛先生来见他,说:“蔡元培先生正在着手筹办第一届全国美展。这个议案是你5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来的,政府又不肯多支持,若办不成,不仅影响画家们的情绪,蔡先生的面子也不好看,我希望你推迟行期,协助蔡先生筹备好展览。”
海粟推掉了船票。蔡元培邀请他和叶恭绰、王一亭、高剑父等四十多人在上海沧洲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也请了徐悲鸿,可他没有来出席会议。筹委会就征集作品、编辑会刊、展厅布置进行了讨论,做出了具体安排。会议推选刘海粟、蔡元培、叶恭绰、王一亭、杨杏佛等主持筹备工作。刘海粟为之奔忙了好几个月,征集了很多好作品,产生了很多中国绘画家。这些中国画家的作品对国画传统有很多突破和转变,显著的如齐白石的单纯线条和积墨,郑午昌的用生宣刷染重色焦墨,贺天建的纵线条,张善孖的动物写生……中国美术开始从沉闷的、僵化的模式中,透溢出个性的生机。刘海粟和陈树人、郑曼青合作的《寒禽瘦石》入选,并列入会刊。他未等到美展开幕就启程西去了。
第一届全国美展于1929年5月开幕,这个预示着中国绘画新生命的画展,竟引起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是以徐悲鸿和徐志摩的笔战为两个对垒阵营的。有关这次论战,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一生》中是这样记述的:“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悲鸿拒绝参加。同时,就全国美展中宣扬形式主义作品,和徐志摩展开了论战。徐志摩是当时著名的鸳鸯蝴蝶派诗人。他不同意悲鸿对形式主义绘画的贬斥。悲鸿在《惑》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论点。首先,他列举了法国许多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的名字,以及他们辉煌的成就。接着他写道:‘雷诺尔之俗,塞尚之浮,马蒂斯之劣……借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一时……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竟趋时髦。’他还愤愤写道:‘若吾国革命政府,启其天纵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圆,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圆一幅之塞尚、马蒂斯之画十大间(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吗啡、海洛因……悲鸿在《惑之不解》一文中又写道:‘形既不存,何云艺乎?’他也指出形式美之伪,认为‘真伪不能混淆’,只有真实地描绘对象,才能予人以美感。‘我惟希望我亲爱之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我以青藤之同宗,来扳程朱面孔,无端致人厌恶,但处今日中国,实不能自已。’”
刘海粟是从徐志摩的来信中知道这场论战的。58年之后他在新加坡,当《明报》记者问到这场论战的实质时,他说:“30年代的法国画坛,基本上还是学院派的堡垒,故排斥、诋毁一切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当然,这些创新表现之作,其技法及表现方法,实际上已超越、摆脱了学院派系的传统表现方法。因此,在这学院派当权极势之下,一切具有创新及表现之作,一时并不给人看好的。这包括了凡高、高更、塞尚、马蒂斯及毕加索等人。这些人的作品其追求自我表现,摆脱陈旧因袭的学院派系传统,而热情地发扬、勇敢地表现流露出他们的主观意识、愿望、感情及思想。其艺术修养之高,创新思想、敢反抗、重表现的豪迈气魄,处处令我为之心折。也许,我之会疯狂崇拜他们,原因也在此吧!相反地,悲鸿去巴黎时,他便踏进了学院派大门,拜达仰.弗拉孟等人学习素描,而终其生在传统的学院派中研究、卫道。他极力反对后期印象派、野兽派及表现主义作品,刻意把马蒂斯译成‘马蹄死’,把毕加索译成‘必枷锁’。”
一场波及画坛半个多世纪的笔战
刘海粟在欧洲勤学苦读三年,于1931年9月回到上海。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为其举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他欧游期间所作油画109幅,罗浮宫临画15幅,东归后油画新作26幅,欧游前所作油画46幅,历年所作中国画36幅,共232幅。
《新晚报》刊出特刊,豋有刘海粟肖像照片,中国画《狮》、《春淙亭》、油画《鲤》、《罗浮宫之雪》、《圣母院夕照》、《威尼斯》、《罗马斗兽场》。并刊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序》、陈公博《展览会序》、沉恩孚《展览会图目序》、蔡元培《海粟先生欧游新作》、章衣萍《刘海粟先生》、陆费逵《海粟的画》、潘公展《当代画宗刘海粟大师》诸多名流文章,吴铁城在序言中称刘海粟为“当代画宗、五国新兴艺术之领袖”、“中国之新兴艺术,刘氏实为首先倡导之一人,其所以有叛徒之名者,亦以其20年来孳孳文化事业之心力之精神,创立新艺术之基耳。”16日出版的《上海画报》也为其画展刊了特刊,刊有蒋介石的题词:“海天鸿藻”,马相伯题词:“西崇实地,中尚虚神,以薪傅薪,谁主谁宾”,陈树人题词:“艺术革命之先导”,吴稚晖题词:“前无古人,后开来者”。林森题赠“百折不回”四字,并跋:
“海粟先生幼而岐嶷,甫舞勺,即活跃绘事,动笔独具心裁,别开生面,时人见其格局创异,不斤斤于绳墨,至以艺术叛徒谥之。同时,胡子适倡用语体文,士林前辈因并目为艺术革命家,盖非笑也。海粟乃毅然不顾一切,独往独来,另辟蹊径,始有今日之成就,惜时下学子,但见海粟之大胆落墨,而不知其用心细密,往往摹仿其豪迈而脱略其法度,此则海粟之罪人耳。余独喜海粟既富有创造性而又艰苦卓绝,独排众议,自成一家,爰缀四言,以志景仰云尔。”
同期《上海画报》还刊有叶恭绰、顾树森、曾今可、徐新六等人评论文章,曾今可在文中说:“刘海粟先生是一个中国的伟大艺术家,同时是个世界的美术家,他的画已经有了国际荣誉,被法国政府购藏于巴黎国家美术馆,且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大师’了,国内从事艺术者,多半出自他的门下。”
《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六期也为其画展出了特刊,载有倪贻德《刘海粟的艺术》,柳亚子《刘海粟先生印象记》,曾今可《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龚必正《读海粟先生油画后》,郑午昌《从海粟丛刊说到画展》等文章。
曾今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篇短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文中有段文字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的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参观展览的各阶层观者达十一万多人次,展览会轰动了国内外,成为艺术界一大盛事,也由之引发了影响中国画坛达半个世纪的一场论战。论战的导火线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那篇文章。悲鸿认为该文是对他的侮辱,他在1932年11月3日《申报》刊出了《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也无,惟赖北京路旧书店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乃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8年,虽无荣誉,却未尝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馆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域,难以究诘,恕不再豋,伏祈公鉴。”
这篇文章激怒了刘海粟,他以同样形式回敬悲鸿。11月5日《申报》刊出了刘海粟的《启事》:
“第三卷第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几经苦斗,为国人共知,非艺术绅士徐某者所能抹煞。且美专22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常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也不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申报》同时还刊豋了曾今可的《启事》:
“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无侮辱徐先生之处。此启。”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场论战,并非师徒之争,而是艺术派别之斗。顷间成了新闻媒介的热门新闻,引起了艺术界、知识界广泛关注。
11月7日,《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转载了徐悲鸿、刘海粟、曾今可三人的《启事》,同时发表了编后评论:
“悲鸿先生艺术之成功,国人自有定论。除开继续地努力外,可不必管自己是谁人的‘徒’,而‘徒’之为荣为辱为毁为誉,实无伤于自己艺术的价值。就是批评海粟先生的画,也应站在纯粹的艺术批评的立场上,真不必拉杂出许多‘野鸡’‘照片’‘吹牛’‘画院’‘流氓’等等和艺术批评无关的问题。而海粟先生呢,自己做了艺术的‘画宗’‘大师’‘领袖’,当然免不了许多非画宗、大师和领袖的艺术家要做叛徒。而刘先生之得有今日,正是由于叛徒之努力,对于艺术的叛徒们,应当鼓励之不暇,又何必以‘艺术绅士’之恶名向人家对骂?这未免有一点失去了艺术的画宗、大师、领袖的风度。”
11月19日,徐悲鸿再次在《申报》上刊出《启事》:
“‘海粟启事’可谓不佞‘法国画院……’,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坛,适行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10年。我不诬汝。(乞阅读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虽有《小贡献》的劝告,刘海粟看了这第二则《启事》,还是忍不住这口气,又提笔与悲鸿对垒。这时,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诗人梁宗岱从北京大学写来的;一封是蔡元培先生派人送来的。他先看蔡元培的信。蔡在信中说,看了他和悲鸿在报上的笔墨官司,很不痛快,劝他不要和悲鸿一般见识。“以你目前在艺坛上的地位,与他论争,岂不正好提高了他的地位,兄有很多事要做,何必把精力浪费在争闲气上呢?”梁宗岱的信很长,是系统评论他作品的,其中写道:“志摩看了你的《圣母院夕照》惊呼道:‘你的力量已到了画的外面去了!’倘若我在场的话,我会回响地应一声:‘不,你的画已经入了画的堂奥了!’表面相反的字眼所含的意思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一个意思的两面,你的艺术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了。换句话说,你的画已由摸索的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为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而且在神气满足的当儿,由力的冲动与崇拜进而为力的征服与实现了。”
这两封信,犹如两帖清凉剂,使刘海粟冷静下来,他自问道:谩骂、攻讦、不承认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非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呢?他记起了1930年5月30日和颜文良、孙福熙、杨秀涛一道从里昂乘快车往意大利,在火车上他曾对孙福熙说:“误解就是艺术,能够任人误解才是伟大;我总以为,我们不必使人了解,还是任人误解的好。我们本来就是传统的叛徒,世俗的罪人,我既不能敷衍苟安,尤不能妥协因循。我是一个为人讥笑惯了的呆子,但是我很愿意跟着我内部生命的力去做一生呆子。现在的中国就是因为有小手段、小能干的人太多了,所以社会会弄到那样轻浮、浅薄。”看来这些话也只是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壮壮胆的。他自责着,海粟啊海粟,你的心胸还不豁达,很不宽广,对艺术的理解怎么可能一致呢?艺术园地怎么只能开一种花,繁花似锦的花园才能兴旺啊!各种流派共存的艺坛才有丰富的颜色呀!可宗派万万不可有!那是振兴艺术的煞星!他忏悔般自谴道:我太意气用事了!竟以“艺术绅士”来回敬悲鸿!即使他不承认是我的学生,即使他初来沪上未曾进过我的学校,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才气又刻苦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消除门户之见,携手共振中国的艺术。惭愧!惭愧!我一定要寻一个机会和他谈谈。刘海粟把刚写了一半的论战文稿揉做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这场著名的论战暂时偃旗息鼓,可它的回响却十分深远,波及到数十年后的中国画坛,以至影响到各个门人和亲属。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他们之间的团结问题专门做了工作。那是1953年的夏天,周恩来总理请刘海粟到北京参观、作画,并请国务院交际处的常俊处长照顾海粟夫妇。一天,常俊陪他们游颐和园,海粟夫人夏伊乔指着昆明湖上一望无际的荷叶说:“多好看啊!”
常俊立即问:“您喜欢荷叶?”
伊乔说:“喜欢,江南还用荷叶包粉蒸肉呢,吃起来清香扑鼻。”
第二天他们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盘荷叶包的粉蒸肉。
海粟很感动,对常俊说:“你真是个有心人,照顾得这样仔细周到。”
常俊说:“照顾好你们,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几天后,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了他那里。
这是他们建国后第一次会见,都很高兴。总理说:“别人以为你的子女多在海外,你不会留下。可我相信,你会留下来继续办学的。因为你更爱的还是祖国!”
海粟很激动,攥紧了总理的手说:“谢谢总理这么理解我,相信我。在那时,是有人劝我去台湾,也有人叫我去香港、法国的,说:‘你的儿子任国民党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你女儿在英国,你侄子也去了台湾,你留下来日子不好过!’这时,我接到了你的信,要我留下来继续办学。是你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周总理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简朴的沙发上坐下,亲手给沏了茶,就坐在他的对面,谈起了去年进行的高等院校系院调整的事。总理说:“你在这项工作中为许多私立学校做出了好的榜样,把你创办了几十年的上海美专贡献给了祖国。我代表政府感谢你!”
海粟眼睛里腾起了热雾,他说:“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培养祖国需要的人才,正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我当初创办上海美专的初衷,我如愿以偿,我很感谢政府!”他又说起了对美术教育的构想,“上海美专积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有很多东西还值得今天借鉴,比如旅行写生,人体模特儿写生,都是锻炼学生如何用画笔来表现新中国建设和建设者精神面貌的好手段;让学生走进火热的生活,走进自然,才能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他又说了他的具体打算。
总理说:“你们的做法很好,像牙塔里培养不出人民的艺术家。”他又告诉他,“徐悲鸿先生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也有很多创新的表现。”他详细地向海粟介绍了,“你们可以互相学习嘛!”
海粟点点头:“是的,我很欣赏徐先生在美术教学上的‘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方针,他在培养美术人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对他很钦佩。他的西洋画根基厚,他的素描和色彩都有很深的基本功。早再20年代,我就看出他会成功,我多次向我的朋友推荐他,说他运用中国画的水墨技术结合西洋画的表现方法所创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应该给予支持。郭沫若先生把我的评价对许多人都说了,但当时有人还说他的功力不够,说我是‘谬奖’。我却坚信不移地说,‘让时间来证明吧!他准成大器。’他中年以后创作的《九方皋》、《愚公移山》气派很大。”
周总理脸上流溢出满意的神色,说:“曾有人对我说,你和徐先生长期不在一起,有所隔膜。我当时就严肃地说,‘不要相信外间的传闻,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是艺术家,过去又有一段缘份。外间凭猜想是猜不透的。我们还要依靠他两人团结合作,把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对吧?”总理亲切地看着他。
“对对对!”他应着,“由于我和悲鸿的艺术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又长期不在一起,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曾经有些误解。那时,我们都年少气盛,有些意气用事,现在想来,很没意思。但那是对艺术的不同认识引起的,也早已成为过去了,烟消云散了。我非常希望悲鸿能捐弃前嫌,我们团结起来,南北呼应,为发展繁荣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发挥我们全部的力量,才不辜负你对我们的希望。”
“你的态度很好!”周总理说,“我来做这个工作。”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画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学习。悲鸿对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建国前就开始了,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你们互相学习嘛!”周总理又鼓励海粟﹕“你们对美术事业都做出了贡献,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徐先生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要谅解他。你们的担子很重,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能健康长寿,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可靠的条件。”
他们从晚上8时谈到凌晨一点多钟。
这次会见,留给了海粟深刻的记忆,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他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听说总理召见了悲鸿。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一生》中也记述了这次会见。
那时,徐悲鸿的身体已不太好,正忙于筹备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工作。他向周总理汇报了美术界的准备情况。周总理在美术界的代表名单中没有看到刘海粟的名字,意识到徐刘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仍然存在,但周总理是有高超领导艺术的人,没有明说,而是把刘海粟对徐悲鸿的称赞和肯定转述给了徐悲鸿,徐悲鸿立即领会了周总理的意思,说:“总理,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美术界团结,这也是我的意愿。可是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是有原则的。我认为,画家的品德非常重要。”
周总理赞同地点点头说:“品德当然重要。”
徐悲鸿继续说:“我更认为,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要能为人师表,不能因为有了画家的头衔而品德就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期间,画家的民族气节应当是首位!”他说到这儿非常激动,“总理,我认为,任命美术院校领导应该考虑德才兼备的人!”
虽说徐悲鸿没有明说中央教育部不该任命刘海粟为华东艺专校长,总理已经明白了他的所指为谁。他回答说:“徐先生,你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在任命美术院校校长之前,就已做过细致调查研究工作。过去,因为画家们生活的地域、工作环境和各自艺术观点的差异,彼此间的交流和接触不够,互相缺乏了解,产生一些隔膜和误解是难免的。现在画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我希望你这个主席在促进画家间的了解和交流方面多做些工作,加强彼此理解,便于团结教育,对某些画家的经历,要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不能只凭道听途说而下结论。请你相信组织,我希望你们美术界加强团结合作,一切以有利于培养新中国的美术建设人才为重。团结就是力量嘛!”
一个月后的9月26日,刘海粟在上海从电波中得知徐悲鸿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突然病逝的消息,他很悲痛。他诚挚地撰文悼念悲鸿,说他去得太早了,说他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一大损失。叶恭绰先生称他这篇悼文有吴季子墓前挂剑深意。后来,他又听到一些谣传,说悲鸿的逝世与他们间的关系有关。说某中央领导在开会期间没有见到刘海粟而询及徐悲鸿,引起悲鸿激动,旧病突然复发。又一说,某领导要徐刘握手,刘海粟把手伸向悲鸿,悲鸿拂袖而去,气冲病灶。这些谣传,使刘海粟深感不安。
徐悲鸿和刘海粟间的隔膜影响深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刘海粟运途多舛,被排斥,得不到公正的承认。台湾《民生报》一篇特稿称他是“现代中国画坛倍受争议的人物”。不可否认,这争议渊源与徐、刘的隔膜不无关系。1994年8月7日,刘海粟逝世,随着中国画坛两位宗师的作古,美术史上这折著名而又神秘莫测的恩怨故事也该闭幕了。
叶恭绰题画论徐、刘
1962年春天,刘海粟摘掉了“右派”份子帽子,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携夫人夏伊乔进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他9年未进京,非常想念在京的老朋友们。他在收拾行李时,就把1956年在西安创作的中国画《骊山图卷》和《临石涛松壑鸣泉图卷》装进了箱子,带到北京请老朋友题识。他如愿以偿,会议期间,他会见了好朋友何香凝、章士钊、叶恭绰、黄炎培、郭沫若、张伯驹等。在中国画院任院长的叶恭绰在他的《骊山图卷》上题了长跋。跋曰:
与海粟别数年,今春来京,以此卷见示,属为题识。且曰﹕吾意在以此卷,为双方友谊之证,非专为此卷也。余闻之,喟然曰:余将何言耶?下笔将罄纸不能尽,则且徒留形迹,以彰故之过,非吾意也。继思徐、刘二君与吾之关涉,深知者究不多,不自言之,将揣钥之谈纷然而出,诚不如吾言之为当。且吾识二君时,年皆方少,余以奖励后进之为怀,颇亦尽其引掖提携之力。二君交逆不终,余方引为遗憾。徐君去世,余劝刘君力表其坦白惋悼之意,刘悉为之,似有类于挂剑,徐君地下当亦释然。二君门下亲属,似不应当成芥蒂。且徐之对刘,诚有过举,然似为病态,无事殚述,且是非终有评定。刘君其努力艺术,前途期乎远大,为吾国增其声誉,则一时之得失,及交谊亲疏,皆可置之勿关念矣。因书此以归之,世人论徐、刘交谊,不妨以此为证。
叶恭绰先生是刘海粟、徐悲鸿共同的师友,他很了解他们,他的这通关于徐悲鸿和刘海粟关系的评论,将是后世美术史家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文献。在同一卷上,张伯驹先生亦题曰:
海粟为悲鸿师,后偶生嫌隙亦类似梨园程砚秋与梅兰芳之事。叶遐翁(恭绰)劝之,海粟尽释然,余亦曾与悲鸿发生论战,悲鸿谓京画家只能临摹,不能创作。又谓其美术学生犹胜王石谷。余则以为﹕临摹为创作之母。王石谷画多法度,仍可为后生借鉴。经友刘天华调解乃复友如初。此两事为后之画家所不知。因重记之,以为异日艺苑掌故。
————
人民文学出版社《沧海》内容简介:
《沧海》(原为三部曲,后修订为上下卷)是旅美画家、艺术大师刘海粟惟一的研究生简繁先生根据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人物的回忆和访谈,对20世纪中国美术家的命运所作的客观而生动的记录。作品从不同角度,冷静而理性地向历史和读者再现了一个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世纪老人刘海粟,同时,还触及了美术界的是非恩怨,读者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画坛之一斑。
本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厚,极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尤其是关于刘海粟大量隐秘的披露,更具独特价值。应当说,这是迄今了解和研究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和刘海粟的最佳文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