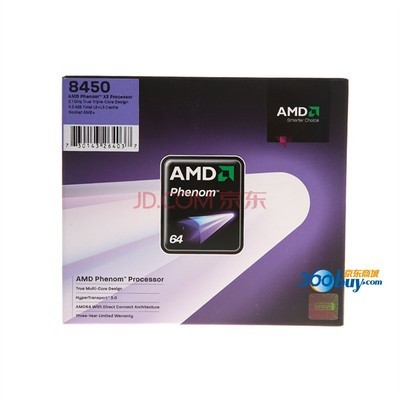大概上初中的时候看到这首诗吧,诗的其它部分都不记得了,只有这一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直留在心底。只觉得美,不可抑制地向往那样的意境,却只可臆想不能抵达。
十多岁的女孩子总是爱热闹的,这句诗却我静下来,想来那时也到了思虑的年龄,虽知道美,却不知美在哪里。后来长大了,懂得它的美在于空旷幽静,是无心无虑的美。到如今,看过了多少世情,经历了多少人情冷暖,才知道它的美不仅在于景,亦在于心,是由心看到的景,是忘我也是忘情。
胡应麟在评论此诗时,说它可以“入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这大概是最我契合我心境的评语。
诗的作者王维一直被人推崇甚高,与陶渊明并称“田园诗人”,可见两人有许多共通之处。不过在我看来,两人的气质有很大的不同,王维是清幽出尘,陶渊明是悠然平和。若拿书中的人物作比,王维是林中弹琴的高士,只能听,不可近;陶渊明是隐居山野的名儒,你去寻访他,他会自茅屋里递出一碗水,微笑问答。
所以,以神秘感来说,显然王维更让人莫测,他有时在空山,有时有竹林,无论在何处,他总是一个人独行,是传说中的人物。这样的人,大概很难动情动心的,因为他已经看惯情感纷争,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辛夷坞》的全诗是这样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花我未见过,想象不出它的样子,在百度搜索,其形其色似红色的玉兰花,盛开之时远观,竟如桃杏一般耀眼夺目。艳丽如此,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吧,却也自开自落,与人无扰。想来也是心静的缘故。
我之前录过一段故事,讲一个出家的女子,她曾深爱的丈夫来探,她送他出寺门,最后一次步履相和,两人都落地无尘。他说:“请留步。”她目送他下山,直至人影全无,她在地上捡一叶赤红菩提,一面行一面嗅,原来春在枝头已十分。
你和他
原是滴水粒米的寻常夫妻
车水马龙里守一份从容
燃香灯黄前悲天喜生的修持
梵世夫妻的菩提 也
挡不住浊世的汹涌
谁能想象你解发的刹那
胸口逝水般滔滔
她是年轻悦目的女子,只因一心向佛,遂离家剃度,割舍了一心一意相爱的丈夫。我总是想,有哪种信仰可以替代爱情的信仰?有哪种坚定可以替代承诺的坚定?是不是世俗的情感已阻碍了前行的脚步,是不是朝圣的灵魂已看到了更壮阔的殿堂?也许有一天我们终会明白,我们不必忠于爱情,而只需忠于自己?
我们无法回头,只能走各自的道路。当一切可以“入禅”,念念不忘或念念相忘,世间多了一个佛前欢喜华严的女子和一个灯下清淡自居的男子,花落也是花开,那就是了。
这个故事是简贞所写。简贞是我偏爱的台湾女作家,她曾与爱悦的男子相恋七载,却最终因信仰的不同和男子的离世而天地相隔。大概是这份残酷,使她的文字既有杀戮的气质,又有遗世而独立的壮美。我每次看她的文章,总要看到心潮激荡、不能自已才作罢。比如这样的句子:“不给我天,我去劈一个天;不给我秩序,我去秩一套秩序,生命用来称帝,不是做奴隶”,又或者:“活着,就要活到袒胸露背迎接万箭穿心,犹能举头对苍天一笑的境地。因为美,容不下一点狼狈,不允许掰一块尊严,只为了妥协。”
但横刀立马不是常态,我们终会平息心境,在拷问过生活和拷问过自己之后,我们只求获得内心永恒的安宁。简贞的静在于“佛”,信仰的力量让她超越了生死,在大开大合之后获得了平静。她在34岁遇到可以终身相托的男子,得到了一个凡妇应有的幸福。
对人生的谜题,我们要解答得很多,比如 情感,比如权欲,比如生与死,比如舍与得。有人愿意借助书本,有人愿意以借助信仰。王维是向大自然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并达到自然与身心的合一。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空无的境界,也是他的理想境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