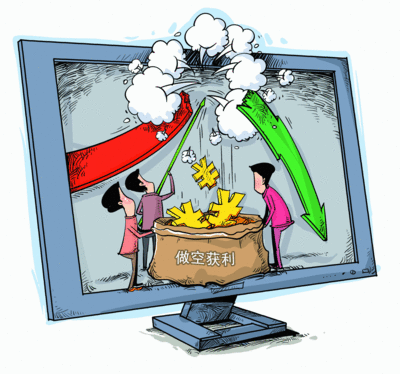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凝聚力与软实力
2014-07-25 17:59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2期 作者:郭小聪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论及文化软实力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的视角,而非美国的视角。美国人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从来不会局限于本国边界之内,他们总是在利用超强硬、软实力谋求全球霸主地位的同时,也给别的国家带来安全问题。约瑟夫·奈(JosephS.Nve)所说的“软实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这样断言和奢望,包括中国。
所以,要有成果地探讨软实力,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包含了具体的指涉,它总是涉及谁的安全、怎样的安全以及如何安全等一系列必须有特定主体的追问。也只有在把握了视角、明确了立场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提出问题,引发有意义的思考。
一 一体两面的凝聚力与软实力
应运而生的理论往往是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软实力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能够被广泛接受,说明今天的国际社会期待让实力有所柔化,争斗显得文明。但软实力说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共鸣,又显然不像美国人那样为了事半功倍,不战而胜,而是为了广结善缘,努力营造和维护有利于中国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如果说美国人是把文化软实力当做“矛”来运用的,那我们中国人就是把它当做“盾”来使用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软实力概念做进一步的辨析和补充,形成自己的阐释,哪怕不够成熟,也比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能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如果我们老是在现成的概念、思路里打转转,那么我们脑海里除了美国式的念头或痴想外,还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说,越是国力上升期,也越是压力陡增期,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外部重重压力,更需要练好内功,认真发掘中国传统中的软实力资源,才能有效应对,以柔克刚。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中也有必要将凝聚力概念抽离、细分出来,与软实力概念相提并论,综合考虑,这样才更能切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事实上,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源于同一个东西,即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只不过,一国文化在国界之外发挥的影响力,构成了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通常称为软实力,而“实力”本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但在国界之内,一国文化所具有的向心力、感召力,则应当被称为凝聚力而非软实力,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熔铸国家意志,提振民族精神,增强国内民众认同感。不过,尽管分属国内、国外,着力点不同,凝聚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却是内在统一的,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一种对内缺少凝聚力的文化,对外也显然谈不上什么软实力。
指出这一区别好像是多此一举,但又并非无关紧要。因为美国人倡导的软实力说从来不讲凝聚力,他们只讲软实力,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锁定在对外关系上。尽管约瑟夫·奈也说过“民族凝聚力”是软实力的“无形的力量资源”,[2]但他并不多说一句,而是反复念叨着:“如果我能让你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无需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了。如果美国人代表了其他人愿望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3]这也很好理解,作为战略进攻方,美国人有着十足的文化自信,他们认定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优越的,从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流行文化,美国社会都堪称典范,值得各国效仿。也只有世界的全面美国化,才会给美国人带来最大的国家安全。所以说,美国人对自己的精神文化是既虔信又保守的,他们很少反省自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对外施加影响,甚至将软实力等同于巧实力。
相反,作为战略防守方,中国人看重软实力并非为了左右他人意愿,而是为了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果说,美国人一心想挖别人的墙根,那我们就是要筑好自己的阵脚;美国人期望用美式价值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则要动员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精神力量众志成城。所以,对我们而言,凝聚力和软实力是一体两面、相互呼应的,要想在国际上站住脚,首先要在国内撑得住台;要想对外拓展软实力,就要认真发掘自己的凝聚力。事实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学者正是用“国内间的”(inter mestic)这一概念术语来形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的这种相融关系。[4]2013年,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在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也强调,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一旦重大危机到来,就会失去存在的信念和力量,麻木不仁,坐以待毙。[5]
正是如此,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地将文化软实力与凝聚力相提并论,一方面指出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会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肯定“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强调两者共同构成国家“赢得主动”的内在力量。这一新见解、新思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意义,切合中国目前的战略地位需求,也启发我们在软实力研究中独立思考,为我所用,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凝聚民气,夯实根基,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文化本性。
二 “衰而又兴”的凝聚力: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
如何评估自身的软实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外人的眼光。其一,说到底,软实力有赖于凝聚力,自身的精神凝聚力强不强,最终还是外人看得清。其二,也往往是从外人惊异的目光中,我们才能从平时见怪不怪的问题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其三,通过外人的眼光反观自我,也有助于提高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探幽索微的能力。
譬如,约瑟夫·奈为什么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和传统的儒家文化?[6]类似的看法在海外屡见不鲜,而我们却感到惊奇。因为,我们自认为经历了近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国才最终与旧传统决裂,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可是为什么海外学者固执地认为,我们今天巨大变化的动力仍然与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呢?
进一步梳理,我们又会发现,西方人的这一见解是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我们可能浑然不觉而西方人却一直大惑不解,因为这与西方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华文明似乎有着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不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至今还在使用,而且还是同一血脉子孙在使用,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他们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旦衰落了就一蹶不振;而中华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几乎是同一时期,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中国在经历了同样几百年大分裂、大动荡之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直到进入21世纪,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Heinrich WaldemarSchmid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这样惊呼:“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为什么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已经存在了约两千二百年。”“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的宗教的国家——真是不寻常”。[7]
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西方人似乎找到了答案,倾向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类似于某种历史活化石,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文明的新鲜空气就会风化,最终逃不脱覆灭的命运。可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惊人变化,说明中国并非老而不死,死而不僵,而是能够顺时应变,急起直追,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才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原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提出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8]也就是说,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的确如此,回顾历史,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发明出一套适合农业文明的静态化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得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入侵,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已经在悄悄地“重新树立其理想”,或者说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这就是从以前那种封闭性的农业社会圆形轨道,转向“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理想追求,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正在深入人心。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你看中国人唱的歌曲,写的诗文,最后几乎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的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路去畅想和结尾,这几乎成了今天的一种陈词滥调,但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确实已经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封闭转向开放,而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学术性语言来说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9]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和挑战,就无法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以支撑战时体制。所以,惟有求新、求变,才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
看似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革故鼎新的一面,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多么难。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说:“我自幼就了解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10]正是由于父辈的醒悟,中国现代学子很快就从四书五经转向了对西方人文科技的学习。学者冯尔康在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时也发现,家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其实也能够很快适应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清朝时期,民间家中安置‘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民国时期改作‘天地国亲师’,‘君’字易为‘国’字的一字之更,反映的是国体的变异,表示民众从忠君转向爱国。”而湖南萍乡刘氏《家训》明确提出“爱国家以保种族”,[11]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和自强力量。
抗战胜利时所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者也”。[12]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对外人来说就是令人敬畏的软实力。当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还在满目疮痍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是它的过去的产物,它的历史是独特的。其他国家来而复去,其他帝国由兴而亡,但是中国持续下去;中国是永世长存的。”[13]
果然,中国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变化之大,经济增长之快,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如同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你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总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可以说是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节奏。而且,即使问题成堆,整个社会看起来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有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以致于“北京共识”的首倡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惊呼: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解体前的反应像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14]
正是如此,中国衰而又兴的凝聚力,在西方人眼中,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如古老长城般难以征服的精神屏障。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PatriciaBuckleyEbrey)的态度很典型,她一方面追问:中国如此巨大,各地方的差异十分明显,遇到的灾难也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什么会延续几千年呢?那么这一次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打击下,中国的古老历史会就此中断吗?但她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否定的,她从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得出了如下看法:“我尽可能地把历史遗产塑造成一种资源而非桎梏。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15]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和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仍然处于五四新文化震撼期中,习惯于把现代与传统看成是断裂的、势不两立的。但西方学者却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这次危机太深重了,这一代中国“儒生”不得不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以重新确立理想的方式力挽狂澜。但今天的挑战仍然不过是其漫长历史中一次新的经历,最终还将化为新的传统,所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是浑然一体的,目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其合乎逻辑的历史演进。而其中的软实力意味着:中国可以一时被打败,但不会永远被征服,越是在大灾大难之际,越能显示其韧性。而且,考虑到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有着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以及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那么一旦中国人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当然,地球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不大的村庄,如果人类都无限制地求新、求变,想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地球如何负担?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怎样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它原本由西方历史文化中催生出来,现在则需要由全体地球人一起来解决,转变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诉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文明与和谐的世界。
三 “和而不同”的凝聚力: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
如果说,西方人有关中国的第一个疑问是从时间维度上展开的,那么第二个疑问则可以说是从空间维度上展开的,这又是一个我们浑然不觉而西方人却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两个问题也是有关联的。
中国历史为什么延续不断?有些西方人试图用高度的种族同一性原因来解释,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的话颇有代表性:“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民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16]也就是说,中国的超强稳定性在于其国家内部文化与民族构成的高度同一。这个见解无疑会引发新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社会内部的精神文化特征也应当是高度一致的,民族同一性只有凭借文化同一性才能得到切实体现和保证。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各地社会生活、文化特性历来是复杂多元的,长期共存的,这一点有目共睹。2013年10月,一位在中国任教两年多的美籍教师即感叹,觉得中国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的文化多样性,别的国家各个地方往往千篇一律,而中国不但大中小城市的文化截然不同,南北东西风情各异,就连相邻两个镇的方言都可能不一样,这让他感到惊讶和享受。[17]按照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如果社会生活、文化面貌差异到这个地步,早就该分裂成无数个国家了,可是中国为什么既能保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又没有妨碍各地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呢?这对西方一直是一个谜。
特别是在汉语语言多样性问题上,西方学者的困惑达到了顶点,甚至觉得有些非理性。因为中国人所操各地方言,在西方人看来早就该划分为不同的语言了,可中国人却为什么依然固我、毫未察觉呢?伊佩霞不能理解:“说汉语的人彼此之间也不都能听懂对方说的话,这些中国‘方言’的差别比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别还大,甚至很容易被当做彼此独立的语言。”[18]一位西方人类文化学家则从学理上指出,区分不同语言的关键点在于说各自语言的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因而即使不同方言也可能被视为两种不同语言。如果讲北京话的人无法与操广东方言的人交流,那就应该被视为两种语言,因为“在语言方面,没有什么分语言或次语言这种东西”。[19]另一位西方语言学者在其所著《汉语概说》一书中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区所用的语言都统称为汉语呢?不管怎么说,现代的汉语方言,更像是一个语系:公元前一千年的汉语和现代的标准语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法语之间的差别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像少数外国观察者那样敏感地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20]总之,西方人最迷惑、最不可理解的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各地方言之问的差别明明已经大到彼此看不懂、听不懂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全体中国人仍然执拗地、迟钝地认为,他们平时说的就是同一种语言——汉语?难道看不出彼此的巨大区别吗?而且,即使语言交流中存在着实际障碍,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相互隔膜、疏远,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向心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这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能够超越万水千山而凝聚了古往今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必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在。梁漱溟先生认为:“试从山川地形上看,从种族语言上看,皆非不能让中国分为若干民族若干国家者。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垒隔阂,广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无比之一伟大民族。”[21]也就是说,正是重情感、重良知的社会文化心理,构成了非凡的凝聚力。
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思维胜于抽象思辨的东方民族,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感性生命之精神——是在今天还未曾丧失的中国之根基”。[22]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感性生命的情感纽带具体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靠着什么样的精神磁力线,才能传递忠诚和热力,让各个地区的中国人既“和而不同”又守望相助呢?要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文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长期不平衡,这本来是会导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和竞争的,某一时期某种方言的流行其实正是某一地方文化在全国走强的标志。而按照西方人的历史经验,这很容易造成人们差别的鸿沟和地区分离主义倾向,但为什么唯独中国没有发生四分五裂的情况呢?
近年来,一本社会学专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23]富于创见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学者程美宝通过对晚清以来广东地方文化观念的考察,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对于中国而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长期共存,不但不会构成分裂的威胁,相反,各种地方文化之间的积极竞争,还会促进对国家的精神认同,对社会生活起到更具活力的凝聚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地方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不以离心离德为代价,恰恰相反,无论谁占据了文化优势地位,都会争着表达忠心,表达自己对于国家文化所做的贡献,显示中华文化在某地之意。广东历史上的三大族群正是这样,无论哪个族群兴盛,都要想方设法论证自己与中国文化正统、主流的关系。譬如,客家人自近代崛起后,便一如粤人、潮人那样,利用著书、撰文、修志等话语权,论证自己的“中原来源说”,声称自己早在南迁之前就已是衣冠旧族,沐得中原文化熏陶。
程美宝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各地文化无论怎样复杂多元,强弱不一,也不会威胁到国家统一,反而还会不断丰富和壮大中国的主流文化。“这种实际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趋向统一的辩证的国家地方关系,恰恰是中国文化最诱人的地方”。[24]这也正是国家认同感与地方文化多样性相契合的最奇妙之处。这个结论还可以用来解答西方人有关汉语语言多样性的长久困惑——正因为汉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表述中是趋向统一的,所以不管各地方言差别有多大,都不可能分化为独立的语言。这的确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源于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感,这也是中国国家意识中最柔韧、感人之处。
所以,中华民族的超强稳定性并非来自于种族同一性,这一点在汉代时就已经很清楚了,台湾学者许倬云曾指出:自汉代以来,“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构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25]这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有本质不同。同样,清末时各省竞相宣布独立,也不是真要分裂,而只是以此政治之举宣示中央政权因无道而不合法,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正是点出其要义。[26]所以,在中国传统中,由于文化认同感的存在,地方意识、地方文化一般不会助长政治上的离心现象,反而会促进大家同心同德。
即使在今天,这种地理上远隔天南海北而在精神上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感人至深。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汶川大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千军万马,源源不断。这表现在抢险救灾中,更体现在震后重建项目中。各兄弟省市不仅无私援助,调拨巨额资金,派出精兵强将,而且相互暗暗较劲,争着要把自己负责的重建项目做成最好的品牌工程。他们此时代表的是国家,争的是谁能更好地把国家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位,把守望相助的同胞亲情殷殷体现出来。
大灾大难面前是如此,在和平日子里这种富于亲和力的精神磁力线也随处可见。例如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各省区的金牌争夺战牵动人心。每当可能获金牌的运动员开始比赛时,有些家乡电视台甚至会早早把摄像机搬到他家里去,等待捕捉夺金时刻乡亲父老欢喜若狂的场面。同样,各地重赏运动员的新闻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陈燮霞预计将从广东省体育局得到50万元奖金和一辆价值80万元以上的奥迪汽车。她的家乡番禺区和榄核镇政府也将分别奖励8万元。考虑到首金的特殊性,她还将从企业和私人赞助中获得额外奖励。”“而同时中国拳击和贵州省实现了金牌突破的邹市明,政府和企业必将对他重奖。由于邹市明是遵义人,目前已有消息称茅台集团会在遵义为他建立纪念馆。”[27]等等。这些浓墨重彩的地方竞争意识究竟在说明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争强好胜吗?显然不是,各个地区争先恐后,热火朝天,争的是为国家做贡献,自有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默契和心气在。所以,不管南方北方,每当获奖运动员家人接受采访时,回答最多的两句话是:给咱中国争了光、是咱家乡人的骄傲。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化情感纽带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各国自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立国之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确如华裔学者谭中所说,“和谐”是中国的命根子,其广土众民正是靠文化吸引力由中国内部各族居民根据他们的共同意愿而逐渐形成的。隋唐之所以比秦汉帝国更能“持续发展”,也正是有赖于儒、道、佛的“三教合一”。[28]中国学者温春来撰写的《从“异域”到“旧疆”》一书,也通过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国族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29]可以断言,正是共同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以及漫长的时间浸润,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才能开花结果,形成强大凝聚力。
甚至,哪怕受苦受难,只要曾经同甘共苦,也会不可思议地变成凝聚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堪称浩劫,但美国学者鲍大可(A.DoakBarnett)在重访宁夏时却惊奇地发现,尽管几乎所有清真寺都曾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宗教领袖也受到过“政治斗争”的冲击,可这里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怨恨,“看不到有什么民族冲突或紧张的明显迹象”,“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有削弱与中央联系的离心力”。为什么呢?鲍大可在其《中国西部四十年》一书中领悟到,正因为“回首往事,回汉两族人民都认为那是一场大灾难”,共同的不幸也让大家有共同的期待。果然,在随后的改革开放热潮中,鲍大可感受到:“我觉得和前些年相比,1988年宁夏与‘中央’的联系更密切了,也更加依赖‘中央’了”。[30]由此可见,大家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才会产生精神认同感。
反过来说,顺便指出,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政治分离状态,缺少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那么即使有共同的文化根基,久而久之也容易各行其是,另起炉灶,分道扬镳。首倡“地球村”概念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McLuhan),在谈到魁北克分离主义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从硬件的意义上说,加拿大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统一。在电子条件下,硬件处在危险之中。在电子速度条件下,硬件世界倾向于移入软件的世界。”[31]这段话令人深思,一个国家维持统一的硬件固然重要,但更可靠的还在于软件,在于患难与共的情感共鸣,这才是信息社会条件下也仍不会丧失的精神内核。同样,如果各方分离时间过长,大到政府号令、规章制度,小到学生课本内容、节假日安排的不同,各自的民众都没有什么共同记忆,也没有日常情感的交集,那么长此以往,自然会渐行渐远,形同陌路,甚至漠视法理分裂的残酷现实。而且,一旦兄弟阋墙,国家分裂,很可能原有的文化凝聚力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变成相互黏合的软实力,共同的文化也不会令双方心存感念,藕断丝连,相反,很可能由爱生恨,爱恨交加,更加绝情。特别是相对弱小的一方,往往会因巩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刻意强调彼此的不同,斩断文化之根,又因知彼知己而常能戳到要害,那才是刀刀见血,事事锥心。毕竟,一旦同处于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就要比亲缘文化的影响大得多。
四 从“协和万邦”到“和谐世界”
过去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自成天下,独步一时,主要靠的是文化的浸润而非武力征服,才形成了东亚朝贡体系及东亚儒教文化圈,这与西方主要靠强力扩张势力范围、输出文化的历史迥然不同。早在《尚书·尧典》中,中国人即已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主张,而“华夏”一词也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流行于世的,文化高可称夏,文化低则称夷,夷可变夏,夏也可变夷。唐代《律疏》阐释得很明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15世纪时朝鲜李朝因汉字艰深,不便平民学习,另创谚文字,朝鲜士大夫多有不满:“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岂非文明之大累哉!”[32]礼义廉耻,高下自见,大家都可以文明竞争,这一观念亦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石。所以说,中国“和谐文化”的根子很深,甚至是立国之本,无论邦国、族群、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政治伦理观念,还是精神文化上儒、释、道的多元互补,博采众长,无不受惠于此。
正因为有着“道并行而不悖”的传统,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后,提出“和谐世界”的新国际安全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有人质疑这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至多是中国崛起阶段的策略性运用,但长期以来,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坚持对话增进相互信任,以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一直贯穿在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指导原则中。不过,随着凝聚力向软实力转化,文化影响力向国外拓展,我们也应当对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有所准备。
首先,国内各个地区的文化不管怎样千差万别,强弱不一,但大家都有一种争着为国家做贡献的亲和力,这也是最为可靠的凝聚力。但在国际上明显缺少这种热乎劲,各种文明、文化形态复杂异常,历史恩怨纠缠不清,国家利益和实力地位是各国最高的追求,却并没有一种显著的争着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心气在。因此,“全球村”即使成为趋势,似乎也缺少“全球村”的内在合力。
其次,人不仅是有道德、有情感、有理性的个人,更是一种首先要维护团体自我生存的社会动物。因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缺少权威政府的统驭,实际上也缺乏普世价值的认同,最终占上风的总是生存竞争,实际利益。所以,一个社会内部通常被赞许、被鼓励的优点、长处,在别的社会不一定被赞赏,甚至可能成为被嫉恨的原因,如果它作为脱颖而出的竞争实力,让别人自愧不如的话。譬如中国人的勤俭,本来是最苛求自己的生存之道,按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勤是对自己策动,俭是对自己节制,向里用劲”。[33]但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的品德,在国外也会招灾惹祸。19世纪美国加利福尼亚人就因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而试图用强力将他们排除在当地经济竞争之外。[34]前几年在西班牙发生的焚烧中国人鞋厂的严重事件,也是因为中国人克勤克俭,让当地人感到莫大的生存威胁,还被视为对当地生活方式的破坏。所以,我们认为好的品质、善良愿望、慷慨之举,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在国外不一定受欢迎。
最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倡导“双赢”、“共赢”理念以取代原有的“零和”式安全游戏,不管初衷多么良善,也不一定意味着皆大欢喜的和平红利,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确定性危险。因为,我们自以为不过是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传统天下观发扬光大,西方人却可能认为这是要动摇他们的一统天下。我们的处世原则越是和颜悦色,以和为贵,讲求平等,就越是让西方人以实力决定权力的现行国际秩序显得颐指气使,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倡导的“和谐世界”的新国际安全观,有可能被西方人视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挑战。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即认为:“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因为除了经济实力的增长外,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的历史,要求地位平等和坚持不听命于外国的敏感,使得这些对中国人来说“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35]还有什么比道德层面上的分歧和挑战更为根本、更难以让步的呢?
今天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撞击后合乎逻辑的后续结果。中国学者韦正翔在《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遏制中国的理由还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明,西方人害怕中国的异质文明,以往他们相信自己的文明是最先进的,属当代的,把中华文明当做文物。可文物一旦复活,局面就将改观,中国目前的发展将具有制度示范性作用,因为国家的兴旺通常会被归结为采用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结果。[36]事实上,中国既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竞争活力,又不愿以霸权论世,这一行为准则和处世方式本身就是对西方实力地位、意识形态的强有力颠覆,具有硬实力效应,而不仅仅局限于软实力影响。
所以,在当今这个讲理、也更讲实力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既然提出“和谐世界”的新国际安全观,就意味着我们有捍卫自身理想信念、行为准则的坚强意志,也有着付诸实践、影响世界的相应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外交上奉行的“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东盟十国加中日韩(“10+3”)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为,已经在塑造中国新的形象。所以,中国越是坚持贯彻“和谐世界”理念,就越是要练好内功,在稳步增长的实力基础上积极营造多元共存的国际和平环境,才能让别人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认识、适应和融合。有鉴于此,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显然不应只是怀柔感化作用的代名词,还应包含和体现力抗强者、主持正义、维护公正等精神内涵与道德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备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注释:
[1][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5页。
[2][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3][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第10页。
[4][美]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9版),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5][俄]罗伊·梅德韦杰夫:《民主化失控酿成苏联解体灾难》,载《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1日。
[6][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第19页。
[7][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德]弗朗克·西伦:《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梅兆荣、曹其宁、刘昌业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
[8][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2页。
[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庭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1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94页。
[13][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14][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第295页。
[15][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57页。
[16][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7]《难以置信!一个美国人讲述他为什么喜欢中国》,2013年10月25日,http://bbs.tiexue.net/post2_6963199_1.html。
[18][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序,第257页。
[19][美]威廉·A.汉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20][美]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导论。
[2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22]王德峰:《中国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载上海证大研究所编:《文明的和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23]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314页。
[25]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26]王吉胜主编:《中西著名思想命题要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27]东东:《首金得主陈燮霞将成为“奖金王”》,载《书报文摘》,2008年第35期。
[28]谭中:《和谐中国是构筑新世界的百年大计》,载香港《镜报》月刊,2006年11月号。
[29]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导言第2页。
[30][美]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孙英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6、112-113页。
[31][加]麦克卢汉编:《麦克卢汉如是说》,何道宽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32]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3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03页。
[34][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35][美]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1-802页。
[36]韦正翔:《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8页。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
[责任编辑:焦杨]标签: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软实力复制网址打印收藏0猜你喜欢
相关新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