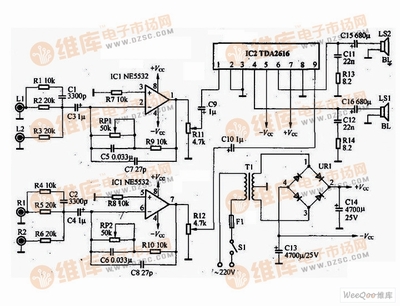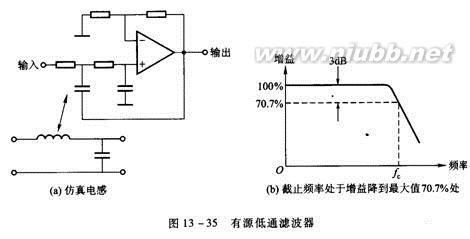11时接平凹电话、杨乐生短信:冯有源同学因病于今晨离世。沉痛哀悼!
同窗三载,牵念一世。
2113-07-31 0:34
收到薛迪之老师短信:
和谷:悼有源会我不能去,请将我的悼诗录在签字留言薄上。
薛托——
悼酒友
忆昔酒友性情人
春花秋月喝十巡
瓷瓶香溢我欲醉
玉杯液满你已醺
激浊扬清无忌口
立眉嗔目不平心
饮罢山也包谷酒
师生情意分外深
薛迪之挽
资料
摘自中国网:
记者:你觉得你真正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过以前编过雷锋的《一双袜子》的文章,这类早期的文学记忆还有哪些?
贾平凹:我产生写文章的兴趣是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学土壤很薄,陕西省还没有一家文学刊物,图书馆也不开放中外那些文学名著。写作可能是人类的一种生命兴趣吧,我那时偏就喜欢写作。这如在院子里倒了一堆土,虽然这堆土不久就得铲出去,而土里有散落的草籽或粮食种子,下了雨又晒了太阳,它就长出草和麦子包谷的苗子来。
那时兴革命故事,我写的东西变成铅印的是一篇《一双袜子》,是一篇革命故事,是和大学同学兼乡党冯有源合作写的,发表在1973年8月号的《群众艺术》上。这篇故事发表后,接连发表了许多,到大学毕业时大概有25篇吧。这都不是文学创作,算作是一种爱好文学的练习,所写的内容已经记不起了,记起的是那时的热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在我后来的写作中从没有,却就在文学练习的那时候有。
记者:“废寝忘食”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你的大学同学冯有源在他的《平凹的佛手》里说到,您写作最初,也有“走麦城”发不了的时候,1976年到1977年之间,你发疯似地写作,但总是寄出又被退回。那段岁月,你对写作产生过动摇吗?
贾平凹:写作最初,成名的欲望并不强烈,只是想能发表,那时寄出去的作品十分之九被报刊社退回来。但是,对写作没有产生过动摇。因为我读一些别人发表了的作品,常常并不满意它们的写法,我感觉我的想象力和文字要比他们好。
记者:孙见喜曾经写过,你“把那127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
贾平凹: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我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扩,又纵深掘进……我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张闳的BLOG:午夜单行道
当代著名作家“文革”作品大全(中)
1973年
8月
《群众艺术》第八期刊出诗歌:沈奇《十万矿石一把抓》;革命故事:贾平凹、冯有源《一双袜子》。
1974年
11月
诗集《放歌天安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工农兵学员平凹、和谷《工农兵学员之歌》。
佛手,是一块奇石,是平凹的一个朋友
怎么办?平凹和我还有和谷,就只好去图书馆的二层楼过期期刊阅览室。
文学引路人(转自马玉琛新浪博客)
闹话少说,言归正传,说说引领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三位老师。
一位是张书省老师,第一个给我们代写作课的老师,偏重于散文。曾带同学们去临潼参观华清池和烽火台,回来后布置作文,有位同学以烽火戏诸侯为题,写了篇散文,发思古之幽情,张老师大加讲评,于是大家便去写散文。
第二位是冯有源老师。冯老师求学时和贾平凹,和谷一个班。三驾马车,一驾去了出版社,一驾去了市文联,一驾留校任教。出去的两驾,已经很有些文名了。
冯老师讲课具有煽动性,煽惑得我们一拨人又去写小说。当时形势,七七级做学问,七九级搞创作,而且蔚成风气。
冯老师当时住在食堂后边像刚遭过地震的危楼里。楼梯斜斜的,楼上有裂缝。这个楼后来因为延艺云的电视剧而出名,叫半边楼。我当时几乎一两个礼拜写一篇短篇小说,写完即拿给冯老师看。每次踏上半边楼歪歪斜斜的楼梯,心就突突地跳,既怕楼塌了,又怕冯老师批评我不长进。冯老师很是耐心,对我进行专项训练,一段时间专攻环境描写,一段时间专攻肖像和心理描写,一段时间专攻性格描写,一段时间又攻故事情节……就这样,一来二往,熟了。熟了就有资格混饭吃。当时冯老师是一头沉,师母在山阳老家,平时爱情不上,师母便托人稍些家乡的土特产,其中有各种豆子。冯老师自己生炉子,熬红豆稀饭。碰上了,喝两碗。我的写作基本功,是冯老师手把手教成的。临毕业时,我发表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就是冯老师推荐给和谷,发表在《长安》(美文前身)杂志上。我和冯老师,一直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冯老师退休后曾谦虚地说,他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却教出来几个好学生,譬如方英文和马玉琛。
我西北大学的同班同学、著名作家贾平凹得知我写《黄河滩》后,欣然命笔.给我题写了书名。我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和谷也是全国有名的作家,他对《黄河滩》初稿也提出过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对老师和同学的这些宝贵支持,我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黄河滩》是丑媳妇也罢,俊媳妇也罢,现在终于要见公公婆婆了。不管公婆如何品评媳妇,媳妇只有洗耳恭听的义务,没有拒听犟嘴的权利。崔正来2009年12月14日凌晨于西安市南郊东八里小区
我与柳青散记(之六)下 作者--李孑(2007-03-2314:50:33)转载▼标签:作家大院柳青李孑 分类: 特约《作家大院--李孑专栏》
没有了的去处
当我还在斗批改监禁受审的时候,省木偶剧团和许多单位,就跑去要求调我或借我工作。他们不识时务,当然碰钉子了。其实,从我下放走后,直到出监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他们就到处奔波,想要调我去工作。但因为我是个天不管地不收的老广,广大下放干部,流浪汉,无业游民,到处支差的马仔车夫,一来不知下落,二来找不到头绪,不知归谁管,去哪里请调,县上无权不管,省上没有部门对口,因此打听在斗批改以后,毫不识相地就去碰壁了。
此情暂且不表,就说我重回渭南,重到双王大队,领导组织写剧本写村史以后。西大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的正副组长郑定宇、陈惠钦,带着八个教师(包括新疆大学的两个教师,一个哈萨克族的教授),还有20个学生,直奔我而来,开门办学。
这是西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期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要闯新路,他们就在两个班一百多名学生中,挑选了20个有志进行文学创作的学生,到双王开门办学。其中包括贾平凹、和谷、李志慧、张书省、冯有源等等。平凹因为突然有病而没有去成。
此前,我与西大中文系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受省委宣传部之命,组织领导西大教师石昭贤、郑定宇、师大教师畅广元、业余作者李小巴、周竟等,深入合阳,澄县农村,去写三史,两个月完成了一本书《血泪话当年》。第二次是组织雷抒雁等8个学生,深入宜君县写了一组报告文学,《延河》发表。两次成果可观,出人才了。所以郑定宇他们此番奔我而来,目的任务明确。
我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犹似“义工和保姆”,从衣食住行到选题选人、深入釆访、酝酿构思、草拟梗概研究提纲的全过程,直到初稿完成、讨论修改、最后定稿,方方面面都服务得非常周到,很受大家欢迎。因此,有人希望我去西大教书,中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广大师生都很赞成。但要试讲,让大家听课后再定。双王是他们一个教学点,各科教师都要来此上课,并参加了我那并非正堂的讲课。
中午吃饭时,郑定宇突然通知我下午给他们讲课,内容自定。我毫无准备,也不明其妙,又不得不从,就答应了,当然是关于文学创作。下午两点开始,我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关于艺术感受、艺术提炼、艺术构思 、典型化的过程等等,完全是他们没有听过见过,书本上没有的话语,同学们很感兴趣,要求晚上再讲,故而又讲了两个钟头。这个突然袭击,颇为惊人无不点头。
冯有源教授墓表
(2013-09-03 00:21:58)转载▼标签:刘炜评过从母校享年色温 |
冯有源教授墓表
先生讳有源,陕南山阳人也,生公元一九四六年四月。垂髫即慧才颖现,渐长有四方之志。一九七二年春,负笈西北大学专修文学,卒业供职中文系,研授辞章之学。越数岁,携家徙晋南,敷教武警专科学校,逾十秋复返母校,为写作学教授以至荣休。公元二零一三年七月病殁,享年六十又七。
先生妙有姿容,仪态轩昂,心宅悃诚,吐属清举。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俱有懿范,知者共仰。职守上庠凡三十馀载,治学勖勉,行止方正。其累岁著述也,体涉艺文、学术两域,神思畅达,叙议熨帖,笔致圆转。其作育人才也,倾尽心力,言色温煦,循循善诱。于文学少隽,扶掖点化尤多。秦中文坛当世英杰,出乎冯门者甚夥,靡不感念沂水深恩,而先生歉然曰:“我寂寂无名,大我名者,实诸子也,忝为人师,浮生何幸!”贤长敦厚襟怀,於焉可徵。
先生既殁,平生知交得悉噩讯,咸来吊唁。治丧甫毕,公之哲嗣昆仲泣云:“聊备薄席,恳望同往。盖先君大行之际,尝有嘱焉:‘身罹沉疴,自分不治。一夕解脱,毋为我哀。顾念三载之间,屡劳友朋、同事、弟子探慰,挚情厚谊,圹中不泯。今兹永诀,不克自谢。故命汝兄弟:葬我之日,就便设席,出吾家所贮佳酿,代我奉觞诸君,以完乃翁谢意。’”二子语未讫,闻者莫不泪下。
呜呼,天道有恒,人寿无常;阴阳相隔,生死渺茫,此诚莫可奈何者。然先生出僻壤而发奋蹈厉,专志业而优游文学,为硕师而桃李满门,今兹原其趋好,察其生涯,如愿以偿盖十八九,故秋年驾鹤远逝,自无可抱憾焉。
不佞与先生为乡党并同事,过从也久,相知也深。其二子慎终追远,嘱予为墓表,略述先生志行。乃概其德业情性如右,以告于冯门后人,并申平昔游从者缅思。癸巳年初秋,邑人后学刘炜评撰。
公元2013年9月1日
我的恩师冯有源
程玉宇
时令正是中伏,天热得几乎把人都能烤熟。那天下午,我早早回到我那居住在乡下的拥山庐里纳凉。才洗了个澡,正准备作画呢,突然听到立志打来电话说:“玉宇,你知道不,冯老师昨天四点多钟过世啦!”
我听了大吃一惊,又怕是听错了,急忙又问:“我前几月到西安还去见过冯老师,老师虽然很瘦弱,可精神还好得很,怎么就过世了?立志,你胡说哩吧?”
“我能哄你吗?这是啥事?真的,冯老师不在了!”
我的恩师,你真的走了吗?我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稀里哗啦流了下来,心中的悲哀如长江的浪涛一波涌来又涌起一波。
我呆坐在院内白玉兰树下的竹椅里,眼泪一直流个不停。妻子从屋里出来拾柴做饭,见我那样,就慌慌的问:“老程,你咋啦?”
我忍不住悲痛哽咽地说:“冯老师过世啦!”
妻子也一下愣在当地,手中的柴火掉的满房阶上到处都是。
冯有源,我的恩师,我文学的启蒙导师。可以说,如果没有冯有源,就没有我程玉宇的今天。
一九七九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暗淡和绝望的日子。那时候,农村青年的出路,除了当兵就是当民办教师。可我去当兵,都准备体检了,我们村的头儿对我说:“你是中农,贫下中农的子女都当不上呢,还能轮到你?你回去吧!”我去考民办教师,都考了全公社第二名,可却因为村头儿的一句话:“那小伙整天在屋里写反党小说,还能让他当人民教师?”。结果,我当教师的梦又黄了。我苦闷至极,更是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白天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抬石头、拉架子车,出着牛一样的力气,晚上则点一盏煤油灯瞎摸胡撞的写什么长篇小说。可怜一个文革中的高中生,肚里能有几点墨水?而且对文学创作一窍不通,更苦闷的是连一个同道也没有,又与谁去探讨?
初识我的文学启蒙导师冯有源,是一九八0年的冬天。
那一日,大雪纷纷,四野茫茫,天地一白。我穿着一身黑布棉袄黑布棉裤,正在权塬村一位忘年之交家里交换书籍,突然我那位老朋友说:我听说你成天在家里写东西,写得咋象?
我说:瞎胡写哩,我现在最迫切的是想找一位能教我写作的老师。
那位老朋友突然一拍大腿说:有了,我们这塬上有个武家的女婿叫冯有源,听人说他与贾平凹还是同班同学哩,正在西北大学教书,大前天才从西安回来!
我听到这一消息不由得一阵惊喜,仿佛一个人正疲惫不堪的行走在一片漆黑的旷野里,这时突然看到前边不远处有一户人家露出一线灯光。那份喜悦,好份激动,真是难以尽述。
于是,当日下午,我就冒着茫茫大雪,跨过那条瘦弱得仅剩一痕的西流河,去了冯家湾,经直走到了冯有源老师的家门上。
那是三间瓦房外搭一间偏厦灶房的黄泥小屋。老式的方格木窗,粗糙脱落的墙皮,以及院里几株早被积雪压得弯曲的花木,更可爱的,则是院落前有一窝绿竹,白的是雪,翠的是竹,在雪地里显得格外摇曳多姿。
看见门里正有一位大嫂在搓着草绳,我便怯生生的问:冯有源老师在家没有?
有源!那搓绳的大嫂忙向里屋喊了一声:有源,有人找你。
这时,就见从屋里走出来一位眉目俊朗,身材颀长、穿着一身中山装,颇有一副书卷气的中年人来,他急忙将我请进里屋,在火盆边坐了。然后我才忐忑不安的说明了我的来意,并自报了家门:我叫程玉宇,是咱三里乡红椿沟人,与你还是乡党哩。
冯老师高兴的说:好,好呀,这么多年来,咱山阳的文学一直是个空白,你有这份心恩,就证明咱山阳今后还有希望。我最早在马滩教书,后来,到咱县剧团当编剧,再后来便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与贾平凹、和谷在一个班,而且我们三个关系最好,可两个朋友都有出息了,我虽然也发了几篇小说,到现在还是个助教。不过,在我教的学生中,有一个镇安娃方英文,还有一个叫马玉琛的,他们也都爱写……
有共同爱好的人,灵魂无疑是相通的,而语言,则是表达灵魂与学识的一种载体。冯有源老师学富五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无所不知,因此一说到文学,便神采飞扬,侃侃而谈,而他最推崇的则是俄罗斯文学,如契诃夫、艾特玛托夫、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以及那位出版了长篇四卷本《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而冯老师借给我的第一本书,便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著的《金蔷薇》,因此,直到如今,我还能清楚的记得那本书中其中的两句话:生活,就象含有金粉微粒的泥土,只有经过无数次的筛选,无数次的积累,集数十年如一日,才能铸成一朵美丽的金蔷薇。
于是,就在冯老师的三间黄泥小屋里,在我那红椿沟竹溪边的茅屋中,我和冯有源老师往往围着一炉炭火,热一壶柿子酒,闲侃神聊得不辩晨昏。谈得夜深了,便抵足而眠,形若弟兄。亦因此,我才知道了中国文坛那些知名人物,并因此了解了陕西文坛和当代文学的趋势。从此,我才深深的明白:自己一开始什么也不懂,便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浅薄无知!
冯老师看了我许多手稿,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玉宇呀,你这路子不对,要写,就写你最熟悉的生活,写你最了解的人物。别小看小小说、小散文,那是螺丝壳里做道场,文章越小越难写。因为在小小说、小散文里容不得有半句闲言碎语,甚至一个多余的字和词。他又说:搞创作有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你现在面临的处境正是创作的第一境界,也就是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写什么?什么东西才可以写成文章。因此,你必须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适合你自己的文学语言,去表达和营造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随着与冯老师的日益交往和密切了解,我也因此奔赴长安逛了几回,并经他介绍认识了贾平凹、和谷以及当时还在商县文化馆当创作干部的郭景富(京夫)等等一些名人。于此同时,冯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本县的几位同道,如当时还在县剧团当编剧的孙庆义、在文化馆当创作干部发过几首民歌体诗的武治芳,以及收集民间故事和“孝歌”成瘾的陈文彦。更为有幸的则是,贾平凹因《商州初录》出版后,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心情十分郁闷,他便与何丹萌二回商州,写作《商州又录》,当他听到冯有源的介绍,说山阳县还有我这个人时,便专门捎信到红椿沟,叫我到文化馆的二楼找他,并让我作向导,去看了十里刘氏沟的九样树,去苍龙山看了丰阳塔,游了佛爷洞。又在色河、十里、高坝一带的金钱河畔和银花河畔,乱走了一通,并应我的邀请专程到红椿沟我老家的陋室去,喝了一回酒,打了一顿关,当时作陪的还有朱宪锋、贾怀林、陈学友等人。那年腊月天,我引着两位著名作家和剧作家到外闲逛,到处喝酒,但不管白天怎样游山玩水,怎样胡说八道,而一到晚上,贾平凹在他的笔记本上,则必定是要写一篇小散文的。于是,我们就一边抽烟,烤着火,还要嗅着那种难闻的温醋气味(贾平凹说那种醋味能治感冒),听贾平凹宣读他的又一篇《商州又录》散文,听过了,我们便忍不住一阵哈哈大笑,就说:你又在糟蹋商洛人哩,小心人家又批判你!贾平凹方正色说道:难道这不是商州吗?难道商州老百姓不正是这样生活着吗?
正是我与冯有源老师相识,他又让我认识了贾平凹等文坛大腕,才是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
后来,我的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便相继在《陕西日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百姓故事》、《散文选刊原创版》、《延河》等刊物发表,甚至还有作品被中央电视台选播,并有数十篇文学作品入选各类文学作品集。
我从一个单纯的农民,成长为山阳作协主席。并且为谋生计还当上了山阳县148法律服务所的主任。为48位患上了尘肺病农民工讨公道一案,我还有幸还被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并被评为商洛市优秀法律工作者。如果说,没有冯有源老师对我的教诲也就没有我程玉宇的今天。
那一日下午,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回忆着我与冯有源老师交往的种种往事。
恍惚见,我似乎听到冯有源老师在门外喊我:“玉宇,玉宇,你在家吗?”
我激动得站起身来说:“冯老师,你快进屋里来!”
冯老师说:“我是来给你先打声招呼,我要回冯家湾呀”。
接着,我仿佛听到冯有源老师离开的脚步声,我扑出门去,门前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我突然惊醒过来,哦,原来是冯老师魂归故里,要回到他的故乡去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