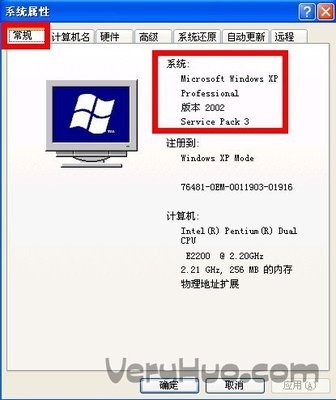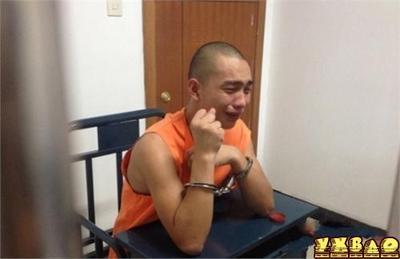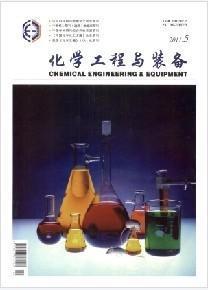有这样一座城市,它矫情,它做作,它婀娜,它更像是霓虹灯下的影子,舞曲里的音符、半截子的旗袍,它生来被文学赋予了文化意义,它就是上海,这个与文学似乎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城市。
这个城市天生是被注视的,这个城市的人也是天生被注视的,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荣耀。王安忆《长恨歌》就是在注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传奇。
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在上海的弄堂里出生,在上海的闺阁里成长,在上海的选美比赛上获得了上海小姐的称呼,在上海遇到了第一个男人,在上海开始长达40年的情和爱,直至在上海可悲的死去。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一个上海小姐身上,所以注定了,就是传奇。
王安忆用过于冷静的口吻以隐形的叙述者自居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上海女人的故事。女人是故事的核心,必定的。既是女人,我们习惯用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去放大这部作品,但是换来的是失望。于是我们又用女性意识的理论去窥视这部作品,终于听见稍许的女性的声音。最后我们再拿起书读,发现大段大段的关于上海这个城市的议论与描写。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王安忆到底是在讲上海,还是王琦瑶呢?
王安忆在提到《长恨歌》的时候曾说过:“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
王安忆也曾经说过:“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2]这个再造的自然便是城市。在城市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女性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她们较男性更易适应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快地与城市融为一体。女性与城市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王安忆选中女人作为都市的代言人,以女人的命运演绎城市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她的笔下,城市就是一个女人。
本文将通过《长恨歌》来演绎这一“城市=女人”的命题,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考察《长恨歌》中的女性声音,作者是怎样用女性意识来表达一个宏大叙事的主题——城市的历史。
上海印象
上海,正如张爱玲说它,“满是沧桑的繁华”,大概在繁华的背后总是有一些岁月的伤痕,带着历史的沉重感,这是一个形容上海比较妥帖的说法。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是如此,上海成了一个彻底的石库门式的符号,是一种对逝去以往的怀念和珍藏。这个符号在《长恨歌》里是二维的,既具有空间意义,也是具有时间意义的。
空间的:地上的弄堂——低空中的闺阁与流言——高空中的鸽子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长恨歌》
《长恨歌》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即为上海的弄堂。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弄堂是上海的雏形或者是浓缩,它不是生冷的建筑物,而是成为了人一样的存在,性感感动。它是这个城市特有的风景线,是这个城市积聚的人气的所在,是聒噪而又亲切的暖意。接着,王安忆介绍低空中的流言,流言阴冷般地在弄堂里蔓延,附着着想象与偏见,筑就了这个弄堂的历史。再是上海人家的闺阁,小姐的居住间,不安静也不阴冷,总是浮着一层喧哗,一层向现代过渡的突变。再是高空中的精灵——鸽子。在王安忆的笔下,鸽子成了这个城市的俯视着,它察觉到人间的一喜一怒,察觉到这个城市一冷一暖。接着,上海的女人出场,王安忆说到处都是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是上海女儿的代言人。上海女儿在弄堂成长,在流言里聒噪,在闺阁里寻春,在鸽子下徘徊惆怅。
上海弄堂蜿蜒曲折,狭小绵长,像一张密集的网一样在这个城市的一角慢慢编织。这个弄堂有着一些小家子气,或者更准确说是带有一点雌性的味道,表面停滞凝固,却有一颗不安的心。再说流言,“是女人家的气味”,是带有一点闲言闲语的琐碎的,就像身上的大块色渍拼凑构成的旗袍,看似正确的,哪知道也是拼凑胡诌的。女人自然挺爱干这种事的。再说闺阁,更只是女儿家的,而上海的闺阁又是不平静的,因为已经有了摩登的味道,有了卷发,有了岔开的旗袍。鸽子虽是一个意象,是这个城市的“温柔”的见证者,他们有些悲伤的色彩,又带有一些忧郁的特质,还是挺女人的。总之,第一章一直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是个女儿家。
此外,在对上海的空间构筑中,行文有一大特色,就是带着一种非常主观的倾向。王安忆不顾别人对上海的感觉,而是直接采用判断句型“某某是某某”的主观判断结构全文。例如: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流言是混淆视听的……王琪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可以说,这些繁多的判断句式构成了作者 笔下的上海弄堂景象。作者用近似下定义的手法夹叙夹议地表达出自己眼中的弄堂。这种句式则为大多数作家不屑于用。说白了,这是近似于小学生的笔法,易让人有堆砌之感,有固定思维之弊。正如作家余光中所说,滥用“的”字原是白话文的大忌;而滥用判断句更是小说语言的大忌。这么说来,王安忆犯了“大忌”,且同时犯了两个。但这样的句式由王安忆用来,却是得心应手。这么说是因为:连绵不断的判断句式朝读者迎来,让人体会到上海弄堂世界里那种特有的舒缓,想到“吴侬软语”的调子,与《长恨歌》里的叙事空间十分符合。可以说,作者的“忌”犯到了点子上,得到了独特的效果。
时间的:四十年前的起点——其中的四十年——四十年后的终点
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长恨歌》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王琦瑶四十年的情与爱,这四十年囊括了从去片厂的那一天直到王琦瑶的死去这一大段时间,在小说中被划分了3个部分。
王安忆先从四十年前说起,在第一章中由弄堂带出了闺阁,由闺阁带出了王琦瑶,王琦瑶也就这样诞生出来了。其实不止一个王琦瑶,而是所有的上海女儿的传奇也一并出来了。在四十年前,王琦瑶去了片长,看到一个在床上死去的女人,王琦瑶的感觉是旧景重现。伏笔已布下。
再说这四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从默默闻闻的一个上海女儿一跃成为上海小姐,借着上海小姐的桂冠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王安忆简略地摘录了报纸上的新闻,比如淮海战役等,暗示了时代的变迁。王琦瑶不得不避乱去了邬桥,后来又去了平安里。平安里在关于严家师母的介绍中又暗示了时间,“产业都归了国家”,说明是解放后的事了。第三部分薇薇的长大,直接将时间从1966年推移至1976年,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了。
漫长的四十年之后的临界点,王琦瑶就悲惨地死了,她发现四十年看见的那个死去的女人,原来就是自己。这四十年开了一个大玩笑,从起点到终点,首尾相接,一场空空也。王琦瑶有些带着绝望的死去。这个城市,鸽子继续带着哀号盘旋,城市继续存在,它从曾经的喧哗的纸醉金迷的旧上海到解放后安于平淡素净的上海再到现代改革开放后又一次骚动不安的新上海,这是时代的变迁,也是这个城市的变迁,却全从一个女人的故事中拉扯出来。
此外,阅读《长恨歌》,每当我们沉浸于主人公故事中时,字里有关这个城市时间的交代,是如此之不经意与别有用心。“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一九六五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八十年代初期,这城市的时尚,是带些,埋头苦干的意
思。”随着作家的笔触,我们阅读到了王琦瑶近半个世纪的一生。城市时间像是泛着古色的座钟,安然、挺拔地立在原地,铛铛铛的报时,提醒我们:嘿!现在是XXXX年了。在卑微的个体生命里,它具有宏观的历史意味。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王琦瑶对于时间实在是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当王琦瑶不再年轻,周围的人却觉得她是“没有年纪的”。没有年纪又怎样呢?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
有关于时代与个人的精辟论述:“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时间,常以不经意的方式,贯穿《长恨歌》的始末,伴随故事主人公的始终。它串起了王琦瑶点点滴滴的生活,带走了她的青春年华与如花美貌,安排着她的情人出场与入场,更是为她老时缅怀积蓄着点滴凭证。
女人王琦瑶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长恨歌》
上海的女儿就叫王琦瑶,她们共同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成长于繁华的旧上海,她们见惯了灯红酒绿,她们见惯了车水马龙,她们也见惯了她们的故事。所以她们天性有一种能张能驰的特性,对一切一笑置之的风度。她们无法逃离这个城市,因为她们属于那里,避乱只是一个短暂的借口,在她们眼里这个城市就是她们的宿命。王琦瑶就是这样。
王琦瑶在漫长的四十年里,她依赖这个城市而存活,依赖这个城市而获得生存的意义。这个城市的情和爱也就是她的情和爱。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再到阿二、毛毛娘舅、萨沙,再到老克腊,男人走马观花地来去,与王琦瑶发生一段段故事。王琦瑶还是故事的中心,也就是说女人还是中心。
一个人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在女性主义观念里,声音的发出与否有时关系到女性个体的生死存亡。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声音是指叙事中讲叙者的话语,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人物,专指文本实践中的具体形式。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探讨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集体性叙述声音。显然的,在《长恨歌》中,发出的是作者型叙述声音。这种声音因为出自一位女性作家,就显得细腻动听。王安忆作为一个潜在的叙述者,她所在的立场绝非是女性主义的立场,至多只是女性意识的立场。
我们看《长恨歌》的故事,女人虽然是故事的中心,也占据着半壁话语,但是王琦瑶在每个男人前面多少带有一点依附性,表现出一种女性天生的柔弱。我们没有从王琦瑶身上看见女性独立的影子。再看王安忆笔下的男人,除了李主任若算是一个绝对的例外,那么其他的男人,要不软弱无能,要不逃避责任,要不远走高飞,王安忆就在这样的边缘地带行走,她不歌颂女人,也不赞扬男人,她是绝对的冷静的观察者,是典型的边缘叙述的模式。
虽然没有赞扬女人,我们没有看到女性主义的身影,但是女性的影子却是在王的笔下比比皆是。从王的文字看,是完全女性角度的叙述,带着女性特别的忧郁与伤感来娓娓絮叨这个故事。小说语言注重“向内转”,即由外指向的语言转换为内指向的语言,由以语法、逻辑为准则的外部语言转化为以语词、意象为中心的内部语言。王在形容王琦瑶的时候,不经意流露出来女性的特质,这也是只有女作家可以驾驭的。比如说对王琦瑶的服饰描写,对王琦瑶时尚嗅觉的描写,都只能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而且都在带着些很摩登的感觉,是上海特有的气息。
所以,故事是女人的,语言是女人的,小说也是女人的。
宏大叙事的女性化消解
由于上海与王琦瑶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的流露与其说是王琦瑶的,更妥帖说还是上海的。上海与王琦瑶成了一个镜外与镜内的两个主体,王琦瑶是像,上海是实体。用一个女人表现上海,王安忆采取的是女人的日常化的叙事。
西蒙·德·波伏娃曾经指出:“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们不以任何激进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抗。”[3]
在波伏娃的阐述中,妇女被这个世界的权力话语边缘化,成为“男人的世界”的陪衬和点缀,同时选择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自我放逐。这就导致了另外一种思考世界和历史的可能——不同于男人世界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边缘化的日常生活化的解读。正如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她强调日常生活的描写,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流露出的平安、细致、活泼的人情味”。而对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她则更坚定地认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王安忆强调:“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而在日常生活这一点上,王安忆看好女作家的创作:“男性看世界往往是大处着眼,对思想的期望过高,而女性比较流连于具体的人和事……她们看似从小处着眼,其实呢?那正是生活的本身”。[4]
《长恨歌》,就是对她这种重视日常生活的创作理念的积极践行。王安忆讲究的是一种“日常化”的叙事策略,日常化的写作立场是指在主题的选择、人物情节的确立以及语言的应用等方面尽量避免大事件、特殊人物、曲折情节以及特点显著的语言方式,而选择用日常的语言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种创作立场。其目的是从事物日常的状态中寻找它的真相。王安忆说她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我对历史也有我的看法的,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
的,我们现在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5]

在《长恨歌》中我们闻到了油烟弥漫的市民生活芯子里的气味,琐碎与平淡,或许,这就是家的温馨。在她的眼中,吃饭穿衣、打麻将、围炉游戏、猜谜语、打针吃药,这些最琐碎最细小的生活才是最永恒的事情。这种芯子里的味道,才是上海的味道。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常化的叙事,在王安忆的笔下却又是与众不同的,而是艺术化的,这艺术化的手段构造了一个美化的生活空间,许是带着些节奏和音符的,生活不再是琐碎,而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的,如吴侬软语般啰嗦,这也是上海的特质。
于是将上海的历史承载在一个女人身上,承载在一个女人琐碎平常的生活点点滴滴中,是构成了对这个宏大叙事主题的的女性化式的消解。
是王琦瑶,还是上海,其实都不重要,因为王琦瑶是上海的女儿。作家独特的视角,将上海看做一个大女人,用日常化叙事来表现她。王安忆的《长恨歌》告诉我们:上海,不是你所看到,所想到的样子,要看得真切,就要到她的芯子——弄堂里来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