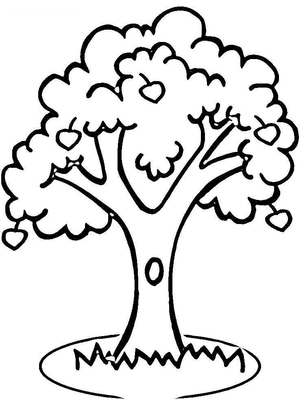洋槐树
家乡有好几棵槐树,那是家槐,又叫药槐、槐豆角,槐米树。槐树是一种很低调的树,它们个头不高,也不急着生长,混杂在其它树中,常年不声不响,好在他们棵型紧凑,浑浑圆圆,也算有几分模样,但也只有在夏天摘槐米时人们才会想起它。有家槐就有洋槐。洋槐有一个“洋”字,自然是外来物种。听说这树是美洲树,美洲在太平洋那边,太平洋与美洲在哪儿,大家都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那地方遥远得与天边差不多。不过洋槐树在清朝已经定居中国,已经本土化,因极强的本土适应能力,一百多年就成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大家族。
不知为什么,一想起洋槐树,我就想起我三娘。三娘是随州人,她的穿着打扮与我们村的女人都不一样,尤其是她说话时,好似总翘着舌头,发出软软的腔调,都说那是洋腔洋调,开玩笑时说那是浪腔浪调。但三娘既好看又能干,跟三伯很一心。洋槐树与三娘一样,一嫁来就与我们那里铁了心,一副随高就低的模样,她好地害地一样长,坡岗石缝都能活。而最关键的是,它的木材弹性好,是做钩担,架子车的好材料,而它的枝条含水少,稍晾几天就成了烧锅的好柴火。但它有一个毛病,就是树枝上长满了刺,一不小心就会扎着手。至今我仍能感受到奶奶烧锅的情景。奶奶会坐在锅台前露屁沟的椅子上,小心一根根往灶火添柴,她望着洋槐枝燃起的欢实的火焰,就像欣赏火焰表演一样,嘴里发出“真真好柴”的赞叹。那时父亲不在家,妈妈是一个大忙人,走路就像一阵风,如果奶奶没有时间烧锅,妈妈只好慌慌张张地一边掌锅一边烧火,往往被槐刺扎着,痛得只“哎哟”。

乡亲们能够接纳洋槐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槐花与槐叶。一棵洋槐树,六七岁就会开花,等长到十七八岁就会出落得漂漂亮亮,它的树冠浑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一串串叶子很懂事地排列着,在疏落中从从容容。由于每隔一年就要砍树枝摘槐花,从砍断的树枝上就会发出数十根枝条,每根枝条当年就会长一丈多长,使整个树冠密不透风,树冠里也就成了小鸟藏身的地方。在洋槐树下歇凉荫,往往只能听到鸟们唧唧咕咕的叫声而看不到一只鸟,往往能看到树枝乱动弹就是不见鸟,看着看着,从树上慢悠悠飘下一根鸟毛。其实,像我仰着傻脸久久看着树枝的只有小孩子,大人是没有这些闲心的,如果有人盯着一棵树看,那棵树一定是一棵老古树,在农村老古树一般都有奇奇怪怪的传说。
与其它花不同,槐花是在乡亲们的期盼中慢慢开放的。当春天槐树刚刚发出嫩叶,还是一树的青黄,那些槐花裹着一层青皮悄悄隐藏在树叶间的时候,乡亲们的心中已经闪亮出槐花细碎的银光,伴随着槐叶的一天天舒展,槐花穗子也在人们的心中一天天饱满起来。槐花的第一次开放有点神秘,它会在某一个夜晚借着暖暖凉凉的春风,突然让整个田园与村庄弥漫着一种独有的清香,好似它的清香就是槐树的一种无声的语言,想向乡村诉说着什么。而在这清香中很多人就会在睡梦中醒来,又在模模糊糊中梦一样让思绪走进一片片槐花的海洋。第二天很多人可能会起得很早,匆匆走出自己的院子,第一眼就看到的就是一树树洁白心事。也就三五天吧,槐花就会在发狂的春风中洋洋洒洒,卷起一堆堆耀眼的气势。
在我小的时候,人开始最关注的花是葛花而不是槐花,葛花就是紫藤花。葛花会开出成串成串的蓝中带紫的花,而且那花是一道美食。水淖之后,凉 拌,清炒,煎炕,或拌上腊肉与玉米面蒸菜,都让人流口水。葛花水淖后晒干,还是上等的干菜。但自从来了洋槐花,洋槐花就把葛花比败了。葛花虽有独特的味道,但没有洋槐花的柔嫩,也没有洋槐花清香中的甜稍。尤其是晒成干菜,葛花吃着有点柴,而洋槐花依然嫩软。
洋槐花的叶片是很规矩的椭圆型,看着让人舒服,但乡村一般不太喜欢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洋槐叶却是很好喂猪的饲料,听说那里面蛋白质含量很高。在我小时候那个苦难时期,没有多少粮食,猪都是清汤寡水涮大的。在没有饲料的情况下,有人就试着捋洋槐叶,晒干揉碎,猪竟大吃二喝,长得毛光水嫩。从此人们就春天摘洋槐树的花,夏天就捋洋槐树的叶,眼中的洋槐树总是光秃秃的。但洋槐树好似一点也不在乎,要不了多少天,就又抽出了枝条,长出了浅黄的嫩叶片。
洋槐树不愧是家乡的好树,她很像一位白胖而勤劳的农村少妇,那是家乡的好媳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