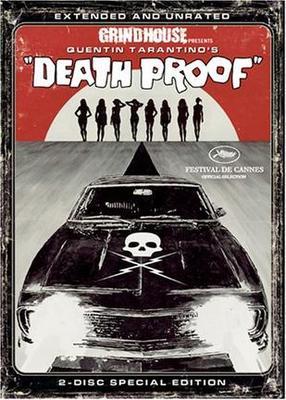历史学家的技艺的评论
一
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被誉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该学派的学术刊名均有“年鉴”二字,便由此得名。年鉴学派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相对。实证史学是自然科学神话的产物,它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然而,史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实验可以重复,而历史一旦流走便不再回头,时间、空间都无法再次交汇。在意识到实证史学的局限后,布洛赫率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观,这便是其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主要动因。布洛赫笔下的新史学是以大历史观为指导的总体史(UniversalHistory),这样的历史不论在宽广度,还是纵深度上都要大大超过前人。
二
横向来看,年鉴派扩大了旧史学的视野。已往的史学总是关注“帝王将相”的故事,其研究重心在于上层的、中心的、大事件、大人物,关于这一点只消考察历史时代的划分便可知晓。正如布洛赫所说:“时代的划分往往以统治者的更替、王朝的征服为界……在民族史中,国王的更替就成了分期界限……当历史上不再有国王时,人们就以政府为线索,好在政府也是会倒台的,于是革命就成了历史分期标志……”。根据上述线索所书写的历史必然只能是精英史、政治史,布洛赫所要做的正是打破旧史学的这种局限,他试图把历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用后 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扩充了史料的来源,使原本看似平常无奇的数据、文件、书信,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作用。传统史学多以政府公函、前人史学家所著史书为史料,日复一日地研究这些历史学中滥用的“经典”,只能将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只有充分重视现有的一切历史文书、文物,才能将史学引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外,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将史料分为“有意”的和“无意”的两类,虽然“有意”的史料往往比较有名、具有相当的价值,然而在布洛赫看来,显然是“无意”的史料更为可靠。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给与历史学以更广阔的学科基础,使之不那么固步自封,它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联系。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提及涂尔干的社会学,他认为历史学可以从中受到重大启发。其本人的代表作《国王神迹》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他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
“从阁楼到地窖”的转变,为分类专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毕竟象牙塔里所能容纳的东西只能是极少数的。布洛赫将专史定义为历史的专业化,即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他认为,只有对现象加以分类,才能弥补人类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欠缺,才能充分揭示主要的历史动力。新闻传播史,作为历史专业化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
纵向来看,年鉴派延伸了旧史学的跨度。布洛赫指出:“……我们的研究证明,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决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名为:“1587,AYear of NoSignificance”,正如该英文名一样,1587年实在是历史长河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年,几无大事发生,然而,正是在这一片寂静中,他发现了数百年后导致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源——以德治代替法治的传统制度。黄仁宇这种“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重新检讨”的角度和方法,正是年鉴派所倡导的。
布洛赫说:“整体比部分更有确定性。”这一观点被年鉴派的接班人布洛代尔发扬光大,他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环境,环境变化虽然缓慢,却渗透到人类所有的活动中;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需上百年方发生变化;短时段对应得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他还说,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显然,局势比事件要稳定,而结构又比局势更稳定。
稳定的结构和非稳定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就自然引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的偶然性究竟如何界定?又或者历史有没有可预见性?历史的偶然性针对的是事件,而历史的预见性则是针对局势乃至结构而言的。布洛赫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价值,然而,造化弄人,正当他着手对其进行具体论证时,他却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枪杀。学者所留下的未解之题是学术界的遗憾,而学者本身的惨死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布洛赫未及完成的第六章“历史的解释”和第七章“论预见”,原本应当是最富创见的思想,我们现在却无缘详尽了解。然而,仅其留下的关于这些话题的提纲就足以成为年鉴派,乃至新史学至高的新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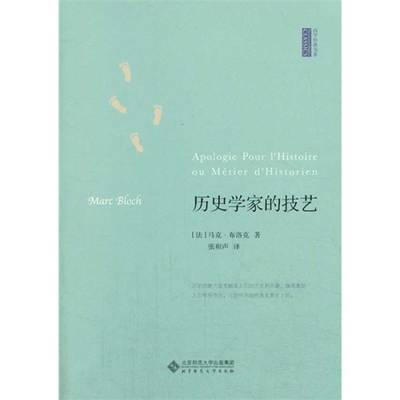
四
布洛赫所强调的总体史,经过其后的年鉴派学者发扬光大后,却走向了极端,产生了异化。前面提到的布罗代尔由于把过多的笔墨放在长时段,而忽略了对事件的关注,于是,有人就批评说,布罗代尔的历史中没有“人”。如果布洛赫尚在世的话,面对这样的指责定会失望之极。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简洁果断地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作‘人类’吧。”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离开了人——这个史学的基本要素,再宏大的叙事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优秀的史学作品都少不了生动细致、真实可感的人物刻画,还是举《万历十五年》为例。该书每个章节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展开,通过对其人其事的叙述来展现时代的特征以及民族的特性。作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章中指出“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而他运用在该书中的历史写作手法正是他对于这一准则的亲身实践。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正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一味地强调事件,会导致见木不见林的倾向;而完全无视事件,则既无树何来林?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正是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所作的探索:一方面,他宣称,历史是一门饱含“诗意”的学科,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恢复想象;另一方面,他又格外注重对史料的应用和考证,以经验主义的作风仔细观察特定的事实。这便是历史学家的技艺——“真正的历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质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洛赫在此所作的,不仅是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更是全人类史学的宣言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