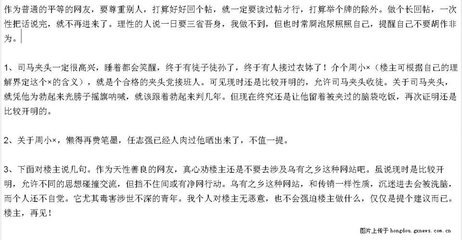中国遗传药理学开拓者周宏灏:立志如山 行道如水
立志要如山,只有如山,才能坚定不移;行道要如水,只有如水,才能迂回曲折,才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奋力到达柳暗花明的那一村。
——周宏灏
周宏灏,生于1939年5月29日,湖南长沙人,遗传药理学、临床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上世纪80年代起,周宏灏教授率先围绕药物反应种族差异、个体差异及其遗传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986-1991年,他在美国范得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以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模型和方法科学地证实了药物反应的种族差异,进而从药物代谢酶和受体基因多态性深入阐明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本质和分子机制,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研究论文因此而获得了美国Henry Christian奖,被誉为开创性的里程碑工作。1991年回国后,他继续深化这一研究,连续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三项美国医学基金项目,创建了我国迄今唯一的遗传药理学研究所,编写了4部《遗传药理学》中、英文专著和研究生教材,在国内首次为研究生开设了遗传药理学课程,成为我国遗传药理学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2005年,周宏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湘雅医学检验所所长、中南大学药理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教授。
梦想从小时起航
可能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个梦想,有的人想当老师,耕耘讲坛,传授学业;有的人想当警察,捕抓坏人,圆自己的英雄梦;有的人想当一名歌唱家,登上舞台,获得别人的鲜花和掌声……儿时的周宏灏也不例外,他也有着自己的教师梦。
周宏灏从小就是个很调皮的人,他不喜欢墨守成规,总想着能想点新问题。周宏灏的父亲周磊村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一所著名高级艺术学校的校长,从事艺术教育几十年。祖父是那个时代湖南大学的教授,母亲在和父亲结婚前也教小学,两位哥哥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周宏灏从小就喜欢教师这个行业。还在读小学时周宏灏就会拿着粉笔在家里画啊画,有模有样地给其他玩伴们教书上课。那时的周宏灏心里,充满了对老师的崇拜和敬仰,而他为自己设想的人生,也跟老师这个职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读书时,脑子灵活的周宏灏成绩就一直不错,尤其数理更是他的强项。初中时有一次物理考试,老师一反常规,题目全部要用书本理论和公式解释自然现象,比如融雪时为什么比下雪时更冷等,这次考试只有周宏灏一个人及格并且打了最高分98分。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一流学生考理工,二流学生考医农”,本来凭着周宏灏的条件,他应该选择理工科的。可是不安分的周宏灏却力排众议选择了医学,他幻想着将来能穿上白大褂给病人看病,但是当老师的初衷也始终没有改变。那时的他想着以后去医学院,又当老师,又当医生,两全其美。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1957年,周宏灏报考了武汉医学院。
1962年,周宏灏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的一家空军医院当军医。在那里一做就是七年。文革期间,全国热衷于政治运动,周宏灏则凭着一副好嗓子担任了空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就这样,上班的时候为患者看病,下了班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工厂和农村宣传演出。那是个浮躁的时代,“我斗你,你斗我”,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国家秩序出于瘫痪状态。然而,周宏灏却认为读书能充实自己的业务水平,“在没搞运动时我就喜欢坐下来看点书,看点外文的东西。”周宏灏坚信英语早晚会派上用场,于是他从图书馆借了大量的医疗文献,依靠字典,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翻译、阅读。
1978年,周宏灏有幸调入湖南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任教。1983年,周院士作为湖南医科大学临床药理国家培训中心派出的访问学者,前往香港大学进行临床药理学研究。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工作期间,留心观察的周宏灏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高血压病人,要产生同样的疗效,英国人用的剂量要比中国人大得多。那时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体重较轻,故用药量要少。但周教授却认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可能是引起药物体内处置和反应性差异的真正原因。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周宏灏决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执着成就中国遗传药理学的泰斗
在周宏灏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周院士和四个外国友人,他们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那还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还是Merck的评委呢,六个评委,这里缺席了一个,我做了八年。先是领奖学金的,后来就变成发奖学金的了。那时候整个亚洲也就是我了。”周院士指着照片,满脸和蔼的笑容。
周宏灏说的Merck奖学金,指的是创设于1965年的公益性的、促进临床药理在全球推广和发展的奖学金,每年仅从来自全球上百人的申请者中筛选出4位学者。1986年,在香港进修期满后,周院士荣幸地成为全球的四分之一,他拿着美国的Merk奖学金,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来到美国临床药理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学府——范德比尔特大学开展新的研究。在美国Vanderbilt大学研修期间,周宏灏科学地证实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确实存在。之后,他又研究发现黄种人和白种人对药物代谢和敏感性均有显著差异,通过在《新英格兰杂志》等权威有影响力的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周宏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周宏灏的这些关于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临床药理学和遗传药理学的经典研究,被国际同行誉为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经典研究”和“遗传药理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美国FDA、ICH和我国从此相继规定新药临床试验和国外药品注册需考虑种族因素。1989年,年过半百的周宏灏获得了范德比尔特大学校长赠送的“金椅子”——一把专门颁发给在临床药理学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荣誉椅,这也使他成为至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正当周宏灏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91年,时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的罗嘉典来到美国,老校长这次美国行只为了两个人而来,周宏灏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周宏灏在美国事业正兴,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遗传药理学实验室里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并且成果突出。惜才的罗校长见此情况,不敢再向周宏灏开口提回国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在那抽闷烟”,回忆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一向开朗善谈的周宏灏不禁声音梗塞。校长在周宏灏家一直呆了三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许诺,也没有声情并茂的说辞,但重情的周宏灏还是被校长的诚心和执着深深地感动了,“因情而动。不是说有三顾茅庐吗,何况我还不要他三顾,一顾就已经够了。”周宏灏动情地说。
那时国家正上演着政治风暴,国内一团糟,“没人不往外跑,没人肯回来,谁都劝我不要回国。”但是固执的周宏灏又一次力排众议,放弃丰厚的条件,谢绝同事和美国校方的多方劝阻和挽留,也谢绝了正联系他去任职的另外两家公司的邀请,毅然决定举家回国。他用简单的话语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既然答应了就必须做到,我们不说一诺千金,但至少讲话要有信用。”而他的儿子——当时在美国读高一的周淦,也放弃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回国从初三读起。“我儿子那时读书读得很好的,篮球打得很好,很优秀的,完全可以读美国最好的大学。”谈起儿子,周宏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之后,因为没有住房,周宏灏一家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三个月。在科研、生活条件降低的情况下,尽管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理解他提出的“基因导向个体化药物治疗”,但他始终坚定地依照他的科学思维,坚持不懈地埋头实验、执着探索,正如他所说的“我做事情很执着的,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我就会坚持下去”。正是因为有着如山般的坚定不移,周宏灏对国外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将药物的种族性差异研究延伸到民族差异、个体差异的研究,且都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果,促使科学用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阶段,为根据基因特点“因人用药,量体裁衣”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和实验依据。在进行个体差异的研究后,周宏灏领导团队率先研制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产业化前景的我国第一张“个体化用药基因诊断芯片”,在将遗传药理学理论应用于临床实际上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发现和阐明遗传因素引起药物种族和个体差异的若干现象和机制及其规律,周宏灏逐渐建立了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遗传药理学理论体系,并启动了以遗传药理学理论为基础的“量体裁衣”个体化药物治疗。
生活——我行我素,率性而为
进入医学院,又当老师又当医生,几经波折,中间多少艰辛多少辛酸,周宏灏儿时的梦想在他的执着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并且取得了很多超出他预期的成果。虽然声名俱得,但率性的周宏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和生活规律。“有的人要我去做一些摆谱的事儿,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的,这些都是虚的,我不去,要我名声的也不去,做实事的我就去。”周院士简洁明了地说。前几年,贵州安顺的一所中学校庆,邀请周宏灏去做演讲,他二话不说就去了,重庆一个中学搞活动邀请他去他也去了,“我愿意跟学生聊聊天,有时候给他们上一堂课,过几十年他们都会记得,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圣很有成就的事。”
从1978年走上中国高校的讲坛直到现在,周宏灏共培养了106名硕士研究生,69名博士研究生,已是院士的周宏灏还坚持给医学院的本科生讲课,“可能有点我行我素吧,但我做的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性格使然吧。”周院士亲切地笑道。周宏灏经常以自身经历来激励学生们要执着要坚持,“要使自己瞄准一个目标,长时间地、始终不渝地去探索科学奥秘……即使这个过程会很长,甚至一开始不被人理解和接受,但追求的目标不能改变,只有坚持下去,最终是会大有作为的。”朴实的话语,却让很多学生坚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科学研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在上班时,周宏灏是一丝不苟的,他讲效率,讲准确,可一到下了班,不服老的周宏灏会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学生们私下亲切地称他“灏哥”。今年临床药理研究所19周年所庆的时候,学生们还特意把时间调整到5月29日,就因为那天是周院士的生日,很多学生和自动从世界各地赶来专门为他们亲爱的周院士和曾经共同呆过的研究所庆生。在周院士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玩偶摆设,非常可爱,还有一张傩舞面具,“那都是我的学生们送我的。”周宏灏自豪地笑道。
已处于古稀之年的周院士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一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每天洗冷水浴的习惯,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坚持游1500米。唱歌、蹦的这些年轻人喜欢做的事周院士也都喜欢,“我唱美声的,我还是男高音呢,像《我爱你中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我都会唱。”说这些时,周院士的表情和语气就像个小孩子。游泳和唱歌这两个爱好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也正是这种经年不辍坚持不懈的锻炼使院士常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心情。
在做每件事时,周院士计较的不是成本或回报,而是自己高兴不高兴,“我做每件事都很高兴很投入,因为我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虽然很辛苦,但是心里非常愉快,心里愉快身体就愉快了。”周院士说的话朴实而平白,但是却极富感染力。看着院士开朗真诚的笑容,笔者心里充满着敬佩之情,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人生在世,最幸福的莫过于懂得去享受生活。如此说来,周院士无疑是事业和生活的集大成者。衷心祝愿我们的周院士能在遗传药理学研究领域再攀新的高峰,为中国临床药理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