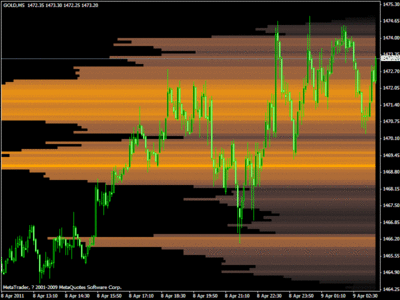陈其五的坎坷经历
作者 荆位祜
看到《世纪》杂志今年第三期上周天同志的《新中国上海文坛若干风波》,所写的事是关于长期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华东局、上海市委宣传部门领导工作的老同志陈其五的。
我很同意周天同志对陈其五同志总的评价。从他1984年去世前近五十年的经历看,他为人正直,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为受屈遭灾的干部和群众仗义执言;他受委屈多年,在恢复工作后,又全心全意、不知疲倦地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是一位值得崇敬的好干部。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不足,如工作过程中有时未全面了解情况而产生某些失误;他作为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讲话、作报告特多,难免偶有失言等,但他襟怀坦诚,知过就改,故属于金无足赤、瑕不掩瑜。
对于周文中说的三件事,前两件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有发言权,对于第三件事,则比周天知道得多一些,具体一些,可以说说我所知道的是怎么回事。
一、陈其五受打击的原因和平反经过
陈其五同志当年确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受委屈达十三年之久,但在受打击的时间上、原因上与周文所说则有出入。1961年,我曾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一同随陈其五同志去上海郊区宝山县葑溪公社蹲点,同去————的还有宣传系统的一批干部,分到各生产大队,宣传贯彻“人民公社60条”。在那里,开始还有农民食堂,后来就逐步散掉了。我没有听到过也从没有向别人说过陈其五同志曾为农民对食堂不满而上书党中央、毛主席的事。他受批判,那是1963年初的事。起因主要是在1962年,他曾对当时的形势、困难发表过一些言论。比如,他直率地认为,应该承认“大跃进”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些山区森林就遭到了破坏;甚至说“我对抽象讨论形势估计三七开不感兴趣,现在叫我写形势大好的宣传提纲我就不写了”;又比如说某地区农村遭了严重灾害,当地主要领导干部亲自赴灾区赔礼道歉;应该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对于有的工人拿了手表券平价买了手表以较高价卖出,有的生产队干部将超计划的蔬菜拿到集市贸易市场出售,不要去苛求;他还为受到不当批判和处理的同志挺身执言等等,这类言论,尽管有些是事实,尽管有些在事后看起来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正确的,但是这都和当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不合拍。1963年初市委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认为,“上海思想战线上存在嗅觉不灵、武器太钝、立场模糊的问题,而且这条战线的司令部内部也存在问题”,于是陈其五同志在上海宣传系统的干部会上,被揭发批判。有许多批判发言上纲上线,是过头的。还有人缺乏根据地揭发他攻击“三面红旗”。在当时的氛围下,陈本人3月份向市委作了书面检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看了他的检查后,在上面批示:“按此报告在小范围内检讨,听取意见,再作补充检查好了。”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持陈的批判检查会、与陈个别谈话的,一般都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他一会儿说:“你不愿意和我们团结,我们从此分手”,意即要将陈开除出党;一会儿又要陈去看反修的绝密文件,说“你可以放下包袱了”,反反复复。到了1964年秋,要对陈的问题进行处理了,给什么处分呢?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基本意见是留在党内,市委领导层内部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开除出党,一种留在党内。为此,市委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专门去北戴河,向已于1964年春肺癌手术离开工作岗位并于7月去那里养病的柯庆施汇报并听取意见。石西民带去的意见是:留在党内,作留党察看处分。柯对此没有异议。石西民回上海以后,市委宣传部有关党支部就据此于10月下旬召开党支部大会,陈其五参加,作出了给陈“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陈在会上除表示别人揭发他的攻击“三面红旗”的话自己并未讲过外,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4年12月中旬,市委宣传部突然接到市委通知,说陈因“态度不好”,应重开支部大会,开除他党籍。又把八年前陈说过的话,当年已进行教育批评、本人也进行检查早已改正的事拿出来上纲上线,说陈是“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作为重要依据之一;还把早先陈曾为彭柏山、王元化等的批判处理说过一些同情的话上纲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宣传部有关党支部的许多党员对于已经决定的事又180度反复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好奉命行事。在第二次支部大会上,张春桥亲自出席讲话,宣布陈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的决定。陈其五同志对此非常痛苦,曾放声痛哭。1965年初,陈其五再次写信给市委并转柯庆施,要求留在党内。但此时已经转到广东疗养的柯庆施已难以改变已被更改的处分决定。3月,华东局监察小组组长郑平同志转告陈其五:你写的信,柯老已看过。柯老指示,事已如此,再改变决定,影响不好。好好改造,过两年再回来。陈其五还拟再写信给柯,而柯不幸于4月9日逝世。6月,市委将陈的处分决定以正式文件下发,陈被撤职、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扬州苏北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文革中,陈被进一步批斗打击,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曾发了一篇两整版的长文,加给他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被粉碎后,陈其五同志写信给中央申诉,经转市委复查,于1979年否定、撤销了1965年给他的犯错误结论和处分,推倒了“四人帮”余党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和原行政级别,1981年恢复原来的工作职务(市委宣传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1984年9月病逝。
二、对陈其五的印象
我曾三度在陈其五领导下工作。一是南京解放初在南京市委宣传部,二是1960年前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几年,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平反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
陈其五同志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一二·九”运动时,他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以后继续积极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了北平“社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平津流亡同学会主席等职。1938年初入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从团、师到华中军区的政治宣传领导工作,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两淮、涟水、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为部队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包括不少城市的入城布告),并在淮海战役中,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先后在南京(当年是中央直属市)、华东、上海的宣传、教育、理论、文艺战线上担任领导职务,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界知识分子有广泛的联系,尽心尽力工作,有许多重要的建树。
他在南京市委宣传部任部长那段时间较短,到1950年春,就因肺病大吐血,离开宣传部休养去了。那时我从市军管会结束后分配到宣传部秘书室工作。秘书室一个主任,一个收发,一个我,主任经常在外面对付全市大的宣传活动,秘书室承上启下的许多具体事,包括来往文件运转、电报管理、会议组织以及宣传经费的开支等等,就由我勉力应付了。事情多,又往往急,对我来说很多是生疏的,过去没有做过。尽管尽自己的全力,仍不免出些差错。有一次,1950年1月10日,陈其五部长要在第二天上午召开一个几十位南京宣传文教单位负责干部的会,我联系好了会场后,一一电话通知了。第二天开会,陈部长发现,市府高教处处长徐平羽未到,立即查问再通知他到会,并当众严厉批评了我。我当然接受,作了检讨。后来,他又对我说,做秘书工作要耐心、细心,有些事不会做,做做就会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由此,我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印象是:朝气盛、锐气足(当时他三十几岁),工作雷厉风行,批评不讲情面,但批评后又能较周到地关心被批评者的心情。
第二段,是他1960年前后几年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我在部的办公室工作。那一段时间,正是从“大跃进”到国家遭到经济困难的时期。在他担负的纷繁复杂的工作中,回想起来,印象较深的,一是他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严重挫折忧国忧民。他对于当时的形势看法不一定每句都准确,内容简如上述,但主导的思想是认为应该承认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是实事求是,才能改进工作。后来他遭到了批判。二是对于某些“左”的倾向有抵制。如1962年一次在市委商量对广州会议如何传达,陈其五同志提出了传达的具体意见,张春桥(1957年5月前任市委文艺部部长,文艺部并入宣传部后,未在宣传部任职,1959年1月起是市委“专职常委”)立即反对,问:为什么要传达!陈其五说,周总理讲话后,陈毅副总理接着讲的也代表总理了。张春桥又反对:他不代表中央!虽然张春桥阻挠,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并不站在张一边。陈其五回宣传部后,仍坚持在瑞金剧场召开大会,向宣传系统的有关同志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的讲话。三是对于某些受到不当处理的干部,如受胡风案牵连的彭柏山、王元化等,他给予了同情和可能的支持,彭柏山从青海调到厦门大学工作,印象中他也帮助说过一些话。从这些待人处事中,可以看出,他在事情面前,敢于直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年的锐气依然存在,这是值得称道的;他因此而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则令人惋惜。
第三段,是他受错误处分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以后,也即1981年后的几年,我也回到部办公室工作。他先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部的日常工作,1983年下半年从部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仍担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夏征农),直到逝世。这几年,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久的几年,党内、社会上各种思想多而杂,出现问题也多,但我们感到,在各种问题面前,他敢管、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承担责任。既对“左”的思想进行清理,又对自由化等错误倾向进行批评纠正,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于1982年本市上演的一台话剧《爱,在我们心里》的处理就是一例。对这个剧,他亲自去看(包括演出和剧本),去听各种反映,派人对有关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在领导上统一认识,然后以慎重的态度,说理的方法,对有关各方面做工作,一步一步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此剧是背离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整个事情的处理十分稳当,曾得到中央宣传部的肯定。他遇事和其他单位联系时,注意尊重和听取对方意见,然后协商解决问题。他关心干部、联系群众,遇到思想问题则进行疏导。遇到别人提出要求,他不以个人表态,而先由部的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后,以组织名义答复。这样处理周到妥贴,也不会反复。在这几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尤其是早年肺结核病的迁延和一叶肺因肺癌被切除,他的肺功能非常差,可是他抱病兢兢业业地工作,有时一天三班忘记休息,到晚上回家登上没有电梯的四层楼,简直是一步一喘,可第二天又照样工作。据胸科医院著名教授吴善芳说,他的肺功能之差,到了血液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而他还能正常工作,是世上罕见的,如果不是顽强的精神支持,真是不可想象。回顾他最后这一段工作,我感到,他不仅全身心地为党、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工作,在平时表现上似乎少了一些往年有的感情色彩,而内心里,却革命激情未减,是非分明,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到这里,我想起六十年前他在南京对我说的那句话:“有些事做做就会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而他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是非曲折的晚年,在做事、做人中更显现出他的领导水平、领导艺术更加成熟,自我要求,自我涵养更趋完善。这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永远怀念的。
老友周天写前述文章时要我提供陈其五同志的照片,我照办了;他的文章发表,又“逼”我写一些陈其五同志的事,现遵嘱写实如上,不足之处盼了解更多更深情况的同志指正。
(本文照片由陈其五夫人冯健同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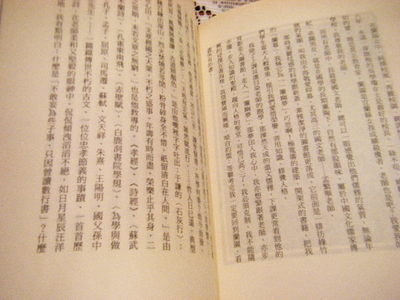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离休干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