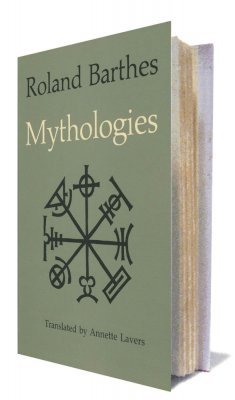导论
符号学还有待于建立,因此我认为还不可能提出任何一部有关符号学分析方法的手册来。此外,由于其普遍性(因为它将是有关一切极好系统的科学),符号学的教学工作也将难以安排,除非这些符号学系统是在经验的基础上构成的。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一步步的进行下去,必须先研究某种知识。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种尝试性的知识考察来摆脱这一恶性循环,这种知识即使谦逊的,又是大胆的。谦逊是指,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大胆则是指,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
我在此提出的这本《符号学原理》,其目的只是要从语言学中引借一些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我事先认为,对于进行符号学研究来说禀具充分的一般性。在汇集这些概念时,我并不断言它们在研究过程中会始终保持完整;我也不断言符号学应当始终严格遵照语言学模式、我们满足于提出和阐述一套术语系统,希望这套术语系统,能够在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象中,导引出一个初步的(即使只是临时性的)秩序来:简言之,本书是与问题分类原则有关的。
因此,我们将把这些符号学的基本方面,按照结构语言学划分为四大类:一是语言和言语;二是所指和能指;三是系统和组合;四是直指和涵指。我们会看到,这些分类是以二分法形式呈现的;我们将指出,概念的二分法似乎常常存在于结构的思想中,好像语言学家的元语言“在深层”复制着它所描述的系统的二元结构似的。此外,我们将顺便指出,研究当代人文科学话语中二元分类的突出作用,无疑是极富教益的。有关这些科学家的分类学(taxionomie),在对其充分了解之后,肯定将提供有关我们时代中的所谓理智想象界(I’imaginaire intellectual)的信息。
Ⅰ 语言结构与言语
Ⅰ.1 语言学
Ⅰ.1.1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parole)这对(二分法中的)概念,在索绪尔语言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且与以前的语言学相比,它们肯定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主要关心在发音流变,词义自发关联以及类比作用中的历史性变化,因此是一种有关个别性言语行为的语言学。为了深入研究这对著名的语言二分概念,索绪尔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多性”为出发点。初看起来,语言表现为一种不可分类的现象,我们不可能从中引申出统一性来,因为这一现象同时具有物理性、生理性、心理性、个人性和社会性。然而,当人们从这种杂多现象中抽引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对象时,语言的混乱型就终止了,所谓纯社会性对象,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规约系统全体,它与组成其本身的记号的质料无关,这就是语言结构;与其相对的言语则含括语言的纯个别性方面(发音行为,规则的实现,以及诸记号的偶然性组合)。
Ⅰ.1.2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结构就等于是语言(language)减去言语。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又是一种值项(valeurs)系统。正如社会性的制度系统一样,它绝不是一种行为,它摆脱了一切事先的计虑(premeditation)。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绝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此外,这个社会的产物是自主性的,正如一种本身具有规则的游戏一样,因为人们如果不经学习是无法掌握它的。作为值项系统的语言结构是由一定数目的成分组成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他成分来说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其中程度不等地出现着其他的相关值项。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看,记号相当于一枚钱币,这枚钱币等价于它能购买的一定效用,但它的价值也可以相对于其他含值较高或较低的钱币来衡量。语言结构的制度性与系统性显然是相互联系的,因为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部分上是任意性的,或更准确些说,非理据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任何个别人所做的改变,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
Ⅰ.1.3与作为制度和系统的语言结构相对,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由于组合作用,说话的主体可以运用语言结构的代码来表示个人思想”〔可以把扩展的言语链称为话语(discours)〕。其次,它是由“心理—物理机制形成的,这类机制使言语能将这些组合作用表现于外”。例如,我们当然不能把发音行为与语言结构相混,不论依赖语言制度与系统的个人是在高声还是低声说话,吐字缓慢还是快速等,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制度和系统。言语的组合作用显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言语是由一些相同记号的反复结合形成的;因为这些记号既在几种话语中重复出现,又在同一种话语中重复出现(尽管记号可按无限多种言语表达来组合),所以每一记号都成为语言结构的一个部分。同样,由于言语基本上是组合性的,它于是相当于个别的行为,而不相当于一种纯创造性的行为。
Ⅰ.1.4语言结构和言语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显然都只能在一种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辩证过程中来规定其完整的意义: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就没有言语,正如梅罗-庞蒂指出的,真正的语言实践只存在于这一交互关系中。V·布龙达尔也说过,“语言结构是一个纯抽象的实体,一种超越个人的规范,一种基本类型的集合,它们被言语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体现着。”因此,语言结构和言语处于一种相互蕴含的关系中。一方面,语言结构是“由属于同一社会内各主体的于、按与实践所呈现的蕴含”,而且因为它是由诸个别标记组成的集合体,在每一孤立个人的层次上它只能是不完全的;语言结构只能在“言语流全体”中才能有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在语言系统中将言语抽出时才能运用言语。然而另一方面,语言系统也智能从言语中产生。从历史上说,言语现象总是先于语言结构现象的(是言语使语言结构发生演变的);从发生学上讲,语言系统是经由环绕着它的言语之学习而在个人身上形成的(人们并不教导婴儿学习语法和词汇这类大致相当于语言结构的东西)。总之,语言结构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这一事实具有真正的辩证法的性质。我们将注意到(当从语言学过渡到符号学观点时十分重要的是),不可能存在(至少对索绪尔来说)一门关于言语的语言学,因为言语全体在被理解程通讯过程时已经属于语言结构了;因此存在的只有一门关于语言结构的科学。于是我们可立即排除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否应当在语言结构之先去研究言语这样的提法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必存在其他选择;人们只能在言语具有语言学(“发音学”)性质的方面对其加以研究。其次,预先考虑如何把语言结构和言语加以分开也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一种预先已有的方法,正好相反,语言学(稍后还有符号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与使语言结构和言语区分开来,同时这也正是意义确立之过程。
Ⅰ.1.5叶尔姆斯列夫并未干扰索绪尔有关语言结构与言语的概念,但他以更加形式化的方法重新规定了这两个概念。在语言结构本身(它始终语言与行为对立)叶尔姆斯列夫区分了三个层次:第一,图示(schema)层,它是作为纯形式的语言结构(叶尔姆斯列夫不大想把这个层次称作“系统”、“型式”或“架构”),其实它就是在该词严格意义上的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例如,法语因素r在语音学上是按其在一系列对立组中的位置来确定的。第二,规范(norme)层,它是质料形式(formematerielle)的语言结构,它已为某种社会实现作用所规定,但仍独立于其显现的细节之外。如法语口语中的r(但不是法文书写形式的r),不论其发音如何。第三,用法(usage)层,它是作为某一种社会习惯之集合的语言结构,例如某些地区中的法语因素r。在言语、用法、规范和图示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制约关系:规范制约着用法与言语;用法制约着言语,但也为后者所制约;图示同时为言语、用法和规范所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显现的是两个基本层次:第一,图示层,有关它的理论与有关形式和制度的理论相结合;第二,规范—用法—言语层,有关这一层次的理论与有关内质(substance)和实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正如叶尔姆斯列夫所说,规范是研究方法的一种纯粹抽象,而言语是一种纯抽象具体化的过程(“一种暂时性的记录”),为完善起见可提出一种新的概念二分法:图示与用法,这对概念可用来代替语言结构与言语。然而叶尔姆斯列夫的改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从根本上使语言结构概念(他以图示这个词表之)形式化了,并排除了具体性的言语概念,而代之以一个更具体化的用法概念。把语言结构概念形式化和使言语概念社会化的这种改变,完全--消除了言语的“肯定性”和“实体性”方面,也完全消除了语言结构的区分性方面,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改变的优点是取消了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与言语区分法中含有的诸多矛盾之一。
Ⅰ.1.6这种区分法不管内容多么丰富和具有多大的优点,实际上仍产生了不少问题。在我们这里谈三点。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使语言结构等同于代码,实验与等同于信息?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这种类比是不能成立的。P.积劳德也拒绝这种类比,他认为,代码的惯习规则是明显的,而语言结构的惯习规则则是隐在的。然而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这种类比肯定是可以接受的,A.马丁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可以在言语和组合段(syntagme)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来。我们看到,言语尽管在发音表现方面多种多样,但可被定义为(重复性)诸记号的一种(变动)组合;然而在语言结构本身的层次上却已经存在着某些固定的组合段(索绪尔曾引证组合词syntagme为例)。然而区别语言结构和言语的界限可能很不牢靠,因为在这里界限是由“某种组合程度”确定的。因此就引出了固定的、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发生学的)组合段分析,因为所有的组合段都要受聚合体变异作用(variationparadigmatique)的影响〔叶尔姆斯列夫把这种分析叫做形态句法(morpho-syntaxe)〕。索绪尔也注意到了这种过渡现象:“或许也有一整套属于语言结构的短语,个别人本身不再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如果这类语言定型式(stereotypes)属于语言结构,而不再属于言语,以及如果人们承认众多的符号学系统将因此而有很大用处,那么应当预见到,对于所有强定型化的“写作”来说都需要一门真正的组合段语言学。最后,第三个问题与语言结构和适切性(pertinence)的(因而也是和语言统一体中真正具意指性元素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人们有时(如特鲁别茨柯伊本人)认为适切性与语言结构等同,因此把一切非适切性的特征,即诸组合性变体,排除于语言结构之外。于是,将二者等同的看法就遇到了苦难,因为存在有被硬性规定的、即“任意性的”组合性变体(初看起来它们属于言语现象):例如,在法语中,语言结构硬性规定字母l在一个清辅音(如oncle-词中)之后是一个清辅音,而在一个浊辅音(如ongle-词中)之后是一个浊辅音,除非这些现象不再是属于纯粹语音学(而非不再属于音位学)了。这样,理论的结果是:我们是否应当承认,真实情况与索绪尔的断言(“在语言结构内只存在区分”)相反,那些未被区分的现象仍然可能属于语言系统(属于制度)?马丁内就是这样认为的。弗莱(Frei)企图通过下述方式排除索绪尔的矛盾,即使区分限于亚音位(sub-phonemes)之内,例如说,p本身不是区分性的,它只具有辅音、塞音、清音、唇音等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不拟深论。从符号学观点来看,必须承认那些“发生的”,即属于语言结构的组合段和非意指性变体的存在。索绪尔几乎未曾遇见到的这样一门语言学,可能在一切固定组合段(或定性式表达)为主的领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大众语言就是这样的领域;此外当非意指的变体构成了一个第二能指系统是,具有强涵指的语言也属于这一领域。如舌尖颤音r在直指水平上是一种简单的组合性变体,而在例如戏剧语言中它就增添了一种乡音声调,因此参与了一种代码,如无此代码,“乡间性”信息就既不可能被发出,也不可能被察觉。
Ⅰ.1.7我们将在本节中提出自索绪尔以来尽人皆知的两个从属的概念,以结束有关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概念的讨论。第一个是个性语言(idiolecte)。个性语言即“被单独一人所说的那种语言”(马丁内语),或者说是“某一时刻中某一个人之习惯的全部规则”(艾柏林语)。雅克布逊曾怀疑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语言永远是被社会化的,甚至在个人的水平上,因为当人们对某人说话时总企图或多或少地用对方的语言,特别是用对方的词汇来谈话(“在语言领域内不存在私有性质”):因此个性语言一般来说是一个虚假的概念。然而我们应当注意,个性语言能有助于表达以下现象:(1)失语症患者的语言,他不能理解别人的话,不能接受与本人语言模式相符的信息,这样的语言就是一种纯个性语言(雅克布逊)。(2)作家的“风格”,虽然风格也总是具有某种来自传统的,即来自集体的语言模式。(3)最后我们也可以干脆扩大这个概念,把它定义作为某一语言社会的语言,也就是由那些以相同方式解释一切语言陈述的诸个人所组成的团体额、的语言;这样,个性语言就几乎相当于我在其他场合用写作(ecriture)一词所描述的那种语言。一般而论,个性语言概念所表明的那种探索,只不过表示了在言语和语言结构之间还需要一个中间性实体(正如叶尔姆斯列夫的用法理论所表示的),或者换言之,需要一种被制度化了的、但还未像语言结构那样可加以彻底形式化的言语。
Ⅰ.1.8如果我们同意有关“语言结构—言语”与“代码—信息”这两组概念彼此相同的看法,现在就得提一下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即雅克布逊用双重结构(structuresdoubles)来表述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对此不予重点介绍,因为雅克布逊已在《普通语言学论集》(第9章)中其重新加以阐述了。我们只指出,雅克布逊的双重结构论所研究的是代码与信息一般关系中的某些特殊情况,即两种有关循环性的情况和两种有关重叠性(overlapping)的情况。(1)插入话语,或某一信息内之信息(M/M),这是间接文件的一般情况。(2)专有名称,这种名称表示一切指定由其表示的人在这里代码的循环性是明显的(C/C):“让(Jean)表示一位叫“让”的人。(3)自名(autonymie)的情况(如“Rat是一个人单音节词”):在这句话中rat(雄鼠)这个词被称作它自己的专有名称,信息就与代码“重叠”了(M/C)。这个结构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很说明性的解释”,也就是相当于委婉表达法、同义词以及两种语言间的转译。(4)转换语(shifter)〔或连接语(embrayeur)〕毫无疑问构成了最值得注意的双重结构。最常见的转换语的例子是人称代词(我,你),人称代词是一种“指示性符号”,它本身把约定性的关系和存在性关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只能借助一种约定性规则才能表示其对象(于是我在拉丁语中是ego,在德语中是ich,等等),但另一方面,人称代词在表示说话者时只能在存在性上相关于说话行为(C/M)。雅克布逊提醒读者,长久以来人称代词都被看成是语言的最原始的层次(洪堡),但他认为情况正相反,在这里问题与一种复杂的和成年后才会有的代词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有关:人称代词是儿童学习语言时最后学会的,也是失语症患者最现失去的;这是一些很难掌握的转换词。转换词理论至今似乎还很少被研究,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说,预先多注意与信息相冲突的代码是很有益处的(反过来说则平淡无奇了)。我们已看到,用皮尔士的术语来说,转换词是指示性符号,或许(这只是一种工作假设)正是由于转换词我们才有必要研究那类出现于语言范围的,尤其是某些文学话语形式内的信息之符号学定义。
Ⅰ.2 符号学观点
Ⅰ.2.1语言结构与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是明显的。人们很早就指出过,在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概念与杜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概念之间存在又显然的类似性,后者是独立于它的个别表现的。甚至有人假定杜尔凯姆对索绪尔有过直接的影响,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观来自杜尔凯姆,而他的言语观是对塔得的个体观的一种让步。这种猜测已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语言学已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管发展了“值项系统”的观点,它导致人们承认有关语言制度的内在分析法的必要性;而内在性概念是与社会学研究相抵触的。似乎矛盾的是,我们看到的语言学结构和言语观的较成功的发展,不是来自社会学方面,而是来自哲学领域。梅罗-庞帝也许是对索绪尔理论发生兴趣的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或许由于他重新坚持了在说着的言语(在产生状态中的有意义的意向)和已说的言语(由语言结构所获得的结果,它使我们想起了索绪尔的“蕴藏”概念),或许由于他把这个概念扩大并提出了所有的过程都以系统为前提的假定:这样,从此就发展出了一种在事件与结构质检的经典对立说,后者在历史学中取得了公认的成效。大家知道,索绪尔的这个概念在人类学领域中也有重大的发展;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著作中都曾非常明确地援引索绪尔的理论,以强调这一观念的重要性。我们只督促读者注意,过程与系统的对立(即言语与语言结构的对立)是具体地表现在亲族结构内女人交流过程中的。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这种对立具有一种认识论的价值,语言结构现象的研究属于机械的(按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即在与“统计性”对立的意义上)和结构的解释范围;而言语现象的研究属于概率计算领域(宏观语言学)。最后,那些将言语吸收在内的语言结构,具有无意识特性,对此索绪尔已明确提出,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最具独创性和最富深意的见解之一,即无意识并非指内容(对荣格原型轮的批判)而是指形式,即所谓象征功能。这一想法与拉康的思想类似,在拉康看来欲望本身是作为一种意指系统而被表达的,此一看法导致,或将导致人们以一种新方式去描绘集体想像届(I’imaginairecollectif),即不是像迄今为止人们所做的那样根据其“主题”,而是根据其形式和功能来对其加以描绘;或者可以更一般地,也可更明确的说,主要按其能指而非按其所指来对其加以描绘。按照这一简要的说明我们看到,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语言学之外或语言学之上,导致了丰富的发展。我们将假定,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一般性范畴,广泛的存在于一切意指系统中。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们在此仍保留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词,即使当我们把它们应用于非语言性的通信系统中时也如此。
Ⅰ.2.2我们看到,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区分是语言学分析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如想立即对有关对有关形象和行为的对象系统作这类区分,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系统还未曾从语义学角度加以研究过。对于所提到的这些系统,我们只能预见到其中某些现象类属于语言结构范畴,另一些现象类属于言语范畴,然而须立即补充说,在这类符号学过程中,索绪尔的二分法须十分细心地做些改变。现举服装现象为例,按服装在社会交流中表现的内容,显然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的系统。在书写的服装中,即在时装杂志用发音语言所描述的服装中,可以说并不含有“言语”:“被描述的”服装绝不相当于时装规则的一次个别的实现,而是相当于记号和规则的一个系统,即在其纯粹状态中的一种语言结构。如果按照索绪尔图示,无语言结构是不可能成立的;在服装现象中这一事实之所以能成立,一方面由于时装语言结构不是从“说着的大量言语流”中导出的,而是由一组自然的产生出代码的决定作用所产生的;另一方面,由于在这里一切语言结构所固有的抽象作用都是以书写语言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样,(被书写的)时装在服装信息交流水平上是语言结构,而在语言通讯水平上是言语。在被摄影的服装现象中(为简化起见假定其中不附有文字说明),语言结构永远是由时装界人士产生的,然而它不再以抽象形式表现,因为被摄影的服装永远附着在某一个别的妇女身上。由时装摄影所表现出来的服装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因为一来在这里时装语言结构,是由一种“准实在的”服装中引出的,而同时服装的穿戴者(摄影模特儿)却可以说是一位标准化的个人,她是根据其拥有的典型的普遍性而被选中的,因此可表示一种固定的“言语”,这种言语不具有任何组合的自由性。最后,在被穿戴的(或实在的)服装现象中,正如特鲁别茨柯伊所指出的,我们看到了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典型区分。服装的语言结构是以如下方式被构成的:(1)按照衣服诸部分之间的,即诸腰身或“细节”之间的对立关系,它们的变化将引起一种意义的改变(戴贝雷帽和圆顶礼帽意义不同)。(2)按照主导衣服个细节部位的组合规则,或长或短,或厚或薄。服装的言语包含着各种不规则的制作因素(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已很少存在了的那类要素),或个别的穿着因素(衣服大小,雅致与耐磨的程度,个人癖好,衣服个别部位之间自由的组配,等等)。在这里把“服装”(costume,它相当于语言结构)和“衣服”(habillement,它相当于言语)联系起来的辩证关系,与天然语言中的情形不同。当然,衣服永远是来自服装的(除了在一些标新立异的场合,此时它有自己特殊的标记),然而服装,至少在今日,是存在于衣服之前的,因为它产生于由少数人组成的“服装业”团体(虽然比起高级时装业来说它较少具有个人特色)。
Ⅰ.2.3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意指系统——饮食现象,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不难发现索绪尔式的概念区分。组成饮食语言结构的是:(1)排除规则(饮食禁忌)。(2)有待确定的诸单元间的意指性对立(例如“咸—甜”对立)。(3)同时性(在一份菜的水平上)或相续性(在一套菜的水平上)的联合规则。(4)用餐礼仪,它或许作为一种饮食“修辞学”起作用。至于极其丰富的饮食“言语”。它包括有关饮食制备和组配的种种个人的(或家庭的)变体(我们可以将按一定数量习惯形成的某一家庭的烹调看做一种个性语言)。一套菜则可清楚地说明语言结构和语言的作用;整套菜是参照一种(民族的、地区的或社会的)结构构成的,然而这个结构是随着时代和用餐者的不同而体现的,这正像一种语言的“形式”,按照某一说话者随特殊信息的需要不同而去自由改变和组合时所加以体现的情况一样。在这里,语言结构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于我们的某种沉积作用(sedimentation)的用餐法,构成了饮食的语言结构。个别的创新现象(人们发明的各种食谱)永远表明具有一种制度化意义;与服装系统不同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某一决定集团的作用:饮食的语言结构只是由某种集体性用餐法或某种纯个别性“言语”构成的。
Ⅰ.2.4我们还可随意地提出有关另外两类食物系统的一些说明,来结束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之间区别性的考察,这就是汽车系统和家具系统。这两类系统尽管不同,但在依存于某一决定(制造)集团的特点上却有共同性。在汽车系统上,“语言结构”是由一套形式和“特点”构成的,它们的结构是随着比较他们之间原型的不同而形成的(与其“复制品”数量无关)。在这里“言语”现象颇受限制,因为在相同的档次上选择不同式样的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只能在两三种式样中和在一种式样内的几种颜色和配件中进行挑选。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或许应当把作为对象(objet)的汽车概念转换为事实(fait)的汽车概念。在汽车驾驶行为中我们看到作为对象的汽车有种种不同的使用法,它们一般来说构成了言语面,实际上使用者在此不可能通过直接影响汽车的式样来改变其各部分的组合方式。使用者的“实行”自由取决于在时间中形成的用法,在这种用法的内部,语言结构的“形式”在被实现时必须通过某些实践所谓中介(lerelais de certainespratiques)。最后,我们想简略提出的另一个系统是家具(mobilier)现象,它本身也是一个语义学对象。家具的“语言结构”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是功能相同的各种家具(如两种床、两种壁橱等等),其中每件家具(ameublement)水平上的不同单元间的组配规则。对于家具现象来说,“言语”的构成或者是由于使用者可能给一个单元带来的无意义的改变(例如手艺人在拼凑一个家具部件时),或者是由于在每件件家具之间组配的自由性。
Ⅰ.2.5最有趣的通询系统,至少是那些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都是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有种种不同的内容。在电影、电视和广告领域中意义取决于形象、声音和字形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目前为这类系统确定语言结构现象和言语现象的分类为时尚早,一方面因为人们尚难确定每一复杂系统的“语言结构”是基本性的,还是仅仅由有关的附属“语言结构”组成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附属语言结构还未被分析过(我们了解天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但并不了解形象或音乐的“语言结构”)。至于报纸,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它看做一种自足的意指系统,即甚至于仅限于考虑其书写成分,但几乎仍然不了解一种似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语言现象——涵指作用,即一种第二意义系统的发展,后者寄存于所谓严格意义的语言结构。这个第二系统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结构”,某些有关的言语、个性语言和双层结构等都围绕这个语言结构发展起来。对于这些复杂的或涵指的(这两类性质并不相互排斥)系统,不再可能,哪怕以概括的和假设的方式,预先决定其语言结构现象的分类和言语现象的分类。

Ⅰ.2.6把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符号学领域加以扩大运用并非没有引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以显然严重影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语言学模式不再适用而应加以改变了。第一个问题与系统的原始有关,这就是语言结构和言语的辩证关系。在天然语言中语言结构的任何因素都被言语所使用,但是反过来,任何言语如果不是从语言结构的“蕴藏”中抽取的,就不可能实现(即不符合其通询功能)。像饮食现象这类系统也包含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上述相互关系,至少在部分上如此,尽管个别的创新实践可能变成语言结构现象。但对于大多数其他符号学系统来说,语言结构不是由“”说着的大量言语流,而是由某一进行决定的集体所造成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符号学语言结构中记号确实是“任意性的”,因为它是通过某一单方面的决定以一种认为的方式造成的。总之,它涉及被制造的语言、即“技术语言”(logo-techniques),使用者运用着这种语言,从中抽取着(“言语”的)信息,但并不参与其制作。作为系统(及其变化)始原的决定集团,可能是数目相对有限的一群,他们可能是知识程度甚高的技术专家团体(如时装、汽车等例子中的情况);不过他们也可能是较分散、较不知名的群体(如时髦家具艺术、大众服装业中的情况)。然而,如果说这种认为性并未改变这类交流方式的制度性特点并在该系统和运用之间维系着某种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意指作用的“契约”为了被接受接得由广大使用者来遵行(否则得话,使用者将具有某种非社会性的标记,他只能传达自己的反常性);另一方面,因为“通过决定”制作的语言结构并非完全是自由的(“任意性”的),它们服从着集体的制约作用,至少是在下述意义上是如此:(1)当由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需求的情况下(在现在非洲国家中人们的服装式样变成了半欧式化式样,在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中所产生的食用快餐中的新礼仪,等等)。(2)由于经济的迫切需要促进某些材料(如人造织品等)消失或增加的情况下。(3)当意识形态限制了形式的创新,使其受到禁忌的约束并在某个方面缩小了“正常”的范围时,我们可以更广泛地说,决定集团的产物,即诸“技术语言”,其本身只不过是永远更具一般性的某种功能之诸同项,后者相当于该时代的集体想象界:因此个别的创新就被一种(个数有限的集团的)社会学的制约作用所超越,而另一方面此社会学的制约作用又相关于人类学性质的一种最终意义。
Ⅰ.2.7把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扩展到符号学领域所引起的第二个现象,与人们在“语言系统”和其“言语”之间可能建立的“量值”(volume)关系有关。在天然语言中,作为有限规则集合的语言结构和作为受这些规则支配、在数量上实际无限的“言语”之间,在量值上极其不成比例。我们可以假想,像饮食这类系统也表现出了量值上的巨大差异,因为在烹饪“形式”内部,进食的方式和组合方法,始终是为数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汽车或家具这类系统中,自由组合和组配的变体数量却是有限的,在模式和其“实行”之间极少存在有(至少可被该系统的制度所认出的)边界。在这类系统中“言语”甚少。例如在被书写的时装这类特殊的系统,几乎不存在其言语了,因此似乎矛盾的是,我们看到一种无言语的语言系统(我们已看到,在此言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该语言系统由天然语言的言语所“承托”)。尽管的确存在着无言语的或只有极微弱言语的语言系统,仍然有必要修正索绪尔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语言结构只是一种区分系统(在此情况下区分系统是完全“否定性的”,语言结构在言语之外是不可理喻的。同时也有必要用第三种成分来补足有关语言结构和言语之关系的认识,即前意指性的(pre-signifiant)质料或内容,后者将成为意指作用的(必要的)支基(support)。在一个“一件长的或短的袍子”这个短语中,“袍子”这个词仅是一个(长或短)变体的支基,后者本身完全属于服装的语言结构。这种区别在天然语言中是找不到的,在天然语言中声音被看作是直接的能指,不可能将其分解为一个惰性的成分和一个语义成分。在(非语言的)符号学系统中,我们却能区分出三个层次(不是两个层次),即质料、语言结构层和运用层。这一情况将使我们显然可以考虑那类无“实行”的系统,因为这第一种质料成分保证了语言结构的物质性。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明,质料成分的引进就更有道理了。如果说在这些系统中“语言结构”需要“质料”(而不再是“言语”),这是由于和人类语言相反,这些系统一般来说都有一种功用性的、而非意指性的根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