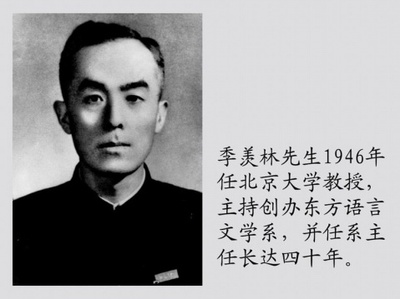我: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爸: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我: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爸: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我:您把你自己看成一个学者,但是因为一些契机,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纳了?
爸:对。但是也有一些没有被采纳。
我: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透彻,看法多么正确,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依赖侥幸。用到他们的时候还赐他们做些事情,不用他们的时候,--挨整、挨阉、挨杀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我:咱们回去继续讲学术。那天我让您评价你的两个女儿,你说“基本满意。”那现在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爸: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我: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爸: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我: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我: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其实我觉得,死了,就好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个地方的事一无所知,自己一个人就上路了。跟我当年来美国也差不多。
爸: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我: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爸:就是眼前这点事。
我: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
爸: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爸:说不上来。
我:“吴市场”算不算?
爸: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爸: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爸: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爸:认真。
我: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我:什么,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被我妈妈给洗脑了吧?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爸: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我:没有张卓元张叔叔睡得多吧?

爸:张叔叔是晚上不工作。可他起得早,动作也快。我跟周叔莲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现在咱们手里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你可以任意改变,难道你真的要改掉您兴趣广泛这一点?
爸: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邬家培,就觉得自己不如他搞经济学精力集中。
我: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爸: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够达观。达观之下,乐观、悲观都随其自然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