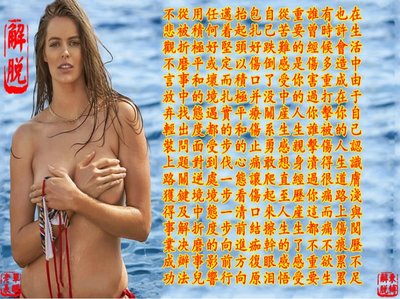大约六岁的时候,生产队分配给我家一头牛,父亲就让我去放牛。
记得这头牛是黑色的,性子慢,身体较瘦,却很高,大家把它叫“老黑”。父亲把牛牵出来,把————牛缰绳递到我手中,又给我一节青竹条,指了指远处的山,说,就到那里去放牛吧。
我望了望牛,又望了望远处的山,那可是我从未去过的山呀。我有些害怕。说,我怎么认得路呢?
父亲说,跟着老黑走吧。老黑经常到山里去吃草,它认得路。
父亲又说,太阳离西边的山还剩一竹竿高的时候,就跟着牛下山回家。
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有些害怕,把一个六岁小孩交给一头牛,交给荒蛮的野山,父亲竟那样放心。那时并不知道父亲这样做的心情。现在我想:一定是贫困艰难的生存把他的心打磨得过于粗糙,生活给他的爱太少,他也没有多余的爱给别人,他已不大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当时不懂得这简单的道理。
我跟着老黑向远处的山走去。
上山的时候,我人小爬得慢,远远地落在老黑后面,我怕我追不上它我会迷路,很着急,汗很快就湿透了衣服。我看见老黑在山路转弯的地方把头转向后面,见我离它很远,就停下来等我。
这时候我发现老黑对我这个小孩是体贴的。我有点喜欢和信任它了。
听大人说牛生气的时候,会用蹄子踢人。我可千万不能让老黑生气,不然,在高山陡坡上,他轻轻一蹄子就把我踢下悬崖,踢进大人们说的“阴间”。
可我觉得老黑待我似乎很忠厚,它的行动和神色慢悠悠的,倒好像生怕惹我生气,生怕吓着了我。
我的小脑袋就想:大概牛也知道大小的,在人里面,我是小小的;在他面前,我更是小小的。它大约觉得我就是一个还没有学会四蹄走路的小牛儿,需要大牛的照顾,它会可怜我这个小牛儿的吧。
在上陡坡的时候,我试着抓住牛尾巴借助牛的力气爬坡,牛没有拒绝我,我看得出它多用了些力气,它显然是帮助我拉着我爬坡。
很快地,我与老黑就熟了,有了感情。
牛去的地方,总是草色鲜美的地方,即使在一片荒凉中,牛也能找到隐藏在岩石和土包后面的草丛。我发现牛的鼻子最熟悉土地的气味。牛是跟着鼻子走的。

牛很会走路,很会选择路,在陡的地方,牛一步就能踩到最合适、最安全的路;在几条路交叉在一起的时候,牛选择的那条路,一定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我心里暗暗佩服牛的本领。
有一次我不小心在一个梁上摔了一跤,膝盖流血,很痛,我爬在地上,看着快要落山的夕阳,我哭出了声。这时候,牛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低下头用鼻子嗅了嗅我,然后走下土坎,后腿弯曲下来,牛背刚刚够着我,我明白了:牛要背我回家。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在心里又喊了一声:我的老黑,我童年的老伙伴。
我骑在老黑背上,看夕阳缓缓落山,看月亮慢慢出来,慢慢走向我,我觉得月亮想贴近我,又怕吓着了牛和牛背上的我,月亮就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整个天空都在牛背上起伏,星星越来越稠密,牛驮着我行走在山的波浪里,又像飘浮在高高的星空里。不时有一粒流星,从头顶滑落。前面的星星好像离我们很近,我担心会被牛角挑下几颗。
牛把我驮回家,天已经黑了多时。母亲看见牛背上的我,不住地流泪。当晚,母亲给老黑特意喂了一些麸皮,表示对它的感激。
秋天,我上了小学。两个月的放牛娃生活结束了。老黑又交给了别的人家。
半年后,老黑死了。据说是在山上摔死的。它已经瘦得不能拉犁,人们就让它拉磨,它走得很慢,人们都不喜欢它。有一个夜晚,它从牛棚里偷偷溜出来,独自上了山,第二天有人从山下看见它,已经摔死了。
当晚,生产队召集社员开会,我也随大人到了会场,才知道是在分牛肉。
会场里放了三十多堆牛肉,每一堆里都有牛肉、牛骨头、牛的一小节肠子。
三十多堆,三十多户人家一户一堆。
我知道这就是老黑的肉。老黑已被分成三十多份。
三十多份,这些碎片,这些老黑的碎片,什么时候还能聚在一起,再变成一头老黑呢?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人们都觉得好笑。他们不理解一个小孩和一头牛的感情。
前年初夏,我回到家乡,专门到我童年放牛的山上走了一趟,在一个叫“梯子崖”的陡坡上,我找到了我第一次拉着牛尾巴爬坡的那个大石阶,它已比当年踏平了许多,石阶上有两处深深凹下去,是两个牛蹄的形状,那是由无数头牛无数次地踩踏成的,肯定,在三十多年前,老黑也是踩着这两个凹处一次次领着我上坡下坡的。
我凝望着这两个深深的牛蹄窝。我嗅着微微飘出的泥土的气息和牛的气息。我在记忆里仔细捕捉老黑的气息。我似乎呼吸到了老黑吹进我生命的气息。
我忽然明白,我放过牛,其实是牛放牧了我呀。
我放了两个月的牛。那头牛却放了我几十年。
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被一头牛隐隐约约牵在手里。
有时,它驮着我,行走在夜的群山,飘游在稠密的星光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