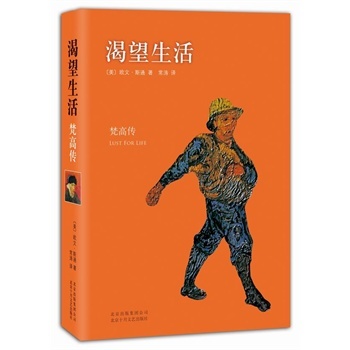梵高简介
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是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
梵高年轻时在画店里当店员,这算是他最早受的“艺术教育”。后来到巴黎,和印象派画家相交,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以此,人们称他为“后印象派”。但比印象派画家更彻底地学习了东方艺术中线条的表现力,他很欣赏日本葛饰北斋的“浮世绘”。
梵高生性善良,早年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曾自费到一个矿区(博里纳日)里去当过教士,跟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在地板上。矿坑爆炸时,他曾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然而在他主持的一次葬礼上,一位老人的厉声谴责使他突然变得清醒,他开始意识到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上帝,博里纳日的矿工们再也不需要上帝,当然也不需要他了。这样,他才又回到绘画事业上来,受到他的表兄以及当时荷兰一些画家短时间的指导,并与巴黎新起的画家(包括印象派画家)建立了友谊。
梵高全部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象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下面去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并且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梵高的确是非常超前的画家。他作品中所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的确难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他以环境来抓住对象,他重新改变现实,以达到实实在在的真实,促成了表现主义的诞生。在人们对他的误解最深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最有信心的时候。因此才留下了永远的艺术著作。他直接影响了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至于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肖像。《向日葵》就是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画家像闪烁着熊熊的火焰,满怀炽热的激情令运动感的和仿佛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单纯强烈的。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者在观看此画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动,心灵为之震颤,激情也喷薄而出,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到梵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中去。总之,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梵高油画作品》
森林中的少女(Young Girlin the Wood at the Hague)
1882年9月,此画画于海牙近郊的森林中。其229信中曾述及:“……铺满落叶的红褐色地面,因树荫而乍明乍暗、班驳离落,如幻如梦,这情景深深地震撼着我。问题是……我极欲抓住大地的暗度。大地所产生的那股巨大无形的力和坚韧的充实感……我无法使自己从那富于颜色的明亮中间与燃烧般的感觉深处逃逸出来。”“着手画树干表面时,树皮上覆盖的一层层厚厚的泥土,令我的笔迷失其中……故将颜料挤出直接盖在树根与树干上,再用笔稍抹一番,这样这棵树便稳立于地上了。”他又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不用学习颜色的描画方法,因为它不能达到稳固厚实的效果。”他对自己的作品,虽然无法感到满意,但却像他自己所说“已找到打动我心灵的……。”
梵高以速写般的方式,将自然对他的喃喃倾诉,诉诸画画。根据他写给友人拉巴都的信,可知靠在树干上的白衣少女,乃是依据英国插画家马可伊度的作品而作。
吃土豆的农人(ThePotato-eaters)
这一幅画作于1885年4月至5月间,为纽南时期的最佳杰作。同样构图的习作有两幅,素描与速写各一幅,但仍属这幅最完美。为了完成这幅作品,他曾作了许多农夫、农妇的肖像,对室内及手的素描,以及瓶子与水壶的静物画等等,这些均是对此画的习作。
此画充满了其社会性与宗教性的情感,画面虽显得粗野,但结构却十分紧密;以围聚的人物为中心,对形体加以把握;以德拉克洛瓦的色彩理论,构成了种种暗灰色调子;以这些完成了这幅佳作。
围着餐桌而坐的四个农人,都曾作过个别习作。那询问似的炯炯眼神,右端的农妇下垂的厚重眼睑,布满皱纹、上勤奋的劳动者的“力量”。他在404信上表示,希望这幅画能强调出“伸在碟子上的那只手,曾挖掘过泥土。”同时窗外的景色,也令人深切地感受到煮土豆的香味。
梵高深爱着扑拙的农人在大地上奋斗的情景,他认为这些与文明化、都市化相较之下,充分地显示出光与力。他明白这幅画或许不合现代趣味,但却是人类自强、自重的一种表现,他渴望着能将这些示诸众人,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优越感。这些都可见诸信中。
纽南教会出入的人群(Coming out of theCHurch at Nuenen)
1883年,梵高回到纽南。翌年1月,他的母亲在下火车时折断了大腿骨,他在355信内夹了这幅画的素描,并写道:“前些时候,为妈妈画这张有篱笆与耸立着树的教堂的油画。”这间八角形的正面教堂现仍保存着。画面上人口与正面的比例、与树的关系,稍有改变,可以看出他在构图上曾下了一番功夫。在这幅画中对光线的敏感,由水平及垂直的动态与明暗的强烈对比,强调了光线的象征作用。像念着经文般自门口走出来的一排黑色人群,因此增加了前景的黑色调:细长直立的树,构成了强烈的律动:配合最前面的土质,使人感到暗的震动与冬天空气的严寒。
“铃鼓”咖啡屋的女郎(The Woman at "LeTambourin")
画于1887年夏天。自这一年的春天起,他便常去克利西街的“铃鼓”咖啡屋,画中的妇女大概就是这间咖啡屋的女主人奥古斯汀娜*谢加都莉,以前曾当过得加的模特儿,传说跟梵高曾有过一段时期的深交。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到,凡高在店内的墙壁上,装饰着他喜爱的日本版画,并与贝尔纳、高更、劳特累克等利用此店举行画展。对莫奈、毕沙罗为首的正统印象派画家来说,他们自称为“反正统的画家”。这一幅画用细微的笔触所形成的律动交响与色彩并置的手法,表现出他有一段时间曾学习过修拉、西涅克的点彩法。
向日葵(Sunflowers)
1887年的暮夏,梵高画了四幅向日葵,这幅给人感觉无比的逼真,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幅可视为梵高画集的代表性作品。孩童时代他就喜爱鸟巢,这种喜爱可以说是他幻想特性的本质。由他的素描习作可以看出,他尝试着要捕捉由中心向周围旋转的分量感。他后来到南法追求太阳,就是对于旋转、炎热的天体的一种热望。事实上,向日葵就是生长在大地上的太阳(法语称之为Tournesol——旋转的太阳;英语称之为Sunflower——太阳之花)。
克利西街(Boulevard of Clichy)
铃鼓咖啡屋,即位于“克利西街”的62号,梵高和提奥同住的公寓也在这条街附近。这一幅画采用了色彩视觉混合、色彩相互渗透和笔触的轻妙律动,以表现街道上早春的气氛。在右方的树木是横线笔触,在中央的街树上则可看到轻快的简短笔触,让欣赏者感到一种看不见的空气流动。这些与前景道路散落的笔法相映衬,构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空间流动感。色彩上则使用淡紫、淡褐与蓝色为基本色调,这种柔和的色调是来自于日本的版画。在巴黎时期,他想捉住艺术上的轻快感,便以轻快为主题画了数幅同类的风景画。本图作于1887年春天。
兰格罗瓦桥(The Drawbridge at Arles"Pont de I'Anglois")
1888年2月21日,梵高到达法国南部的阿尔,住在卡列尔饭店。这一张是他达到后的3月间所画的。469信中写着:“今天的工作是画一张5号的画——那是在蓝色天空下,一辆小马车正通过的一座吊桥,和天空同色的河水、绿草,橘色的河堤,还有一群穿着各色衣服的浣衣妇女。”这一张画的色彩清澄而果断,有如金属管乐器奏出的嘹亮声响。天空是一片蓝,水波荡漾的运河,均远离巴黎的喧嚣,漫游在郊外的凡高,仿佛可以听到他自己快活的声息。
这座吊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破坏,现在已另外在别处建筑新桥。
梵高的客邸(黄屋)(TheArtist"s House at Arles(The yellowHouse))
1888年,梵高在阿尔租了一间旅馆居住,因为它的外壁涂成了黄色,故被称为“黄屋”。画面上建筑物的右侧即是梵高的住所(正面的窗户涂成绿色和黄色的部分)。梵高很早就向往“艺术家的乐园”,因此希望这个家能成为南法的“未来画室”,并且希望能够尽快地接他的穷朋友高更来一起共同生活(高更于10月20日到达阿尔)。在这一张画上,由广阔前景的土黄色地面,即向两旁延伸的马路,到小建筑物正面的硫黄色与一大片天空的蓝黑色,在到窗户、侧壁与树木的绿色,这些颜色之间相互呼应,构成了色调的转移。
夜间的咖啡座(Outdoor Cafeat a Starry NIght)
梵高自5月到9月18日借住的兰卡散尔咖啡馆,位于形式广场(Place duForm),由于通宵营业,因而被称之为“夜间的咖啡座”。他曾用两个通宵画了一幅咖啡馆室内的作品,《夜间的咖啡座》是同期的作品。他时常觉得夜间比白天更充满了生气蓬勃的色彩,所以几度跑到户外去画星星。画中,在煤气灯照耀下的橘黄色的天蓬,与伸蓝色的星空形成同形逆向的对比,好象在暗示着希望与悔恨、幻想与豪放的复杂心态。梵高已慢慢地在画面上显露出他那种繁杂而不安、彷徨而紧张的精神状况。
吸烟斗(割耳)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Bandaged Ear)
1889年梵高在卢朗陪伴下从阿尔医院返回“黄屋”这期间画了两幅自画像,都是右耳包扎着绷带,口里衔着烟斗,头戴毛皮帽,身着大衣,姿势相同的自画像。一幅以红色为主色,一幅以淡绿色为主色,背景为日本版画。由这段时期的信里,可以知道他的健康在一天天地恢复,但是他对高更的歉疚,仍然没有排除,他还想提奥表示,以后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作画,不能再陷入过度的焦急。这幅自画像可以说是透过他自己的眼睛,展望未来,而具有一种明确思想的表现。
星月之夜(The StarryNight)
挚爱深夜的梵高,在阿尔时期曾有两件作品描绘星空。在圣雷米的初期(1889年6月)所画的这幅《星月之夜》是凡高深埋在灵魂深处的世界(宇宙进化)感受。每一颗大星、小星回旋于夜空中新月也形成一个漩涡,星云与棱线宛如一条巨龙不停地蠕动着。暗绿褐色的柏树像一股巨型的火焰,由大地的深处向上旋冒:山腰上,细长的教堂尖塔不安地伸向天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回旋、转动、烦闷、动摇,在夜空中放射艳丽的色彩……。这种回旋式的运动圆形,有如远古时代的土器形体或者装饰在土器表面的螺旋花纹。在德拉克洛瓦或巴洛克的艺术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回旋的曲线和旋转的运动,但其真正的源头,恐怕还是来源于人类的潜意识之中,促成梵高产生这种原始意识的,一是得自于农民以劳动征服大地所带给他的共鸣,再者是他对德拉克洛瓦的佩服,三者是对于日本浮世绘画家北斋和广重的构图主题的把握。
在西欧传统绘画的远近法中,画家常常从观众席来观察舞台,观察风景与人物。但是对梵高来说,在他病情尚未发作之前,已感到被另外一个世界监视着。他察觉到受苦恼、受烦闷的,不只是他本身或者如向日葵那样的对象,而是能够把一切万物都包括进去的广大范畴。
花季的巴旦杏(Almond-tree Branch inBlossom)
1890年2月中旬,梵高到阿尔去时,病又发作了。在能够提笔写信时,他告诉提奥:“工作很顺利。最后一块画布是画盛开的杏花。你或许可以看出,这是耐着心画的好画。我以冷静的情绪,使用比平常较大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但第二天就不行了。这的确令人费解和无奈。”凡高的母亲在2月15日写信告诉他,提奥夫妇在上月底生了一个男孩,因此他画了这张有“青色背景的天空,数枝开着白色杏花的粗枝的作品。”以便挂在侄儿的寝室。
在这幅画上,他运用了从浮世绘与大和绘式装饰花草图中的画法,画下了枝、叶子和杏花。
庭院中的贾歇姑娘(Mademoiselle Gachet inthe Garden)
画中的白衣人物,是在奥弗照顾梵高的贾歇医生的女儿。此画作于1890年6月1日,与《茅屋》一样的,把梵高搬到奥弗之初,那段安乐时期的感情,都表现在画中。这幅作品与圣雷米时期不同的地方,是以往的弯曲漩涡式的笔触,变成一种诙谐感,繁茂的树叶也被画成柔和的火焰形式。白色蔷薇与白衣姑娘:前面葡萄园与天空的淡紫色,这些与花盆、屋顶的青橙色,构成了显明的色调。
孤鸟翔空的麦田(ABird Flying over the Wheat Fields)
画于1887年夏天。此画一见即令人联想到他在奥弗所作的最后一幅画《群鸦乱飞的麦田》,但与后者比较起来,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幅画让人感到清新明朗,好象可以听到远处清新婉转的歌声。梵高采用修拉与西涅克的色彩分割理论,又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学习到短促笔触的并置以及从光线中捕捉色彩的瞬间变幻,以色彩的视觉混合手法来表现。
这幅画的彩度高,向上向下的短促笔触,使画面洋溢勃勃的生气:云、麦田、草地均富动态,云雀的声音暗示了在画面上所看不到的垂直轴。麦穗顺着风向俯偃仔细观看会有一种写实的感觉,同时又让人觉得在遥远的彼方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憧憬。
暴风雨似的天空与麦田(Fieldsunder a Stormy Sky)
这一幅画与《群鸦乱飞的麦田》、《多比尼庭院》,是梵高在奥弗所作的最后三大作品。梵高在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650信提到这幅画时说:“我正埋头作一幅以像海那样广大的丘陵作背景,有黄色与绿色微妙色彩的广漠麦田的画。这一切存在于青色、白色、粉红色、紫色等色调的微妙天空之下。我现在非常的安宁、肃静,可以说很适合于作这幅画。”
同《群鸦乱飞的麦田》比较起来,这幅画含有深深的冥寂,好象要吞没梵高的一切。在地平线那一端所表现的,不再是德伦特时期作品中可看到的灵魂的憧憬,而是要将他的身心召回的凄美而恐怖的压迫感。
群鸦乱飞的麦田(Crows over the WheatFields)
这幅画充满着恐怖、不祥的感觉,梵高似乎已经超越了灵魂上的生死境界,置身于异世界的试炼,并试图将此世界置于笔下。649信写道:“我的生活,从根基上被破坏,我的脚只能颠跛着走。”这正说明当时他画下这幅悲惨的画的心境。“我担心,我是否变成你们沉重的负担……那时侯——回到这里再开始工作——画笔几乎从手中滑落下来……可是,从那时起我画了三张大的作品。”画上的线条很生硬,失去了次序,不但天地鸣动,所有的凄切、悲哀、绝望,都似乎从地平线的那一端飞扑过来……。
鸢尾花(Irises in a Vase)
这幅画是离开圣雷米疗养院之前所作的。梵高与贝伦博士及提奥商量后,决定离开南法,前往贾歇医生居住的奥弗(位于巴黎北方)。据633信称:“于此作最后的挥笔,所以我尽情的、忘我的工作。”
1890年5月17日,梵高留下了这幅画,只身前往巴黎。对于这张画,他曾做这样的说明:“紫色(由紫色到深红色、纯藏青色)的花束,在鲜丽的柠檬黄背景下浮现,而花束本身另有黄色的色调。放置花瓶的台面,表现出不配衬的补色效果,但这种强烈的对比,格外显明。”梵高给妹妹威丽明和弟弟提奥的信上,都曾提及此画,梵高他本人好象很欣赏这幅画。
奥弗的教堂(The Church ofAuvers)
在奥弗,梵高的画以深青色、藏青色为主。他一生中对于社会的不理解所作的抗争,对于真善美所作的追求,还有生存中的苦恼与欢乐,似乎都孕育在这天空的蔚蓝里。他写给妹妹的22信中说:“这一张画与在纽南画的古塔、坟墓等习作,似乎很相似,只是现在所用的色彩,或许表现得更为华丽。”
梵高由教堂开始,经过不同的时期,最后走到奥弗教堂,完成了他生命和绘画的旅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