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斯基自传:“脱下蓝裙子:羞耻与生存”
1997年莱温斯基进入白宫实习,与克林顿总统合影
原标题:莱温斯基脱下蓝裙子:羞耻与生存
来源:2014年5月《名利场》杂志
文|莱温斯基 译|邓楚阳
“有人说你是美国口交女王,你怎么看?”
那是2001年初,我当时正坐在纽约库伯联合学院的演播厅,为HBO录制一档问答节目。作为当天的主角,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简直吓懵了。
当时注视着我的有数百名观众,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他们听见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惊讶地张开了嘴。他们也很想知道我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参加那档节目的录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回顾“实习门”,而是为了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上去。“实习门”的调查和对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弹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政治和司法问题。但人们却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人们似乎都对更深层次的问题漠不关心,比如说我们的个人隐私在公共场所不断遭到侵犯,政治和媒体领域里的男女平等问题,还有一些法律的漏洞,例如父母和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在法庭作对彼此不利的证明。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听到观众席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还有人在小声议论着什么。还有许多面无表情的人对我喊:“不要回答!”
“我觉得这么说很伤人,也很侮辱人。”我鼓起勇气,故作镇定地说道。“既侮辱了我个人,也侮辱了我的家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一下子变得和口交有关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出现这样的结果,大概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社会里。”
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一边笑一边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也许你能够泰然自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停了一会,继续说:“但我在经历了这样的问答之后,可能又要接受一年的心理治疗了。”
你们也许会说我一开始同意参加HBO的《黑白莫妮卡》就是把自己送到公众面前再一次接受所有人的羞辱。你们甚至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对那样的羞辱习以为常了。这一次在库伯联合学院的遭遇,与之前那一份肯尼斯·斯塔尔经过一系列对克林顿进行独立调查所完成的长达445页的《史塔报告》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那份报告里,有描写关于我的性行为的文字,还有许多我与别人私下对话录音的文本记录。但是当录影结束、观众都离开之后,关于“口交女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HBO的节目里播出过——仍然在我心里挥散不去。
确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人们把重点放在我与克林顿的婚外情上。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与别人一对一地对峙,愚蠢地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无意间将自己带回公众的视野,试着向所有人讲述真相,造成的后果就是,自己成了小说中千夫所指的荡妇,胸前还刺着一个红字“A”。
要是那一次在库伯联合学院录制的节目是发生在到处都充斥着社交媒体的今天的话,我将会遭受更彻底的羞辱。那段视频一定会在Twitter,YouTube,Facebook,TMZ,上疯转。这颗毒瘤会在《每日野兽》和《赫芬顿邮报》上被不断地提到。而且,这还不够。有了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的帮助,12年后的今天,你们还可以在YouTube上反复看这段视频,看上一整天(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知道,在公众面前丢脸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是第一个人。似乎每一个人都难逃互联网的监视与责难,那些流言、半真半假的传言、谎言就是在互联网上渐渐滋生的。借历史学家尼克劳斯·米尔斯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羞辱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仅陶醉于幸灾乐祸,还对那些善于羞辱他人的人进行嘉奖。这一点从那些狗仔队、花边新闻的访问量、深夜秀的收视率、偷拍视频的点击率中就可以看到。
是的,因为互联网,我们彼此之间都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在推特上向所有人发布革命的进程,也可以记录或大或小的成就。但我们同时也被困在了诽谤和中伤的恶性循环中。事实上,在这之中,我们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也许我们的社会本没有这么残忍——尽管我们现在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电子设备给我们带来的快捷和方便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冷漠、刻薄。就在我尝尽了生活中的各种屈辱之后,我也不得不惊叹于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习惯和喜爱。
就我个人而言,每有一个网友点开那段视频,我就会感受到屈辱又在我的全身游走了一次,尽管我是那么努力地想要回避那段往事,它还是不停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美国口交女王。“那个实习生”。那个泼妇。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第42任总统来说,我就是“那个女人”。
你们或许都不会意识到,我其实也是一个和所有人一样的人类。
1998年,当我和比尔·克林顿的丑闻被曝出来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全世界最丢脸的人。特别 是《德拉吉报道》,它让我成为了第一个在互联网上被全世界一起羞辱的人。
许多年以来,我尝试在时尚配件行业施展拳脚,并且参与一些媒体项目,包括HBO的纪录片。其他时间里,我尽量低调做人。(上一次我同意接受采访还是10年前。)毕竟,就算我稍微高调一点点,也会被人们说成是想要借机炒作自己本来就坏的名声。很显然,别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评论我,都没有错,而我要是想为自己稍微辩解一下,就会饱受指摘。我拒绝了可能给我带来1000万美元收入的工作机会,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这么长时间以来,媒体并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地挖我的消息,但就在我想要翻篇向前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
与此同时,我也亲眼看着周围朋友们的生活一步步向前进。结婚、生子、进修。(再婚、再生子、再进修。)于是我决定要翻开自己人生的新章节,我要去上研究生院。
我飞到英格兰是为了去深造、挑战自我、重新认识自我,同时也是为了逃避各种目光。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和同学们都非常好——他们很友好,也懂得尊重别人。在伦敦,没有太多人认识我,大概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里看书。2006年,我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探究司法中的偏见”。有时我会自嘲,说自己用蓝裙子换来了蓝袜子,而在伦敦取得的硕士学位又给我的人生添上了精彩的一笔。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为我的人生开启另一扇大门,让我从此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后来,我辗转于伦敦、洛杉矶、纽约、俄勒冈的波特兰,四处参加工作面试,我的目标工作都是一些关于“创意交流”、“品牌”,以及一些注重慈善的企业。然而,由于雇主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及我的那段“历史”,我从未成功地通过面试。有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让我无法对他们说“不”。他们会说,“当然了,这份工作会要求你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当然了,很多媒体也会来到现场”。
2008年总统预选期间,有一份工作看起来似乎很有希望,直到后来面试官说了这样一段话:“莫妮卡,事情是这样的。你是一个非常聪明、干练的年轻女性,但对我们来说——或者对其他任何依靠政府拨款的组织来说——雇用你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如果要雇用你,我们首先得让克林顿夫妇签署一份表示与此事无关的声明。毕竟希拉里有25%的几率会成功当选总统。”我强颜欢笑,说到,“我能理解。”
另一次面试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典型:我走到洛杉矶(我的家乡)一家新兴广告公司凉爽舒适的前台。像往常一样,我用最友好、最不邪恶的语气,微笑着对接待员说:“你好,我是莫妮卡·莱温斯基,预约了与谁谁谁的面试。”
那个20多岁的前台接待员听见了我之后,把眼镜从鼻尖推到鼻梁,问道:“哪个莫妮卡?”
就在我回答之前,另一个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20多岁的男性匆匆地跑过来,打断了我们:“莱温斯基女士,很高兴见到你。我马上告诉谁谁谁你到了。拿铁?绿茶?纯净水?”
接下来,我就坐在了一个小圆桌边,对面就是这家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我们一边讲话,她却不停地眨眼睛。我想,这次又没戏了。我尽量让自己不受她的影响。但是,她不仅在眨眼睛,还开始清喉咙。她眉毛上的是汗珠吗?我突然意识到:她比我更紧张。
后来我逐渐了解了我面试和社交中各种状况的真相:对于别人来说,坐在“那个女人”对面,都是一种煎熬。不用说,我没得到那份工作。
最终,我认识到,传统的工作可能并不适合我。一段时间里,我只能靠着自己的一些创业项目和从家人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勉强过日子。
在另一个面试里,我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品牌,你觉得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告诉你,如果你是莫妮卡·莱温斯基,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问题。
2010年9月,有一件事情把我过去的所有经历推向了顶峰。母亲的一个电话让我改变了对我的世界的看法。我们在电话里谈论泰勒·克莱门特。泰勒,你们应该还记得他,就是那个被人偷拍到亲吻另一个男性的18岁罗格斯一年级新生。那段偷拍被传到了网上,他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们指责、谩骂,几天之后,他跳下乔治·华盛顿大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母亲哭了。她一边啜泣,一边不停地说道:“他的父母该怎么办啊……太可怜了。”
这是一件让人难以承受的悲剧。虽然我也流下了眼泪,但我并不是太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母亲会如此痛苦。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回想起了1998年的那件事情,那时候,她几乎一秒钟都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因为泰勒的事件,她又回到了1998年,那时候她夜夜守护在我的床边,害怕我会自杀。那样的耻辱,那样的非议,还有那样的恐惧,让她非常害怕,她害怕自己的女儿会自杀,害怕自己的女儿真的会因为羞辱而死。(这么多年来,我从未真正地尝试过自杀,但是在事件的调查期间和之后的一两年里,我确实有很强的自杀倾向。)
我永远不会将自己的苦难与泰勒所遭受的痛苦相提并论。毕竟,我所遭受的羞辱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我与一位世界知名人物有染——这是我自己所作出的错误选择。但在那一刻,当我意识到母亲的痛苦有多深的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在泰勒跳下大桥之前和他谈一谈,和他说说我的感情生活、我的性生活、我私下的事情、我最敏感的秘密是如何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知晓并且谈论的。我希望能够告诉他,对于他的遭遇,我或多或少能够感同身受。并且,尽管很困难,我们都还是能够生活下去。
泰勒的悲剧过去之后,我自己的遭遇对于我来说有了全新的意义。我想到,或许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能够帮助那些受尽屈辱、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们。问题就在于:我该如何让我的过去变得更有意义?我敢于搅乱这个宇宙吗?或者说,在我的情况里,我敢于搅乱克林顿的宇宙吗?
尽管这10几年来我尽量保持沉默,但人们总是时不时地将我拉进话题的漩涡,而且每一次都与克林顿有关。比如说,今年1月和2月,肯塔基州议员、未来可能成为共和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兰迪·保罗试图将我牵扯到总统预选的闹剧中。为了反击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不尊重女性,兰迪·保罗争论到,比尔·克林顿已经将工作地点变成了一个“暴力”的地方,因为他对一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多岁女生”很残暴。(比尔·克林顿是一位民主党人)
确实,我的老板占了我的便宜,但我始终认为:我们之间是相互的。只有之后一些为了保住他的地位而拿我当替罪羊的一系列调查才展现了这件事情“残暴”的一面。
就算我想要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也不可能。无论是好是坏,我都是人们谈论的对象。每一天,我都会被别人认出来。每一天。有时候路上的陌生人会反复从我身边经过,就好像我没有注意到似的。(幸亏百分之99.9的情况下遇见我的陌生人还是会对我说一些支持和尊重的话。)每一天,都有人在推特和博客上提到我,但并不是每一次的提及都是友善的。每一天,我的名字似乎都会出现在报纸专栏上——与丑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感情生活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麦莉·塞勒斯在她的推特上提到我,阿姆在他的rap中唱到我,碧昂斯也在她的最新单曲中为我大声疾呼。谢谢你,碧昂斯,但说起来,我想你的意思是“比尔·克林顿脱下了我的裙子”,而不是“莫妮卡·莱温斯基脱下了自己的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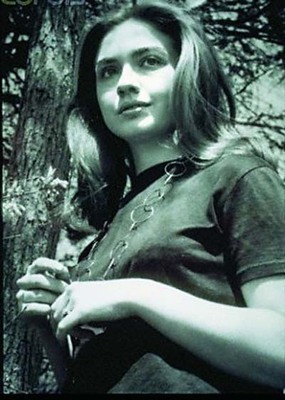
每一个和我约会过的男人(是的,我也会出去约会),都会问我关于1998年的事情。要向“公开”和别人的恋情,我必须得非常小心。在弹劾事件之后的几年里,我在扬基棒球赛的前排发现我当时的约会对象——一个我很享受与之相伴的人——实际上正处于另外一段感情中。虽然那只是一段绿卡婚姻,但我很害怕我们会被拍到,他已婚的事情会被爆出来,我又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么多年以来,我早已经能够分清楚一个男人和我约会的目的究竟是真的喜欢我还是为了别的原因。幸亏那些目的不纯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我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帮助了我重拾真实的自己。所以,无论结果多么让人心碎,无论过程中流过多少眼泪,无论事情让我多么大彻大悟,我对他们都抱有感恩之心。
今年2月份,又是那位保罗译员,再一次把我拉到了聚光灯下。这一次,我变成了“自恋的疯女人”。
尽管我想要向前看,但这一系列我熟悉的事情又回来了:有一天,一个来自我在纽约公寓门卫的电话打乱了我生活的节奏。我在电话里喘着气:“什么?又来了?”他们又出现了:狗仔队们,他们像秃鹰一样,在公寓的外墙边不断盘旋着,为的就是拍到我的照片。
我慌忙地打开电脑,准备谷歌一下自己。(亲爱的读者们,请不要对此进行评价。)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谷歌新闻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消息。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我今天有什么安排,都必须得推掉了。要是我离开公寓——被他们拍上一张照片——都会让一切传闻变得更加真实。
我再一次被闪光灯包围就是因为一篇头条新闻:一家网站之前在查找堪萨斯大学校友戴安娜·布莱尔——希拉里·克林顿最好的朋友和仰慕者——自1990年以来的记录。在其中,他们发现,这位于2000年逝世的布莱尔女士引用了前第一夫人讲述的关于我和她的丈夫的话。根据布莱尔的记录,尽管希拉里认为她丈夫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她仍然称赞他很好地“控制了一个‘自恋的疯女人’”。
读到这里,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如果那是她说过的关于我最恶毒的话,那我还真算幸运了。我看到,克林顿夫人曾向布莱尔坦白,对于她丈夫的婚外情,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她自己在感情上忽视了他),并且似乎原谅了他。尽管她认为比尔的行为非常让人作呕,这段婚外情却是双方相互的(并不是一段攀附权势的感情)。
每次关于我的新闻在各大媒体上出现时,我的朋友们都会打电话给予我精神支持。他们总是能用善意的玩笑来舒缓我紧张的神经:“那么,我们要把你的首字母变成NLT(NarcissisticLoonyToon,自恋的疯女人)吗?”我尽量不去在意第一夫人对我做出的这样的评价。鉴于我和琳达·特里普的经历,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与原配的交流被别人断章取义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即使这样,这件事情还是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意识到希拉里·克林顿——与我不同的是——她在对我进行评论的时候,完全知道这是会被记录下来的:根据备忘录上的记录,是她本人要求布莱尔把她们之间的对话保留到档案里的。
对,我明白了。希拉里·克林顿想要把她对自己丈夫情人的羞辱记录在案。也许她确实对她丈夫不恰当的行为进行了指责,但是她更想责怪女性——不仅仅是我,还有她自己——是麻烦的制造者。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像每一个失败的婚姻——大部分都与男性政客有关——最终受害的似乎都是女人。当然了,安东尼·威勒斯和艾利略特·斯皮特斯确实在电视上受尽了羞辱。但他们淡出公众视线一段时间之后,又无一例外地回来了,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而这些事件中的女人却无法如此轻易地抚平她们生活中的伤痕。
但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不怎么开心:自恋?疯女人?
你们也许还记得,就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名字的5天前,FBI——就在琳达·特里普找到特别法官肯尼斯·斯塔尔向他透露我与总统的恋情时——早就将我控制在了五角城市商场内。1998年1月16日,24岁的我蜷缩在一间宾馆房间里,一些接受斯塔尔命令的盘问官们在我周围。他们不准我联系律师,并且威胁我如果否认与克林顿的婚外情的话,我将会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以及其他的指控。他们说,如果我同意带上监听器记录与总统的两位心腹,甚至总统本人的谈话的话,他们就会放了我。我拒绝了。向琳达·特里普的坦白换来了一场无意的背叛。但要是我照做了呢?简直就是对所有事情的背叛。我做不到。也许我是大胆、愚蠢,但是我自恋吗?我是疯女人吗?
这份被埋藏了16年的言论又把我带回到过去的痛苦,特别是让我感觉到女人是在处心积虑地难为彼此。你们也许会问,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都去哪了。
这也是让我苦恼了多年的问题。
我仅仅希望,女权主义的阵营能给予我一些理解。一些老派的女孩之间的正能量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鉴于当时的情况——性别政治、工作场所的性行为——你们应该觉得她们会站出来替我发声。但是她们没有。我能理解她们的窘境:比尔·克林顿一直都以对女性“友好”的形象示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件事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骚扰”;宝拉·琼斯曾经对比尔·克林顿提出了这项严重的指控。“多亏”当时的女权运动有了一些进展,我的名字才得以在一些列的广泛调查中浮出水面。琼斯的指控于是变成了右翼分子对抗支持克林顿的女权主义者的把柄:既然如此她们为什么还要支持性骚扰的调查呢?如果总统是共和党人又会怎么样?于是关于他为人虚伪的流言开始流传。少许现代女权主义代表的声音确实从侧面传达了出去。但是,我们得到的并不是一些有意义的结果,而是1998年1月30日我与克林顿总统事件的持续发酵。丑闻曝光后的第9天。曼哈顿伯纳丁餐厅的鸡尾酒会。参与者有:作家艾莉卡·琼、南希弗莱迪、凯蒂·罗非、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周六夜现场》的编剧帕特里克·马尔克斯;马瑞莎·鲍文,在线杂志《文字》的编辑;时尚设计师妮可·米勒;前女强人苏珊·夏洛格;还有当晚的主人伯纳丁餐厅的合伙人马盖·科兹。《纽约观察家报》把这群人聚在了一起,以便彼此之间交换实习门的内幕,同时讨论的结果还会被弗朗西·普洛兹记录下来。(可惜的是,真正促成这场聚会的人——马琳·道德——并没有出席。现在我还会时不时地约她出来喝两杯。)
噢,那次聚会真是简直了:
马瑞莎·鲍文:他的一生都在于掌控,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非常有智慧。他的妻子也非常有智慧,似乎能熟练地掌握一切。但是和一个并不怎么出彩的女人在椭圆办公室里发生关系,这真是有意思。
假如我在场的话:我并没有说过我这个人很出彩,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出彩的人?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白宫。
苏珊·夏洛格: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自私?自私而且过分,享受了对方的口交服务却没有回报?我的意思是,她并没有说“他让我很满足”。
我:我什么时候“并没有说”这话?我在哪一份公开声明中没有说?我在哪一份证词里没有提到?
凯蒂·罗非: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是因为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长相,她长得可真是有趣。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总统神化,所以当肯尼迪与梦露传出绯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合理,因为他们俩都是属于神级的人物。我是说,我总是听到别人说莫妮卡·莱温斯基长得不好看。
我:好吧,谢谢你。媒体公布的我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护照上的登记照。换做是你,你会愿意把你的登记照给全世界都秀一遍,让大家觉得你就长那样吗?你的话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想要和一个重要人物发生关系,首先女人得长得漂亮才行。如果这都不算是把女权运动的进程往回拉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算什么了。
艾莉卡·琼:我的牙医说她有牙周病。
夏洛格:你觉得她会怎么样?我是说,她是会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还是干脆出本书?或者说人们不出6个月就会把她给忘了?
南希·弗莱迪:她可以出租她的嘴。
我:无语。
琼:但是,你要知道,人们确实喜欢那些接近权力的“嘴”。想想在她跪在他身下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吧,“噢,我的天。”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像对总统一样对我!做啊!
我:还是无语。
我,本人,对于发生在我和克林顿总统之间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
我再说一遍,我,我,本人,对于,发生在我和克林顿总统之间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当时——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段关系是真实的,是相互的。我们频繁碰面、共同计划约会、煲电话粥、送礼物。20多岁的我还太年轻,还不知道现实的残酷,还不知道自己可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回首那段往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一切可能挽回那一切。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我也会想到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她真的参加2016年的总统竞选,会怎么样?如果她真的赢了——并且连任了,会怎么样?
但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白宫将会迎来第一位女主人。我们都记得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呼喊:“个人就是政治!”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和比尔·克林顿之间的事情是私人的,不应该被卷入政治斗争中。当我听说希拉里有意参加竞选的时候,我简直无法想象媒体们对我新一轮的攻势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不会写出“她现在怎么样”这样的标题,福克斯电视台会不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报道我的事情。我的生活轨迹几乎与政治事件紧密相连,这使我感到非常无力。对于我来说,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当希拉里竞选总统时,我几乎完全过着隐居的生活,推掉了一切媒体项目,那些项目直到2012年的竞选结束才重启。(还有,并没有人给我120万美金让我写一本书,媒体的报道是错误的。)而最近,如果她真的打算参与竞选的话,我又有些害怕了,害怕再一次成为焦点。可是,难道我又要让自己的生活在10年、8年内停滞不前吗?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民主党人——并且深知自己有可能被左翼或者右翼利用——在这10年内,我保持了沉默。沉默到有人觉得是克林顿一家人用钱堵住了我的嘴,因为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让我闭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选择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呢?因为时机到了。
去年,我正式步入不惑之年,我不能再徘徊于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的未来了。我一定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不一样的结局。终于,我决定站出来,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这一切,给我的过去赋予新的意义。(而至于后果,我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不管媒体头条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标题,这并不是我与克林顿家族的对抗。他们的生活早已翻篇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我祝福他们。我也全心全意地明白,未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与他们任何一个人有丝毫瓜葛。
问题又回到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自从1998年以来,我的名字出现在了许多全国性的问题中。我们要让政治渗入到我们私人生活的多深处才满意?我们应该怎样在隐私与性行为曝光的需要性之间平衡?政府不停地窥探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的私人信息,我们要怎样保护自己?最后,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如同我所遭受的那番羞辱?(目前,我的目标就是为和我一样遭受过公然羞辱的人们做出努力,并开始在一些公开论坛中发言。)
到目前为止,“那个女人”从未摆脱过别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我是那个难以预测的傲慢女人,是那个愚蠢的荡妇,也是那个可怜的受害者。克林顿政权、特别法官的手下、白宫走廊两边办公室的人、媒体,都可以随意塑造我的形象。而那个形象一直没有改变,因为这其中有权利的参与。于是我就变成了任何人讨论女性、性背叛、政治和身体等话题的主体。
和其他参与者不同的是,我当时太年轻了。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因此就算现在的我想要回到1998年以前,也不知道该给自己一个怎样的定位。我没有让那一件事情定义我——只是1998年的我太年轻,还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型。如果你还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的话,你就很难不接受别人所塑造的那个你。(因此,我非常同情那些在网络上遭受网友羞辱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以来,我一直不停地寻找自我、接受心理治疗、尝试不同的道路,我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但我不会再这样了。是时候摘下贝雷帽、脱下蓝裙子了。我要向前看。(来源:2014年5月《名利场》杂志)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