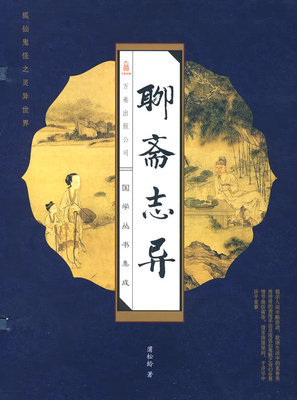郭松龄发动兵变的目的,见仁见智,姑且不论;然仅就其不明白“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这一点,足见其政治上的弱视。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沈阳东陵区,其父是个私塾先生。早年入私塾读书,19岁进入奉天董汉儒先生开办的书院读书,190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开始学习军事知识。郭松龄勤于职守,深得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1909年,朱庆澜调入四川驻防,任陆军第34协协统,郭松龄随朱入川,任第68团连长、营长,随后不久郭松龄加入同盟会。1912年四川受武昌起义的影响,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朱庆澜任副都督,但随后不久,朱庆澜受到川籍将领的排挤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也无法在四川立足,只好离开四川。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次年进入中国陆军大学。1916年郭松龄从中国陆军大学毕业,被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从事军事教学工作,随后不久由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朱庆澜将军担任广州省省长,郭松龄南下投奔朱庆澜麾下,先后担任粤、皖、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州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后来又调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广州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郭松龄无法在广州立足,只身回到奉天。
回到奉天的郭松龄在陆大同学、时任督军署的秦华的推荐下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重开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调入东三省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在这里,他结识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二人结成莫逆之交。时年郭松龄36岁,张学良19岁。张学良毕业后,向张作霖力荐郭松龄出任自己的副手。随着张学良的升迁,郭松龄从担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起,先后担任调停直皖战争先锋司令、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主力之一第三军副军长、奉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实际上就是奉军主力的统帅。在此期间,郭松龄始终和张学良组合在一起,军中一切大事,郭松龄都可以做主。
张学良晚年自谦:“我的前半生完全靠他”
因为张学良的缘故,张作霖对郭松龄开始格外关注,1921年5月,郭松龄被破格提拔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在合署办公的框架下,张学良完全将军队的指挥权和人事权交给郭松龄。在郭的主导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军队系统开始创办军需独立制度、提拔军事院校毕业的学员出任官佐,三、八旅的军事战斗力大为加强,远远地将仍有绿林习气的其他各旅甩在后面。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军队成为奉军的模范军队。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由张学良任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的奉军东路军第二梯队虽然在奉军整体溃败的前提下,撤退有序,仍在三海关一战中,在临榆、抚宁一线顽强地抵抗了几倍于己的追兵,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取奉天的进攻,使得奉军的主力得以安全撤回奉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和郭松龄已然成为奉系集团两颗军事新星。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将奉军编为三个军,张学良和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军长,是奉军的主力。在山海关、九门口的主战场上,郭松龄在关键的石门寨、黑山窑战斗中,率领部队,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一举突破直军防线,为奉军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奉军中掌握军权的人物。
在长达七年的合作中,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共事与合作始终为奉系集团内部众多人士羡慕不已,也为外人津津乐道。据张学良1926年12月31日自责通电中说:“爰识郭某(指郭松龄)于寒微,遂竟倾心相属七年,赞翊擘画多方,昕夕无间,情同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度狂澜……”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和依赖是超乎寻常的。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都是郭负责,军事指挥和一般人事任免也多由郭松龄操持。张学良如此放手,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郭松龄对张学良也很尊重,平时做事都是经请示后才决定,少有依仗信任而有所跋扈,尤其是张学良坚持的事情,他多是服从。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学良的灵魂。”张学良自己就曾经公开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俩之间的骨肉般情谊。
郭松龄公开坦言:“一身所有,皆公之赐。”
郭松龄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随着张学良的升迁而升迁,尽管在这七年的时间里,郭松龄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加上他自己的才干,迅速成为奉系集团掌控奉军主力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都与张学良的关爱分不开。郭松龄是个感情用事的人,也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就因为和韩麟春、姜登选闹口角愤愤离开战场,是张学良连夜追赶到他,经过劝说才将他拉回战场上。张学良对郭松龄说:“茂宸,你要干什么?从前我是你的学生,可今天不同啊,我现在是你的长官,没有我的命令,你擅自率领部队离开石门寨,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这怎么行!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你要抗命,就开枪把我打死,不然你就得服从我的命令。”在张学良的诚恳劝导下,郭幡然醒悟:“我违背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张学良扶着郭松龄的肩膀说:“老哥,你愿意死?要死,你到前线去死,何必让我处死你。你要给我争面子,就带领部队把敌人打垮。”正是张学良这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了赫赫战功。这与张学良的真诚和诲人不倦分不开。
奉系集团内部本身隐藏着重重矛盾,有“士官派”和“陆大派”、“老派”和“新派”、“文官派”与“武将派”之争。张作霖对于影响奉系发展的后两个派系之争看得较重,解决得也很好。但对于士官派和陆大派的纷争张作霖过问得并不是太多,因此这两个派系的矛盾愈演愈烈。尤其体现在郭松龄和杨宇霆两个人身上,两人几乎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杨宇霆作为“士官派”的领袖始终压制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张学良也和郭松龄深有同感。在这种长期的矛盾中,不仅张作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就是张学良也没有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劝导,反而对郭松龄表现出格外的同情。如在1924年11月12日郭松龄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我要推你继任东北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年仅24岁的张学良听了,骤然骇然失色。但张学良既没有批评郭松龄,更没有劝导郭松龄,反而对他的话表现出漠然处之。
尽管奉系内部矛盾重重,但整个集团仍能形成以张作霖为核心的统治构架。张作霖在奉系集团内部最倚重的智囊人物是杨宇霆,军事指挥人物是郭松龄,“经世治国”人物是王永江。由此可以看出,郭松龄在张氏父子心目中的地位。
“兄弟”志同道不同,分道扬镳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怀。早在东北讲武堂时期,郭为战术教官,张为学员,两个人就有着将来共创伟业、大展宏图、造福桑梓的梦想,他们彼此互相激励,总以天下为己任。
但随着职位的升迁,郭松龄性格中的弱点越加明显,他孤傲、盛气凌人、刚愎自用、意气用事,并且心胸狭窄,揽权的企图越来越明显。郭身上所有的缺点张学良几乎都能予以宽容、谅解。但由此引来的却是郭在1925年11月30日,也就是反奉的第九天给张学良的信中将多年来对张学良的不满和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我公(张学良)为人多疑好杀……公明知龄与韩不能相容,而此次出兵,又复使伊与龄并列,更委于珍为副军团长,使龄受其节制。公(张学良)乃诿为主帅意旨,事前不知,此语谁相信耶?夫信用韩、于,权操我公(张学良)……而龄所保荐部下之不信任,龄所陈述政见之不采纳,犹其余事耳,此应请公反省者一也……嗣与李景林榆关血战,我公父子始得保持地位,至于今日。我公父子对李景林及松龄之信用,果何如耶?此应请公反省者二也……去年榆关战役子弹缺乏时,我公复欲支身后去,经魏婉劝始止。公乃自云‘不忍舍弃将士’,证以前事,龄实未敢深信。此愿我公反省者三也。”

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2日起兵反奉之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进行的,不仅郭的部队被蒙在鼓里,就连张学良也被蒙骗。张在得知郭发布通电是“清君侧”,惩办杨宇霆,请张学良主持东三省大政之时,想尽各种办法企望能够与郭松龄见上一面,然而郭却决绝不与张学良见面,甚至不接张学良打给他的电话。张通过写信仍幻想可以劝说郭松龄幡然悔悟,甚至可以答应郭提出的任何停战条件。
张学良在给郭的信中写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必能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在这封信里,张学良明白无误地向郭松龄表明自己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同时也隐含着指明了郭松龄起兵反奉动机,向郭松龄提出只要达成双方停战,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并保证事后郭松龄的安全。
然而郭对张学良的转信人日本医生守田道出了他的内心独白:“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台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可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人。”由此可见,郭是急于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采取的这次反奉行动,目的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
张学良很看重郭松龄的才干,不仅如此,张学良对郭的很多主张也是深表赞同的。但是郭的做法张学良是完全不能认同的。倘若郭能收敛锋芒,与张同心协力,事后应该会有大的作为。张学良在晚年还深深表露出对郭的惋惜之情,他甚至说,如果郭不死,日本对东北就会有所顾虑。张学良对郭之死更多的是同情、惋惜。
张作霖咆哮大骂:“郭鬼子忘恩负义,小六子上了贼船”
郭松龄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同盟会会员,早在郭松龄任讲武堂教官时,张作霖就在一次和郭松龄的见面时对郭说:“你不是那个同盟会吗?怎么愿意到我这儿干了呢?我不管你以前如何如何,现在在这儿干,只要你有本事,我就升你的官。”郭默然无语。
此后的张作霖对待郭松龄基本上是按照他的用人思路进行的。即只要跟着他,只要有能力,我就给你升官。
张学良作为长子始终是张作霖重点培养的奉系集团的接班人。据张学良自己说:“我本想做一名医生,没想到不但没有救人,反而学会杀人了。”张作霖一心一意希望张学良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所以张作霖刻意培养张学良。对于张学良大力举荐的郭松龄,张作霖每每都屡荐屡升,甚至打破惯例,采用两旅合署办公的形式将郭松龄和张学良组合在一起。这些无不倾注了张作霖对他们二人的巨大感情,这其中固然有郭松龄的能力和战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张作霖是把郭松龄看作张学良的襄助者和辅佐人。
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仍然秉承着以往的一贯做法,将奉军的精锐和几乎全部的主力交给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实际上就是交给郭来指挥,这是奉军中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令张作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却引起了郭松龄的极大不满。郭自以为张作霖赏罚不公。当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南遭到反奉势力的打击,溃逃江南时,郭松龄开始瞒着张学良秘密筹划反奉倒张。
在郭松龄发出讨奉通电时,张作霖完全没有料到郭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他初以为他的儿子张学良和郭一同密谋反对自己,逼自己下台,大骂张学良学唐太宗李世民,逼老子下台。眼看着郭的大军(张作霖的全部主力)开向奉天,张作霖曾扬言交出大印,让他们俩上台表演好了。后来得知儿子并没有参与郭的倒张行动,才开始想办法组织力量对抗郭的进攻。
郭的通电一发,对于张作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来郭军力量强大,二来自己手中却也无可用之兵。情急之下,曾想一把火烧掉大帅府。稍后郭军进军速度迟缓,张又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才开始组织张作相和吴俊升的部队抵挡郭军,同时命令张学良亲上前线指挥部队。在张学良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心理攻势下,郭军土崩瓦解。这一次张学良与他的老师对阵,并战而胜之,张学良的统帅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
郭的反奉,对张作霖和奉系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张作霖的个人生涯中也是一次巨大的挫败。在奉系集团内部,虽然有过像汤玉麟、张景惠、杨宇霆那样身居要职的人反对过他,但最后都被他收为己用,奉系内部更多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的跟从他打天下,现在无意间冒出个郭松龄反奉,让他恼火至极。
张作霖在处理郭松龄反奉兵败的善后会议上,仍恨恨不休地大骂张学良和郭松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鬼子的贼船……李景林、张启坤、许兰州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于学忠)是吴子玉(吴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个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
张作霖是个满脑子都有升官发财思想的人,他对待属下从不讲什么主义、正义,只讲好处、利益。正如他在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者也是他的好朋友孙中山的谈话中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他对孙中山说:“孙先生您应该放弃联俄联共的政策,因为各国公使跟我说他们都反对这个政策。您也不要反对外国人,我愿替先生去疏通与外国人的感情,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张作霖一生崇信关羽,讲究忠义,对所谓的离经叛道深为痛之,所以当郭松龄打着义旗造反时,他恨恨不已,不仅将他处决,还将他剁去双脚,在奉天小河沿曝尸三日,并将其惨象拍成照片分发东三省全境。而张学良目睹郭之照片,惨不忍睹,命令属下将之焚毁。张氏父子对郭的态度和感情完全不同。
郭松龄反奉在近代东北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战乱。他几乎推翻了张作霖的统治,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社会各界普遍受到震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很有代表性。当年沈阳《盛京时报》就有署名铁生的一段话:“郭公为改造东三省之伟人,为民请命,奋不顾身,今不幸罹于死难,凡我同胞,同深悼惜。今敬撰挽联一副,以哭当歌。上联云:‘死者不复生,惟有前仆后继,偿我公未了志愿’,下联是:‘忍者夫已逝,行将众叛亲离,尽他日依样葫芦’。”这种声音代表了民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普遍心声。是对郭松龄反奉行为由衷的敬意和无限惋惜。另外还有一种声音似乎更多地代表了彼时普通民众对郭松龄为人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署名“农民”登在《盛京时报》的一副对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
如果说从张学良的角度或者站在张家父子的角度来说,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似有不妥;如果站在民众厌恶军阀统治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来说,郭松龄反奉就是正义之举。对于历史来说,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论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希望我们现在的读者在读这段历史时从中也能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