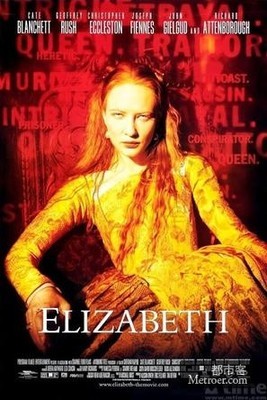白先勇和他的同性戀人王國祥

http://man.eladies.sina.com.cn/n/2005-05-20/165918934.html
新浪男人
欲将心事付瑶琴
---浅析白先勇作品中同性恋形象和作者本人潜在的情感联系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斐声海内外的小说家,他的文章,语言精美,主题深刻,人物鲜活,技巧高超,具有沧桑感怀的幽远境界,其中的多部作品已成为华文作品中的经典。同时,他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五部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同类作品之中的翘楚。它们分别是: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青春》、《孤恋花》、《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月梦》,长篇小说《孽子》。其中,《孽子》不但是其写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同时也是公认的华语同性恋主题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一、那些青春鸟的旅程:少年形象分析
“那些青春鸟的旅程”是《孽子》第三章的标题。在这部小说里,白先勇用“青春鸟”这一别称,来指代故事中所有同性恋少年的形象。在白先勇此类作品中,少年主人公的形象占去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或是天性异禀,或后天受环境影响,都或浓或淡地体现出与常人相异的性向特征。少年时期,欲望真实、敏感而又强烈不加掩饰,而作者少年时的某些真实的感受,就这样清晰地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一) 同龄少年之爱
此部分要讨论的是年龄相仿的少年形象间的感情关系与情感特征以及作者少年时性向在作品中的投射。
1.寂寞的十七岁
十七岁,敏感而多情的花季年龄,为何会寂寞?作者用《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杨云峰,作了最好的诠释。
杨云峰性格孤僻,学业不佳,始终无法在对其期望极高的父亲面前抬头。在学校一无所长且不善交际的他没有朋友,更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始终觉得郁闷孤单,以至于到了自己给自己打电话的地步。在他就读的南光中学,唯一可以让他倾诉、并理解他的,就是魏伯炀了。
在体育课上,杨云峰意外受伤,在众多嘲笑他的同学中,只有班长魏伯炀扶起他去医务室,并护送他回家。路上,杨云峰回想自己在家及在学校遭受的种种不平,忍不住大哭:“平常我总哭不出来的,我的忍耐力特大,从小就被同学作弄惯了……爸爸妈妈刮我,我也能不动声色……可是枕在他的臂弯里,我却哭得有滋有味。”
从此之后,杨云峰对魏伯炀的感情更加深厚,他不但找各种机会和魏伯炀待在一起,而且还幻想“他是我哥哥,晚上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多聊一会”。上述种种都可以证明,魏伯炀已经是杨云峰的唯一情感依赖。对于这种情感的把握,或许姑且可以认为是男孩子之间深厚的友情,但杨云峰对魏伯炀的好感却实实在在的超出了对一个朋友的程度。以至于到后来,杨云峰的同学都开始对他们的交往议论纷纷,说他是魏伯炀的“姨太太”。终于,在风言风语中,两人疏远了,杨云峰十分苦闷,“我真的想出家当和尚……从来没有这么寂寞过。”
由此可见,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寂寞感情明显是由一个同龄的同性少年来排遣的。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相对单调的文化环境,年少而无知的单纯心境,这一切都使得主人公无法对自己做出定论,而作者的高明也在于,他并没有用什么来鲜明地点清主旨,而是让读者悉心把握。实际上,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已给足了明示。杨云峰在新公园(这又是个巨大的明示,白先勇的最重要的同性恋作品《孽子》就是以新公园为主要背景的)闲逛时受到了一个男同性恋的试探性骚扰。这一看似偶然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而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白先勇,恰逢国内连年战事,同时又因为少时曾患传染病而一度被家人隔离,所以童年时所经历的孤独心境,直至成年都依然鲜明。在家人宴请宾客,歌舞升平之时,他却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霎时,一种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又由于其父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陆解放之后,举家迁至台湾,白先勇自然对陌生环境感到极不适应,生活中除了读书,就觉得没有其它乐趣了。这一切都在《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的身上有明晰的体现。这般愁苦的心境,自然需要对象来排遣。《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炀,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必然是作者本人对其朋友的感情投射。由此可见,作者同性相恋的倾向,在年少时就已初露端倪。
在可查询的白先勇作品之中,朋友王国祥是作者笔墨花得最重的一个人物。在《树犹如此》中,白先勇把他和这位好友从高中到大学,从台湾到美国,从共同培植园林到不远万里帮助朋友求医问药的细节娓娓道来。两人情谊的点点滴滴,在作者饱含深情的笔下,都有了洞察心灵的力量。从友情角度分析,两人堪称至交。但若从同性相恋的角度来讲,文中的某些片断才更能让人理解。例如,白先勇为给王国祥治病,只身从美国来到大陆,遍访河北、浙江名医。或许真的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使一个人为一个朋友踏遍千山万水而毫无怨言。而这种力量是否还在友情的范围,可由读者细细体会。
由于资料有限,且白先勇本人在作品之中,以纪实或回忆方式记录个人少年情感片断的情况并不多见,故以上分析均只能是推测性结论。
2.龙凤情深
《孽子》是白先勇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华语同类题材作品之中的扛鼎之作。王夔龙(龙子)是将门之后,学业初成,意气风发。结识了新公园中的“名角”阿凤。两人宛如“天雷勾动地火”,相见恨晚,情意绵绵。龙子随即逃出家门,在稻田边与阿凤共筑爱的小屋。作品中,龙子英俊高大,家境殷实,用情专一,阿凤潇洒矫健,浪漫多情,忧怨频生。二人故事背景中常伴随一望无垠的金黄稻田,忽明忽暗的银色星空,争相怒放的红色莲花等浪漫唯美的景象,再加上阿凤与龙子的感情纠葛始终以过去时出现,所有故事陈述者的口气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羡慕与向往,这一切,都使得此二人的感情充满了浪漫与唯美。而龙子亲手将爱人阿凤刺死的结局则使得二人的感情更加轰轰烈烈。在新公园这个男同性恋的世界里,他们的爱情凄美多于真实,已经成为作者笔下的一个只能供传说的神话了。
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同性恋主题晦涩不明,而在《孽子》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情节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给予作者无限的空间与平台去解构、诠释作者内心深处的同性恋情结。从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李青(即作品中的“我”)一出场,阿凤和龙子的感情纠葛就由他人之口,在其耳边萦绕。此时,阿凤已死去多年,从美国归来的龙子也已沧桑中年,读者都是通过作者安排不同人物的回忆和转述,来对阿凤和龙子进行概念化的把握,但结论都几乎一致:这是一对痴龙怨凤,这是一幕过于凄美浪漫的爱情悲剧的传说。
少年形象是《孽子》的主要群体。作品中大部分的主人公都是无家可归或是有家不能归的少年。他们因为相同的性情走到一起,在台北新公园的莲花池边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王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世俗的道德礼治被暂时搁置,少年们用自己的标准理解和构筑他们的爱情。在这里,少了些世俗的羁绊,少了些家庭的干涉,而少年又因为年龄的特点而大胆执着,所以他们的感情就显得壮烈而唯美。龙子和阿凤的纠葛就是这种感情的最佳代表。
在这样一个宽阔的写作平台上,作者用这样浓情的笔墨构筑了自己的情感乌托邦。根据大多数人的观念和社会的礼制习俗,同性恋都是异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自己有相同取向的人相识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在这有限的人群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所以,这样的巧合一旦发生,或者是作者理想中的臆造,白先勇自然会倾注惊人的浓墨重彩。这正是他的同性爱情观。既然它不为世人所容,那么它就一定要像传说般浪漫动人,像神话般轰轰烈烈。
作品中有这样一处设计,龙子的父亲是军界要人,家境殷实。龙子杀死阿凤触犯重罪,随即被家人送往美国避风头。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为国民党五星上将,白先勇大学毕业即去美国深造。这种巧合化的设计或多或少是为了让龙子身上折射出作者的影子。而龙子对爱情的执着则无疑就是作者在尘世中苦苦追寻真情的明证。
(二)兄弟之爱李青是《孽子》的叙述者和第一主人公。他和其弟(名叫弟娃)感情极深。李青的家庭是一个破败残缺的家庭。父亲是风光不再而终日沉浸在回忆中的退役下等军官,而母亲又生性轻浮,最终和一个小号手私奔。在父亲严厉暴躁,母亲轻浮失节的情况下,兄弟俩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日久弥深。和弟娃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都成为李青后来在新公园孤独无助彷徨时最美好的回忆。这种回忆,因为弟娃得病不治而亡而更加深刻。无论是在李青“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在李青寂寞独处的时候,包括在梦中,弟娃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以至于李青不得不在生活中找寻一些替代性的人物来填补弟娃留给他的空白。从在咖啡厅结识的让他恍惚失控的少年到他从新公园收留的并甘心照顾的痴儿“小弟”;从在路经校园时一起打球的活泼男生到小说结尾时和他一起跑步奔向前方的罗平。从小说开始到结束,李青的感情归宿百分之百的寄托在了弟娃的身上。
手足情深,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李青具有爱恋同性的性向,而且置身于这样一个聚集着他的同类的台北新公园之中,他对于弟娃的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兄弟之情。这种感情带有一定迷恋和爱恋的成分,有浓烈的同性相恋的色彩。实际上,这种“哥哥”与“弟弟”之间的感情是同性恋世界中一种极常见的情结。很多男同性恋者都喜欢把比自己小的同性当作弟弟一样来关心爱护。“弟弟”只不过是一个能让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称谓,爱人才是“弟弟”真正的名称。
白先勇在家中排行第七,其下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但在可查作品与资料中,白先勇并未对其任何一位兄长或弟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喜爱。所以可以判定,文中李青对弟娃的深厚感情并非作者真实生活的投射。但生活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思想的真实,白先勇之所以赋予主角人物这样一种特殊而又强烈的情感,事实上就是其自身情感欲望的写照。《孽子》成书于1981年,其时,白先勇已经45岁(此时他依然孑然一身)。这是一个人已不惑韶华难寻的年龄,但那种对青春与年少的热望却始终不曾消减(迟暮伤逝的情感在白先勇的作品之中几乎处处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寻一个少年(弟弟)作为情感寄托,则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是否确有其事以及这个少年是谁,相信只有白先勇本人才会有一个肯定而明确的答案。
(三)对父亲的复杂情结
在《孽子》中,小玉是新公园里的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他有着十分动人的外表和很强的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并笼络其心的能力。据他的母亲讲,他自出生之后,其父便去“东洋淘金”,一直没有再回来。其继父“山东佬”脾气暴烈,发现小玉在家中与邻居私通后,将他逐出家门。缺少父爱的小玉始终喜欢年龄比他大几十岁的中老年男性,诸如给他小恩小惠的“干爹老周”,给他创造工作机会的日本华侨林祥等等。为了寻找父亲,他最终设法搭乘上去日本的货船,从此开始了他的寻父生涯。
在作品中,小玉总是在想象中把生父描写成一个完美的形象。(比如他曾对李青说,按照他母亲的说法,其父的长相和日本演员池部良很相似。)并把找到父亲作为一生的终极目标。否则“死也不肯闭目”!单以父子情深来解释他对生父的魂牵梦萦过于简单,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同性相恋的成分。实际上,“干爹老周”也好,华侨林祥也罢,都可以说是小玉那淡淡的恋父情结的对象。他们的年龄和父亲相仿,给予他的又是同龄人无法给予的细致关爱,暗示着一种父亲的角色。只是小玉认为“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到底是差些的”。
在白先勇的许多作品中,父亲,总会具有下列特征:威严、正派、传统、视荣誉为生命。在他的同性恋题材作品中,这些父亲的身份都几乎毫无二致:例如在《孽子》中,李青的父亲是个国民党川军的一个下等退役军官,龙子的父亲是位军界大员,被称为“老爷子”的傅崇山,(傅卫是《孽子》中一个有着同性恋情结的青年军官形象,傅崇山是他的父亲)也曾任过高级将领。把以上的性格及身份特征加以整合,完全就是其父白崇禧的翻版。与此同时出现的父子关系之中,冲突的色彩总是特别浓烈。《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和其父的矛盾就是很好的代表。似乎父亲们威严传统的一面总是和儿子的心性如水火般难容。在对白先勇许多采访中,他都提到自己的父亲律己甚严,要求甚高。他还说过:“他(指其父亲)不是特别疼我,其实他最爱的也不是我。”而不够完美的亲情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让白将军在有生之年去接受其子白先勇爱恋同性的事实,以白崇禧传统的个性,自然是不大可能的。而这个矛盾便成为父子之间潜伏着的一个最大的矛盾了。但是,父子之情又怎可能轻易的被忽略?一方面,白先勇实在无奈于自己性情和父亲正统观念之间的冲突,把这部小说命名为《孽子》就是一个明证;而另一方面,作为儿子,他怎能不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和理解呢?小玉寻父的行为体现的就是白先勇心灵的回归。白将军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孽子》成书于1981年,可见,白先勇与其父的性情矛盾并没有在父亲的有生之年被解决,这自然成为他心中最难以释然的情结了。
白崇禧将军在儿子眼中是个怎样的父亲,白先勇在其作品中并无正面谈及。但从白将军戎马一生的累累战功中,从白先勇对作品中其它父亲的刻画中,从白先勇自年青时就留学海外,其后写作成就享誉海内外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家教严厉、正直强干、传统威严、荣誉感强烈的白将军的形象。而白先勇的感受,又通过此类作品中“儿子”们来传达。比如杨云峰对父亲严厉脾性的惧恐,李青对父亲暴烈性格的畏惧和愁苦,小玉对父爱的执着追寻以及傅卫对父子之情的极端珍视。综合来看,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但无论如何矛盾,作者始终想通过作品传达这样的理念,父子之情,唯美于它血浓于水般的纯度,深刻于它暴风骤雨般的力度,光辉于它深邃如海般的深度。
二、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老年形象分析《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是白先勇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短篇。在这部作品中,白先勇通过描述老年同性恋形象的经历,揭示了灵与肉的关系。逝去的岁月一如天上的星星一样不可能抓住。这类形象在白先勇此类作品中虽然数量不多,但都具有这个年龄段独特特点。渐渐远去的青春和与生俱来的情欲让他们在矛盾之中苦苦跋涉。白先勇重要的几部同类作品都是在作者步入中年之后完成的(如《孽子》),于是文中作者感情的印记便更加清晰了。
(一)中年形象分析
在《月梦》中,吴钟英医生曾在年轻时与一位少年(静思)在湖心小岛上有过一次肌肤之亲。这次接触带给吴医生强烈的灵肉震撼和唯美记忆,而同时,静思也又因为当晚游水时受凉患上肺炎而离开人世,静思,以及和静思度过的那个月夜,便成为吴医生一辈子痛彻心扉的梦。多年后的某一天,医院收治了一位身染肺炎并已病入膏肓的孤儿,当吴医生发现这个孤儿和静思外貌酷似时,多年来淤积在心中的情感,通过各种方式,毫无保留地爆发了。
中年形象是此类作品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迫于社会和习俗的压力,他们结婚成家,为了追求社会地位,他们事业有成。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比此类形象中的少年和老年承受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以及注意力,于是,强烈的情感欲望只能被压制到一个尴尬的位置,给他们最大慰藉的,只能是对少年时光中那些纯情经历的反复回忆,痛快淋漓、无所羁绊的爱恋,于他们而言,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罢了。这也许就是《月梦》这个标题的清晰含义了。
而令人惊讶的是,白先勇发表《月梦》的时间是1960年,当年的他,仅仅23岁。这是个年轻的年龄。一方面,笔者的确喟叹他如此年轻便有这样收放自如的写作能力和超凡的才气,因为同年,他还发表了《玉卿嫂》;而另一方面,笔者可以判定,《月梦》的出炉必然基于作者本人对于同性恋情心态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相关事实材料的了解和掌握之上。也就是说,23岁的白先勇,早已开始感受,认识,甚至认同自己的心理倾向了。而且,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关注和了解了相当一部分同性恋人群的生活及事实。吴医生必然有生活中的原形。
可以料想的是,在《月梦》发表的多年之后,在白先勇也步入中年的时候,吴医生所经历的尴尬与痛苦必会在作者身上重演。
(二)老年形象分析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是白先勇此类作品中篇幅较短的一个。根据叙述者所转述“教主”(朱焰)的闲言醉语,我们可以窥知这个小说主角一生大概的故事:默片时代他“红遍了半边天”,可有声片一来,他便没落了。之后他改当导演,却又因为酗酒,一身傲骨而得罪明星,所以一流片子总轮不到他导。后来他爱上姜青,一个少男明星,突然觉得自己“从死之中复活过来”,并倾家荡产重拍了曾让他失败的《洛阳桥》,一举捧红了姜青。而姜青却在不久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朱焰的心灵再次死亡。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朱焰,是作者此类作品中老年形象的典型代表。他丧失了青春,却摆脱不了对肉欲的渴望和对过去的难以忘却的回忆。与其有相同特点的人物还有《青春》中的老画家,《孽子》中的盛公和赵无常等。
对于大多数的男同性恋者而言,青春是他们最大的本钱。年轻的人因为拥有它而去炫耀放纵,而年老者却因为缺失它而自觉猥琐。作品中的老年形象对于青春肉体的膜拜,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如老年朱焰对一青年男学生的失控举动,又如《孽子》中影坛前辈盛公对年青英俊小生的提拔以及《青春》中老画家对于少男模特裸体所产生的冲动等等。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举动既是其内心对消逝青春的无望的把握,也是自身天性和欲望的体现。而此时的白先勇已经届不惑之年,他对青春的伤逝之情在他所有的作品之中都有浓烈的体现。青春渐渐走远,这铁一般的规律让作者内心无奈以至痛苦。而社会对同性恋并不宽容的态度以及作者公众人物的身份都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白先勇前半生的感情绝非一帆风顺。一个年届不惑的知名作家在一生最辉煌的岁月里却没有体会爱情的甘甜,创造出这样一些悲情式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老年形象的爱情,在此类作品之中都被赋予了更多“灵”的色彩。朱焰之所以和新公园里的其它形象不同,就是因为他曾经享受过三年的光辉灿烂的艺术生命—“朱焰只活了三年!”实际上,这是作者把“艺术生命”(灵)和肉体生命(肉)的清————楚地分开了。
在白先勇笔下的老年角色中,大部分都有很强的灵性,除朱焰外,《孽子》中的盛公是一位曾红极一时的名角,郭公公也是一位摄影师,《青春》中的画家更是有一种在艺术中寻觅爱情的痴狂。再来反观白先勇,他的文学家身份早已暗示他在老年时,对于爱情的看法,就是要摆正灵和肉的关系。
通过老年形象,作者也体现出一种上升到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上。不仅是同性恋者,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痛惜青春之短暂和年寿之有限。“我们哪一个人,在死亡以前,不是为了营目前之务,在没有出口的人生圈子里忙着在打转转?”那么既然都是这样的一生,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白先勇又给出了明确答案: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就是人除了“肉”,还有“灵”。艺术,理想,爱情,是“灵”的表现。而现实生活和性欲,是“肉”的表现。在无奈的人生定律之下,一个丧失了青春的人,只能靠一份回忆,对“灵”的回忆,来救赎那只剩“肉”的生命,保住人性的尊严。这样,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便在作品之中展现出来了。
三、结语
(一)感伤主义是此类作品之中的感情基调
通过列举所有作品后,笔者发现,白先勇的此类作品之中,少年形象的数目远远超过老年及中年形象,而此类题材的主要作品大多是在作者青年以后成书。明显,这体现了一种作者对往昔的回忆,对青春的感伤。
另外,除《孽子》之外,几乎所有作品的结局均以一种悲怆或黯然收场。例如《孤恋花》中娟娟发疯,《青春》中老画家的尴尬,《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朱焰的黯然离去等等。对于《孽子》的结尾,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认为是“无强加的乐观结局”,但笔者并不认为结尾处让阿青和罗平喊着“一、二”号子行进的“长长的忠孝西路”对他们而言是一条乐观的人生之路。同性恋者的人生之路,并不是白先勇可以预见甚至设计的。他自然希望这条路上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但社会的宽容却远没有走到那一步。这种矛盾,着实让作者难受。
作为一名普通的同性恋者,对于社会的现实也许只能选择接受。而白先勇同性恋者加作家的双重身份却使他能够用笔、文章来对人们的误解进行澄清,对现实进行抗争。这样看,无论作品之中弥漫什么样的基调,作者的社会责任已经实现。
(二)作者本人性倾向在作品中的体现
1988年,《PLAYBOY》杂志记者在采访白先勇时问到:“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的?”白先勇坦然做答:“我想那是天生的。”
1988年,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让一个功成名就的51岁的著名学者、作家去承认和大多数人相异的性倾向,这实在需要相当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和坦然以及自己异禀的天性,从作品之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60年,年仅23岁的白先勇发表《月梦》,作品中对同性爱恋的描写已相当大胆;1961年《青春》、《寂寞的十七岁》又涉及同一主题;1969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的发表已经明显说明了作者对此类现实把握的深度,而此文实际上就是《孽子》的先行本,因为两部小说中许多人物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970年的《孤恋花》表明他已经将笔端伸向女同性恋者;1981年,26万言的《孽子》横空出世,它反映的深刻社会现实,体现的浓厚人文关怀,都是其后同类作品难以匹敌的。
一个并不多产的作家,为这个主题创作了五部短篇小说,一部也是其写作生涯中唯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他用笔之精,功力之深,情感之切,涉面之宽,分析之准,影响之广都超过了涉及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们,这一切的一切,体现的不就是那一颗异于“常”人的心吗?
1986年,白先勇又在《人间》七月号上刊登了题为《给阿青的一封信》,这封名义上写给《孽子》主人公李青的信实际上是他对那些受到同性恋倾向困扰的少年们的告白。他希望用“个人对人生的观察及体验”,帮助他们“寻找自己认为可行的途径。踏上人生之旅”。文中,他通过列举柴可夫斯基、苏格拉底、惠特曼等诸多名人例子来说明,作为一名同性恋者,逃避,自怜,放纵都“无法解决终身难题”,只有接受命运,诚实、努力作人,“才能维持为人的基本尊严”。白先勇个人认同自己性取向并奋斗成名的心路历程在文章之中一目了然。
对于爱情,白先勇写道:“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此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恒。你人生中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您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把握拥有,便是永恒。这段话,也就是白先勇自己的同性爱情宣言了。
(三)从白先勇作品中看到的台湾地区的人文气息
白先勇所有此类作品均以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为背景,所以,台湾地区的同性恋状况从他的作品中基本可以看见全貌:同性恋现象在台已经有一定的历史,而且比较普遍。社会各个阶层、年龄的人群之中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有固定的活动地点(例如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新公园),有固定的交际圈,并尽量保持不和外界发生冲突。但台湾地区的多数民众及人文大环境并不对此持宽容态度。然而以上结论只适合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由于历史,政治,地理,经济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的台湾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文气息也明显更加浓郁,这一点在音乐,传媒,文学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孽子》于1981年成书(实际上,作品已从1979年起在报纸上以连载的形式和读者见面了),一方面是白先勇的写作勇气和社会责任感使然,另一方面,此书的出版也得益于台湾地区相对开放的人文气息。此后,白先勇此类题材的作品和其它作品几乎在短短几年里全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尤其是《孽子》的海外出版,更是在德国、法国引起轰动。与此同时,《孤恋花》、《寂寞的十七岁》、《孽子》在八十年代全部被改编成电影上映。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和当局文化政策的宽容以及民众人文观念的提升密不可分。白先勇深知个人力量的有限,但是,凭借他的才思和不懈,他的作品却在文学,影视,话剧,戏剧等多方面宣传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宽容的人文思想。身为同性恋者的他,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环境对这类人群的偏见,去消除社会对这类人群的不解,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定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了。
(四)白先勇及其作品带给我们的思考
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然而,无论它的历史可以被追溯到多久,
它却总是无法被世俗所容。异性相吸,两性繁殖的自然法则让更多的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同性恋有悖常理,违反人伦。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用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标准去决定和衡量,少数服从多数似乎已成为公理。于是,习俗,道德甚至于法律都是为了大多数人来建立。与此同时,忽略,甚至是践踏少数的利益就变得理所应当。我们是否可以静想一下,这样做,是否有失公平?他们(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或是残疾人等各种被看做是异于“常人”的人群)并没有选择天性的权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最基本的人的权利呢?“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人生而平等,这是几个世纪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同性恋人群向社会呼吁的并非同情,而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也并不是怜悯,每个人都拥有他应得的那份基本尊严,这就够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让我们重新回首白先勇作品中那些感人的片段吧!《孽子》中,无论是李青彷徨无助时还是在他面对客人时,他内心深处缠绕的,却并非是与之相关的钱色交易和自己被压抑的欲望。相反,是对与其兄弟弟娃相处时光的眷恋和对其破败家庭的牵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亲情闪耀的至善的人性之美;《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那无法在家庭学校排遣的辛酸,却能在魏伯炀的臂膀里尽情释放,他像“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他哭得“有滋有味”。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友情闪耀的至纯的人性之美;《月梦》中,在那个“五月的夜晚”,“天空干净得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夜,简直熟得发香”。在湖心小岛上,在“水晶镜子”般月亮的照耀下,吴医生和静思,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肌肤之亲。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爱情闪耀的至真的人性之美。作者白先勇就这样用他的语言和思想,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挖掘“他们”的人性光辉。而事实正是如此,在这样的情节发生的时候,无论我们是谁,也无论他们是谁,都一样的会心生感动。
白先勇曾经说,《孽子》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由此可见,他所关注的,不是这种现象,而是这一类人群。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开始重新考量评判是非的标准,更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们明白,只要有爱和宽容,这个世界便不应有你我他之分,所有的人,都应该被称为:我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