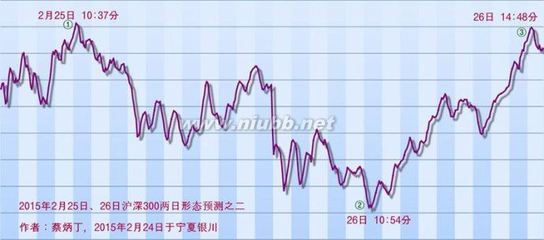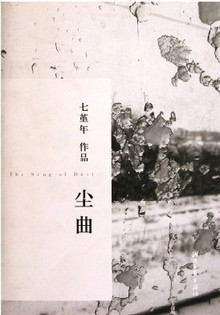(四)
暮夏。
暮夏的白杨,细碎的灰绿色叶片在风中银玲一般翻飞,声姿悦人,斑驳的影子撒了一地缭乱的舞步。我总觉得夏天是一年当中最惨烈的季节,那些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忍耐和蕴积的事件与情感好像都忽然被炎热唤醒了,然后预谋不轨地一齐跳到生活中来捣乱。我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最后一段短暂时间,便是在夏天里。那些中午,我头顶着晌午的烈日,在汽车驶过之后呛人的扬尘中,燥热而狼狈走回家,一路沉默不言。汗水从额前大滴大滴地滚落下来。父亲为我开门,抽着烟,皱起眉头,面色总是不见欢喜。吐出蓝色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得以离开。整个上午他慌慌忙忙地收拾行李,母亲则一个人坐在里屋,一声不响。没有人做午饭。没有人说话。我进门,低着头从父亲旁边擦身而过,径直走上自己的阁楼。我把书包扔在床上,僵坐在那里。
便是在那个难忘的中午——
我躲在蒸笼般的狭小阁楼里热得汗如雨下,却一直没有出来。日光那么剧烈,晌午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母亲的哭声从楼下阵阵传来,父亲沉默。瞬间我听到开门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又重重地被摔上了。
我明白父亲走了。一时间我在床沿边坐立不安,开始不停流泪。双手用力抓着床单,用力到快要把棉布给抓破。十分钟之后,我站起身来便迅速冲出门去一路狂奔到车站,在攒动的拥挤人群中气喘吁吁地找寻父亲的身影。我跑过去拉着他的手不放。烈日之下,我拉着父亲的手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直抽泣,狼狈而无助地看着他。
良久,父亲放开我的手,抹掉我的泪,在司机不耐烦的催促下一言不发地上了车。整个下午,我都站在车站广场。头顶被晒得针刺般灼烧,脸被泪水里的咸涩盐分腌得生疼,感觉皮肤像是一张紧绷得快要被撕碎的纸。夜幕降临的时候,车站里的人渐渐稀落,越发冷清。母亲到车站来找我,出现在我背后。她轻轻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对我说,我们回家吧,绍城。
我觉得母亲的手冷得像是冬夜里飘落到肩头的雪。
父亲走后,生活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常年来我与母亲都早已经习惯了父亲的远去。我开始在梦境里面想不起来父亲的面孔。这个给与我一半骨血的亲人,像是一串来自我生命底部的回声,在森然而闭锁的深渊里,他的声音由强到弱,渐渐幻灭。我开始觉得,有些人事,一开始就不属于你的,就总归是要走。
一季季雁阵归去来兮,掠过空中的时候,啼声忧悒而邈远,把天地都喊得苍凉。依然是在这座萧条冷清的灰色的旧工业城市,绍城,我开始上初中。我毫无选择地又一次要将我的成长交付给它。这一次是青春。
黑漆的紫檀书桌上,陈旧的录音机搭着一块白色的纱棉布,一叠老歌磁带整齐地摞在上面。铁罩台灯,在深浓的宁静夜晚打开一片温情的暖色光晕,安静得而令人伤感。灯下一只苏联产的老闹钟,表盘上是罗马数字,作为爷爷晚年的立功奖赏,走时的时候齿轮之声依然如军人般铿锵响亮。一摞厚厚的参考书和作业本,因为勤奋的使用而卷了角。书桌前的老藤椅泛着暗黄,腿脚不再结实,此刻只有帆布书包安卧在它怀里。而榉木窗棂也已经腐朽变形,斑斑油漆像干涸的土地般龟裂,灰尘模糊了小块小块的方格子玻璃。拉开印有竹叶暗纹的蓝色窗帘,望出去是一片同样陈旧的世界。
这样的老阁楼,让你想起你奶奶的缝纫机,你父亲遗忘在抽屉底部的几枚肩章,或者是你好奇多年的一本的无名的塑料封皮旧日记。而对于我来讲,记忆仅有的作用,只是一再提醒我,我曾经怎样在毫不自知之中炼就了遗忘与漠然的禀赋,用以面对一些妄想中的,或者是事实上的非难。
夜里,当我在安静的阁楼里做题的时候,母亲常常会拿着打毛衣的棒针和线团请求来我身边陪我做功课。她表情悒郁,幽幽地念叨,一个人在下面看电视冷清着呢,上来陪你坐坐也好。你只管做你的功课,妈不打扰你。我每次听见她的声音,心中都会哀伤。
而夜神还不懂得这些,它只会面无表情地伸出可爱的小舌舔一舔嘴唇,蓝眼睛慵懒地望着我。我转身做作业,它便很快索然无味地离去,开始在房间里独自一圈圈神经质地游走。
是那种静得只能听见自己一个人的呼吸的生活。母亲害了肝病,越来越虚弱,早上起不了床,终日几乎是以中药为食。我自然要照顾她。于是每天清晨,我比鸽子起得早,在黑暗中穿衣,然后到厨房去煮鸡蛋,蒸馒头,冲牛奶,煎中药,洗脸刷牙。把早饭和药都放到桌上,唤醒母亲,然后背上书包便去上学。
因为沉默寡言,自己一直都是受人忽略的孩子。在母亲工厂的文体活动中心去借很多很多的书来看。那些书种类繁杂而陈旧,有许多或许自买来就从未有人看过。借书的陈姨说话唠叨,却心地善良,每次看到我去,她都分外热情。而我也经常可以获得多借几本的特权。
我借到的第一本书,是出版年代久远的《安娜·卡列琳娜》。繁体字。人物的名字有下划线。中间有很多很多缺页。开篇的第一句话,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关于这样的旧书,我又想起芥川龙之介的一句话。他说,人生就像一本缺页很多的书。说它是一本书,的确很勉强。但它毕竟是一本书。
那些年,我差不多看遍了那里面所有的书,从《汽车修理》到《水浒传》,饥不择食地阅读,囫囵吞枣。我从不间断地看,无论是在午休时安静无人的教室,还是在人声鼎沸的课间。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说一句话。而我的私人世界亦因孑然独立而被完好地保存了起来,不被任何人所窥视或者打扰。比如说,当我与夜神一起坐在楼顶晒太阳的星期天的下午,或者在深夜的台灯下面写一些从不寄出的信的时候。
而彼时我还不知道母亲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
夜里她肝疼得睡不着,就坐在床上彻夜不眠地织毛衣,神经质地不肯停下来,又开始偷偷地用吗啡,已经上了瘾。发作起来的时候,就像毒瘾缠身那样死去活来。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只能惊恐万分地在门口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吓得不敢说话。母亲第一次连续五个昼夜目不交睫的晚上,我从梦中惊醒,听见她在楼下哭得哀戚。我忐忑不安,轻手轻脚地下楼去,推开母亲房间的门。灯依然亮着,毛衣的线团散落了一地,母亲因为连日的不睡,眼睛里已经全部是血丝。她神经质地对我絮叨,说她总是头痛欲裂,可是到了晚上还是睡不着。
母亲失神地喊我,绍城……绍城……我快受不了了……我头很疼……我想睡一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为什么会这样……绍城……
我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心绪像是一大片荒草着了火,烧得凄凉。
母亲独自一人把我从小养大,我知道她的苦,但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苦。我在她佯装坚强的庇荫之下成长至今,唯一能够了解到她内心的途径,无非是她时不时的郁悒哭泣。而生活在绍城中的郁郁寡欢的平民们,因为底层生活的诸多艰辛,并不对眼泪见怪。包括我。毕竟我们常常在还未清楚了解痛苦的来源的时候就已经安然地接受了它的结果。
母亲的肝病不见好转,失眠很严重,抑郁,幻听,厌食,精神常常游走在崩溃边缘。常常卧床低烧,浑身无力。形容邋遢憔悴,越来越自闭,拒绝任何形式的出门。已经不能够去上班。请病假在家。工厂效益不好,她一分钱的工资都拿不到。我照顾母亲的生活。她不肯出门,于是只好轮到我每日放学回家,顺路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给母亲现做饭,煎药。家里终年弥漫着中药味。到了月中旬,就去收发室领取父亲的汇款单。我时常庆幸,因为父亲的抚养费,我们的生活还不至于捉襟见肘。而当我背着书包提着一篼蔬菜和生肉走出菜市场,被偶然碰到的同学奚落或者嗤笑的时候,我已经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冲过去跟他们打架了。
我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心里甚至都不会有一丝不悦。
读书用功。成绩优异。我一度天真地以为,我的成绩会使母亲骄傲,笑逐颜开,心情豁朗……进而康复并且正常起来。然而没有。那段死寂的岁月,母亲每况愈下。常常地,当我在狭窄的厨房做菜的时候会突然听见她紧张地问,“你刚才说什么?”或者“有人进来了吗?”,我知道那是她的幻听症,开始的时候我回答,“不,我刚才什么也没有说”,结果总是让她难过很久,于是后来如果她再问我的时候,“你刚才在喊我?”我就顺势回答,“对,我叫你去拿双筷子,可以吃饭了。”
这些善意的谎言,让母亲好受,却让我无限心酸。
如此黯淡无光的岁月,持续了三年。中考那年,母亲终于还是住院了。
医院简陋而萧条。母亲的病房就在一楼,我每日放学都会绕去看望她,但我总是不敢进去——我只是趴在窗台上,踮起--脚尖,远远地,怯怯地看着我可怜的母亲:她躺在病床上,盖着薄薄的白色被单,浑身插满了各种各样张牙舞爪的管子,吊瓶从来都没有取下来过……
母亲闭着眼睛僵直地躺在那里,似乎毫无知觉,周围也没有人,空旷而明亮的病房里面洒满了白得晃眼的阳光,看起来仿佛是近在天国的门前。我就这样踮着脚双肘趴在窗台上长久地凝视她,脚酸了,手麻了,依然毫无感觉,却无限清晰地害怕,只觉得母亲要离我而去,眼泪就不知不觉猛地唰唰掉下来……
我多想回到童年时光。彼时我还是和伙伴们一起在冬天溜冰,在夏天游泳的无忧无虑的孩子,彼时父亲还会在除夕之夜顶着大雪归来,进门之后放下行李,便把我抱起来举过肩头飞快旋转,笑着叫我的名字,城城,城城。而母亲的柔和笑容,徐徐绽放。
但我知道这一切再也回不来了。
在绍城阴霾的苍穹之下,我年复一年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有的。我就这么念叨着鼓励自己,因为书里面告诉我说,人可以失去一切,但终究不能够失去希望。
初中毕业的夏天。
那日我一大早就去学校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心情有些愉快,照例在回家的路上顺道去买菜,我想多买些母亲喜欢吃的来做好了之后给她送去,一起庆祝一下。
忙活了一阵,我端着香气扑鼻的热腾腾的饭盒出了门,胸口衬衣的口袋里揣着一纸通知书,灼热明朗的阳光下面,我像匹骄傲的小马一样匆匆往医院跑。那日依旧是苍白地晴朗,有些炎热,高大的杨树被风吹得刷刷响,我一路跑着,汗水从额头上痒痒地滴下来。跨进医院的大门,我就看见一大群人在住院病栋前围成一圈,慌张而恐惧地窃窃私语。我忽然一阵莫名地紧张,挤过去看——一具尸体赫然近在眼前,潦草地被一张蓝色的床单罩着,头部大滩大滩的黑浓的血已经蔓延在地面上,床单末端露出的半截小腿赤裸着,也没有穿鞋。
人群中一声惊慌的声音忽然叫我的名字,绍城!!——你怎么来了!!快走啊……
是陈姨。她拽着我往外拖,人们也纷纷拽着我往外拖,他们都慌乱起来,有一个声音无意中说,造孽啊……怎么亲娘跳楼被孩子撞见了啊……
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硕大的铁拳给攥得死死地,呼吸不得,只感觉一阵古墓般的寒气从脚底传遍全身,头晕目眩,竟拿不稳手中的饭盒,砰地一声掉在地上,热气尚存的饭菜撒出来,立马在人堆里被踩成了烂泥,富有嘲讽意味地预兆着一场不幸。我当然早已顾不上这些,不分青红皂白拼了命地对阻拦我的人拳打脚踢,挣脱了之后就朝母亲冲过去……我扑在母亲身体上惊慌地嚎哭,跪在那里,恐惧万分,却又在意识不清之中不幸撩起了床单——就这样母亲惨不忍睹的遗容逼进我的视野——头骨都已经摔得变了形,像一张上了朱红油彩的薄薄的皮影人儿,黏稠的血混合着脑浆从头下蔓延出来,鼻腔也出血……我被吓得不停惊叫,眼前一黑,只觉得一片瀑布般的黑血从视网膜上淋下来,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我惊吓过度,几近昏厥过去。此后发生的事情,我都不记得。
那年暮夏发生的事情是命途之中的一个巨大地堑,黑的裂缝触目惊心地横在路上,深不可测,一直劈入地心去。那一季漫长得过不完的夏天,我常常一整日地独坐,千百次地问,母亲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呢。回答我的声音除了墙上的挂钟又咔嗒一声走过一秒之外,仍然是阒静。我明白这永远是没有答案的提问,我想,也许只是她太累,亦从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一丝希望的缘故罢。但是,连我也不能够成为她的希望么。但凡想到这里,我心里便有隐隐的恨意。
彼时我几乎夜夜噩梦。一再撞见母亲那张满是血的脸,然后痛哭着醒来。我开始惧怕睡眠。在夜里一想起来,就怕得浑身颤抖。
陈姨善心收留我在她家借住。我没有回过家。也不敢回家。在事情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空落的白天过后的黑夜,那些不眠的黑夜过后的白天,我不知道家里阁楼上的鸽子是否依然在白昼里一遍遍寂寞地飞翔,从窗口望出去的夕阳是否依然在浑浊的天色之中犹如一汪猩红的鲜血。而我也不知道夜神因为饥饿早已遛出了家,独自出去觅食,不曾归来。
这一年的流火七月,我过得晨昏不辨,昼夜不分。像个真正的弱者,一言不发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命运中有些事件就像是一个不知从何处踢过来的莽撞的空心球,张牙舞爪地飞过来将你砸晕,有时候碎了一地的金银让你中个头彩,有时候泼了一身的粪土让你翻身不得。世上重大的幸运和厄运都是没有前兆的,也发生得毫无道理。可惜我们常常花费一生的时间去试图追问这个本身就没有答案的问题。
陈姨替我联系上父亲,把事情都告诉了他,让他回来接我。我知道无路可走,只能离开绍城。
父亲回来的那天,陈姨陪我去车站接他。我站在车站的广场,想起了几年前他离开我的时候。同样的夏天,同样的烈日。这样无力地回忆起来,心中忽然有一阵惨伤。
如此我又看到了他。他下车的时候,脸上挂着疲惫困顿的神情。我们面面相对,咫尺之遥,就在那一瞬间,我便觉得他老了。他走过来,只是摸摸我的头,没有言语。这一切与我设想中的情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夜里,父亲与我一起在家中吃晚饭。他问我,城城,行李收拾好了吗。父亲语气平淡,又略带小心谨慎。我沉默地点点头,埋下来不看他。他便又带着无奈,迟豫地伸手过来轻轻抚摸我的头。
翌日临走之前,我却忽然想起了夜神。自从母亲出事,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它了。我不顾父亲的阻拦,失魂落魄地出门寻找。在烈日下,我汗流浃背地循着条条小巷找遍了所有它逗留过的墙脚,但是仍然不见踪迹。最后我筋疲力尽地回到楼下的院子里,难过地站在太阳底下痛快淋漓地落泪,狼狈不堪。父亲走过来,一言不发地摸摸我的头,然后牵着我孱弱如柴的手,带我离开。
我回头,看见我童年时久居的小阁楼还留在那里,在明亮的日光中,瓦片烁烁发亮,鸽子们沿着屋脊站立成一排。灰尘迷蒙的窗户面向我,犹如两只注视着我的流泪的眼睛。
绍城,再见。
(五)
我跟随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南方城市。来到彼地时,夏天仍未结束,空气潮湿闷热,苍灰的云朵布满了的天空,道路都被两旁茂盛葱茏的阔叶大树厚厚地遮盖了,在行人的肩上留下无数斑驳的影子。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座在空气的每一个缝隙中都汩汩流动着伤戚的城市。
当我与父亲出现在他的新家时,我愣住了。
凯站在我的眼前,说,绍城,你终于来了。
这个回忆中的少年,已经长得那么高。穿着宽松的白色T恤,一条看起来很凉爽的水绿色的短裤。修长而健康的胳膊和腿。趿着人字拖鞋。刚刚洗了澡,头发湿湿的,散发着一股洗发水的味道。一张比以前更加英俊的洁净年轻的脸。他对我说,绍城,你终于来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无力地垂下手,将行李重重地撂在地上,抬起头困惑而伤感地看着父亲。父亲表情尴尬,轻声对我说,城城,有些事情你慢慢会知道的。
那便是我来到这个家庭里的第一天。凯带着我一一看房间。这是饭厅,这是厨房,这是主卧,这是副卫生间,这是我的房间……
房子虽不是十分宽敞,装修却精致考究。凯的房间,地上铺的是从日本订购的榻榻米。卧具都是进口的棉布,一片纯色的米黄,枕头是方形。房间里贴着格调简约高雅的墙纸,与枫木家具十分陪衬。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叶脉标本以作装饰。靠近窗台的地方,放置着一架天文望远镜,一套架子鼓,和一把吉他。写字台前方挂着一张巨幅的黑白布画。一个梳辫子的女孩的背影,提着篮子,独自一人消失在空旷荒凉的麦田中。原处的地平线上有一棵树,仿佛那就是她的家。
凯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乐队的专辑封面。他望着我的时候,眼睛还是那么明澈。
父亲在凯的房间里面铺好一套干净的卧具,他说,这里地价太贵,我们家的房子不够宽,你就先和凯住一个房间吧。我沉默地点点头。从包里拿出毛巾和洗漱用具,走进卫生间去。
我站在莲蓬下面冲洗身体,疲惫不堪,觉得周围陌生,亦觉得自己卑微无力。竟然忽地又想起母亲来,于是双手捂住脸,一边冲洗,一边在水中流下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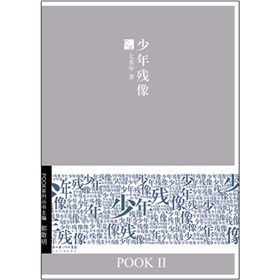
阔别了三年。那个夜里,我们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彻夜不眠地聊天,有说不完的话。
凯缓缓对我说起,当年父母们一起停薪留职下海,凯的父亲意外身亡,我父亲出于道义,在难关上帮了凯的母亲很多大忙。他们渐生情愫,到了后来感情已经非常深。我父亲坚定不移地与我母亲离了婚,来到这里,与他母亲重建家庭。随后,他们把凯和奶奶也带来了。然而凯的奶奶承受不住晚年丧子的打击,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很快病逝。这一系列的变故过去之后,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还算平静美满。
凯一直说,我一直沉默。说到了凌晨的时候,凯起身,一言不发地走过去,坐到高凳上,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只给我留下一个轮廓熹微的背影。他说,绍城,我多怀念,若现在是在你家的阁楼里,那么不知会看见多少星辰。
他又说,你爸爸把你母亲的事情都告诉我了。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有的。绍城。你要相信。凯的言语中有无限镇定与温和,只让我觉得安心。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疲累,渐渐睡了过去。
那是我在那个夏天,头一次沉睡,并且在沉睡中没有梦见母亲的死。
我在新家的生活还很不错。爸爸和凯的母亲对我都很好,凯也一直陪伴我,看得出他们都在千方百计地帮我平复心绪。我内心感动,却不愿表露。白天凯带我到处坐公车逛逛,也买些衣服,球鞋,熟悉下城市街道什么的。下午他就带着我骑单车去海边游泳,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直到月色已高才迟迟回家。
那处海滩显然很少有人来游玩。沙滩很粗粝,十分硌脚,岸边也有岩石。但却因为人少,独享一份安宁。
我第一次看见海。站立在咸润的海风中,因徒然面对过于广大无边的蓝色,忽然就言不由衷地落寞起来。凯朝海边走去,半路上蹲下去捡起了个什么东西。他站起来的时候,举起一只风筝高兴地朝我叫喊,绍城,这里居然有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我就这么远远地看着这个回忆中的少年。那日他穿着一件条纹蓝白相间的纯棉恤衫,健康而年轻的身体,沾满了阳光的味道,头发和衣衫都被风吹得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少年举着一只斑斓的风筝,笑着大声叫我的名字,没心没肺的样子。身后是一大片蓝得让人狠狠心疼的海。忽然间我觉得他像一只生活在海洋深处的漂亮海豚,又快乐又寂寞,和一只寄居蟹作伴就可以度过一整个温暖的下午。
他是我的少年,也是我自己。
月色下的大海,凉爽至极。一股股浪潮给海岸线缀了精致的白色蕾丝。天空之上紫灰色的云朵轻轻飘浮。海边除了涛声,万籁俱寂。我们并排着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壮丽的银河,胸中有怆然的欣喜。
凯伸手过来,轻轻抚摸我的眉毛。他闭着眼睛仿佛是在细细感受,说,绍城,抚摸一个人的眉毛的时候便可以知道他的心事。很久以前,你在我家睡着了之后,我抚摸你的眉毛,便觉得你不开心。因为你在梦里都没有舒展眉头。
于是我也就很忧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