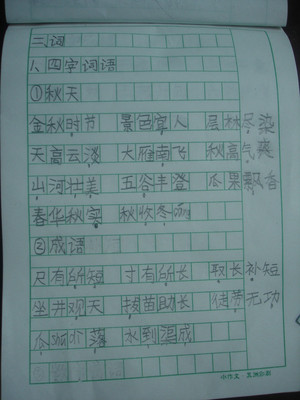“琴姐”
云南乡村的工作员习惯称呼她为琴姐。四十多岁的琴姐是村里有名的能婆,巧媳妇,她地种得比别人好,还有一手精美的绣活。琴姐两口子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依靠种大春水稻,她家的口粮绰绰有余,依靠小春(冬季农作物)生姜油菜,她家不愁柴米油盐酱醋茶。除此之外,琴姐还是村里刺绣项目的发起人之一,通过出售绣品,她既补贴了家用,又赢得了村民和家人的尊重。在绿寨的时候,琴姐非常自信和开心,她总是把家收拾的很干净、很敞亮。在琴姐面前,老公温顺、勤快,儿女听话、孝顺,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谁也无法想象,从2005年开始,琴姐的家境日益衰败。那一年因为女儿考上中专要交学费,儿子落榜要交补习费,她家第一次卖口粮并负债。但出售粮食怎能支付巨额的学费呢?无奈之下,春节还未过完,琴姐与另一名妇女瞒着家人踏上南下广州的列车,开始了漫长辛酸的打工人生,这也是一条不归路。
2006年初夏,我与同事几经转车在广州白云区一个城中村破烂的家族工厂里见到琴姐。那次见面她哭了,因为春节离家后大半年,她除了没日没夜地拼命加班,没见过一个熟人,连广州城是什么摸样都不知道。她开玩笑地说:“我是从那个村来到这个村。”这次见到琴姐她很自信,虽然做工和吃住都在一间简陋的大厂房里,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她的缝纫活(给国际化妆品牌加工配件)做得最好也最快。一般的女工月计件工资七八百元,而琴姐的收入上千元。那天临走时,略带伤感的琴姐对我们说她一定要好好干活,让孩子们安心读书。我们也乘机嘱咐她:“一定要戴口罩上班,防止纤维尘危害身体。”
2008年初夏,我又在广州白云区那间简陋的厂房里见到了琴姐,她明显地衰老了(她已经生病),老公也随她进厂打工。没想到历经三年时间,琴姐的计件工资仍然名列前茅。她说:“女儿正读大学,要很多钱,我和老公加起来每月有两千多(收入)。”当谈到儿子时琴姐很担忧,因为补习一年还是落榜的儿子在电话里告诉琴姐自己在北京,不用担心。琴姐说:“要钱的时候,他(儿子)才会打电话过来,平时没有消息,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他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2009年底又一次见到琴姐,还是在那间破落的工厂里。这次见面,琴姐已经病得无法正常开工,她的计件工资已经不足八百元。她说:“咳嗽,胸痛已经有一年了,也没钱看病,我和老公要回云南看病,已经买好回家的火车票。”我们安排她到广州中山二院体检,医生建议做CT,被她婉拒了。回家后她没去医院,只是找江湖郎中抓了中药在家休养。后来,她又抱病到广州打工……。
2012年5月底,我突然收到琴姐的电话,电话里是她惊吓的哭泣声。“张老师,救救我吧,我得癌症,要死了……”同事立刻赶到医院了解情况,原来琴姐听不懂广东话,把良性子宫瘤理解为恶性肿瘤。好在是一场误会,琴姐大难不死。
最近一次见琴姐是2012年11月1日。当我与村里的另一位在广州打工的夫妇在火车站人群中老远见到她时,琴姐明显地消瘦和憔悴,连走路都慢悠悠的。看到她拖着病体与我们见面时,脸上还是泛着微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眼里感到有些湿润。饭桌上琴姐说她身体越来越不好,这些年拼命打工供两个孩子读书,到头来一个孩子都没有读出来,女儿眼看快毕业了,却辍学嫁给外乡人,儿子到处流浪,也没个正经营生。琴姐说:“很想回家,但回不去呀。村里的房子这么多年没人住烂在那里,光修房子也要上万元。回家种地光买骡子也要花上万元。老公说当初出来是你,现在要回去也是你,没有钱,怎么回去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