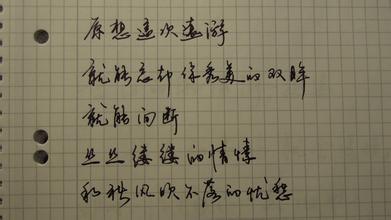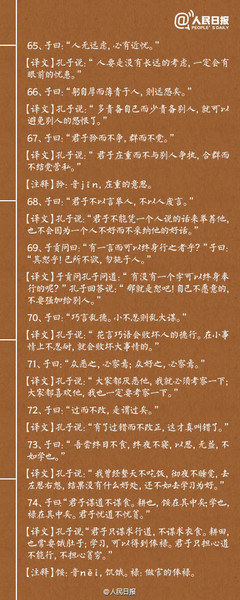掩卷大笑之余,隐约感到笑里藏疑,忙再读钱先生之论,寻找自己思维的盲点,果然有新发现:道士们为解馋而臆造之言固然属于“卮言”,那么“卮言”的准确含意为何?“卮”字看着眼熟,与何炅老师所唱《栀子花开》的“栀”字像亲戚;又想起《史记》里鸿门宴那段,樊哙闯进项王大帐吹胡子瞪眼后,项羽说“壮士,赐之卮酒”,可知这卮字应为一种酒器。“卮言”原意莫非是酒后胡话?
人一较真,事情就接踵而至。
为求“卮言”真解,我翻《辞源》、《辞海》,答案是“随人意而变、缺乏主见之言”或者“支离破碎之言”,“后人用卮言,作为对自己著作的谦词”;而“卮言日出”语出《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句话又看着眼熟,略微沉吟,想起大学课本里先秦文学部分介绍《庄子》一书时引过“寓言十九”之语,但不记得引过“卮言日出”,而我只读过《庄子》的内七篇,《寓言》属杂篇,只字未看。“卮言日出”四字竟与我数次擦肩而过。

钱先生显然在痛贬道士们“卮言日出,巧觅借口”,但我一时理解不了道士们说话如何“缺乏主见”,遂决定从源头一探究竟。恰好手边有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清代浙江书局所刊《二十二子》,便把《庄子·寓言》细读一遍。这一读,发现“卮言日出”之于《庄子》实为褒义。我又在网上搜索一番,读几篇当代人的解释,总算对“卮言”有个相对完整的印象,大致如下:
1、卮言是无主观成见而能随时变化之言。根据古人旧注,“卮”是种圆酒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空满任物,俯仰由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无心即无成见,无成见则不固执己见,无成见之言则能随事而变,则能与时俱进,这种状态与自然变化之理相合,因此“和以天倪”。
2、卮言是没有固定解释的模糊之言。卮言“谓支离无首尾言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支)言耳。”因为支离破碎,所以无法给予固定解释,也便难以模式化、僵硬化,因此不会囿于文字,而是更加关注“言”后之“意”。
3、卮言是不偏不倚的中正之言。“卮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日出则斜,过午则昃,及中则明。卮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极分而已。”
4、卮言是酒后圆滑清谈之言。“卮言,如卮酒相欢之言,举觯后可以语之时之言,多泛而不切,若后世清谈。”
在我看来,“无成见”和“无定解”二解当为《寓言》本意。无成见则能日新,无定解则不拘泥,得其意而忘其言,恰如饮酒而置杯。“卮言”的核心是“无成见”,形式是“无定解”,状态是“日日新”,作用是“得真意”,这似乎符合庄子一贯主张,也正是庄子行文的特点。如此“卮言”,实乃高境界!也许这样的“言”,才算是不偏不倚,才似酒后吐真言。这样看来,“中正之言”和“酒后之言”的解释,并非胡乱演绎。任何事物都非单面,如此境界对凡夫俗子显然要求过高,学而不似就走向反面:立论高妙实则毫无个人见解,文辞华丽却显思维极度混乱,颠来倒去而总是陈词滥调,貌似中正然终为乡愿和事佬,如此“卮言”,俯拾可见,何贵之有!
再看道士们的“卮言日出”,我猜测,钱先生似用反讽,以本意境界极高之语刻画道士们虚张声势、故作清高的丑态。道士们鼓励信徒不必吸取那虚无缥缈的“日月精华”,而是补充点山珍鸟兽,看似惊世骇俗、与时俱进,实则“口馋”而已,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偏要说的冠冕堂皇,哪有什么新意可言?道士们在美味面前意志薄弱,不再执着修道,心甘情愿地“缺乏主见”,大快朵颐,足见比凡夫俗子稍微不凡不俗的人,同样难敌人间烟火,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再次胜利!
得了以上感想,突然对“卮”这种酒器发生兴趣。网上搜了一堆照片,看得津津有味。不料问题接踵而至,从西周到汉代所用的盛酒“卮”,均为上下一般粗的圆筒状,偶有例外,也呈圆肚茶壶状,怎么可能“满则倾、空则仰”呢?倾仰合用,即低头抬头的意思。无论酒满与否,卮本身并不会倾和仰。又查,发现古代还有一种大名鼎鼎的“欹”,这玩意大概在原始社会就已被发明出来,上宽下窄,未装水时略向前倾,灌入少量水后,欹身就竖起一些,水装到一半时,欹身会自动的立起来,而一旦灌满水,欹身就会一下子倾覆过来,把水倒净,尔后又自动复原,等待再次灌水,完全符合“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据说孔夫子对此大发议论,《荀子·宥坐》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宥坐之器即为“欹”,宥即右,“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圣人之言当然振聋发聩,后代君王们多在宫中立一“欹”,表示自己谨守这种“不多不少、正好半瓶”的中庸之道。然而“卮”为酒器,“欹”为汲水之器,两字似不通假,压根不是一回事儿。若说“卮”就是“欹”,为何不说直接说“欹言”?看来,若“卮”果为酒器,古人“满则倾、空则仰、中则正”之注恐为以儒学附会道学之词。“空满任物,俯仰由人”,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中认为:卮满则酒溢,卮言比喻自然流露的“无心”之言,我想,这应当是对“卮”与“卮言”关系的合理解释吧。
由“卮言”想到:高境界的“卮言”非我能及,无知带来的“无主见”也非我所愿,那么“中庸”一点,待人接物也罢,钻研学问也罢,保持开放的思维和宽容的心态,不先入为主、不固执己见,苟日新,日日新,不是很有意义吗?这当然很抽象,很老套,也非《庄子》之所谓“卮言日出”,但对我而言,已是很高的要求了。
最后,为一“卮”字折腾自己好几天,似乎不值。遂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语聊以解脱:“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