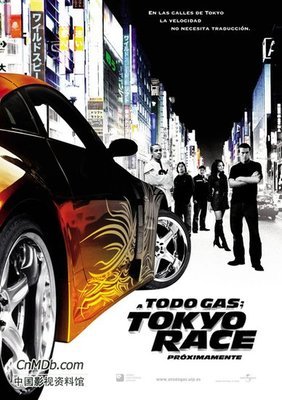四季在草木上枯荣,山居茅屋纸窗前月上山岗,清辉盛满手握的茶盏,我怀念古人曾经把盏的风雅,在中国人来说只要有一个可以安放茶盏的地方,尘俗的喧嚣似乎就与内心有了一段美妙的距离,喝茶可以使人神安,神安则心安,心安之处即是故乡,但是去哪里寻找一盏使人安心的的茶呢?
晨昏雪漫窗帷,一山清幽如许,多少个白天在城市里辗转后,夜赴南山,一路寒暑更替,只为了不辜负与寂静山月的茶盏之约。红色的炉火上丝丝缕缕升腾起来的茶烟抚过疲惫的肩膀,铁炉上咕噜咕噜的水声不由的使人表情放松,深思飘渺。
几年以前我面对层峦叠嶂的终南山发了一个愿,一直到山的尽头去,去寻访那些茅屋洞穴中精神高洁的隐者,之后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幽深的洞府之中,看着可以洗尽所有尘埃的山泉,洞府的主人是一位隐僧,他请我喝他冲泡的绿芽,梦境中那是我喝过最美的茶,梦醒之后很长时间我感觉被那样的茶清洗的身心透亮,但是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梦中的那个洞府,我喝到过隐者们递过来的各种茶,但是没有梦中的那一味。
终南山曾经是个风雅的地方,古代的时候,陆羽就常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于长安与终南山之间的山道上。
人们常常怀念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几次雅集,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七位酬唱往来于竹林中,稍后嵇康陨灭,广陵散绝响,在他们之后王羲之身处深如瀚海的政治纷争中在会稽山阴一隅,永和年间羽士巨公一场清韵,曲水流觞;为了使后人对于他们的聚会远隔时空而能窥望,他还专门写了一个《兰亭集序》来记载这次相聚,北宋布满狼烟的天空下东坡居士在被流放的间歇邀请当时在西园秉烛夜游,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而能群贤毕至,雅集于一席,生命如云过千山,瞬间消散,君子俯仰天地,一期一 会,临流论茗,抚琴松竹间,文人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生命中的诗意绽放。
让他们与这个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是杯子里的酒,但茶却可以使人醒悟,君子都是情愿在苦涩的茶汤中品味生命的况味的。
十多年前,长安城的马守仁先生就在终南山中结庐煮茶,我们隔着数十座山谷和河流但经常互访,茶事是寻常事,最是寻常事煮得深义酬。先生的茅棚由一处山民的旧居改建而成,趟过一条河,在一片竹林中隐藏着他的茶室和一尘不染的茶席,泥土的墙壁有稻生长的痕迹,先生茶壶里煎煮的古意涤荡着世间人起伏的心。

小时候学画我记住了任伯年的一副画,雨打梨花深闭门,我住的终南草堂山门前就有一条小河,门前没有梨花却有杏花,下雨的时候我闭上柴门一边听雨一边听茶,我们商量像古人那样风雅的聚会,甚至尽可能地将终南山的好山泉一一寻访出来,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事,可是我们觉得无比激动。
我一直想寻觅几位默然深交的知己一起在南山上煮茶,临水跌坐在磐石上,背后是远山淡淡的影子,茶汤中洞箫回荡在幽谷间,有人坐在千层岩石之间的山洞中弹奏着高山与流水的,听琴的除了穿着粗布的山人,还有山间的野鹿,山羊,以及林间的松鼠……
一个人的时候时读几卷石屋山居诗或者寒山子的山居诗,不会觉的孤独。去林深处捡柴,顺便采些松针回来煮茶,松柴煮松针味道清香如寒山子的诗句,如果读倦诗书也晏坐已久又可以去采露水来饮,夜晚的时候兰花的暗香吹打着茅屋的纸窗,时而对月长啸,继而汲泉煮茶。山中的冬季和雨季是寂寥的,煮茶的炉火升起来,照亮了茅屋的一隅,山中无人迹,也少幽禽的时候茶汤味道淡了以至于淡到无味,无味中却似乎能品出岩石的味道来。
经常有人来喝茶的时候我会将第一盏茶轻轻的放到比较高的岩石上去,杯盏对着草堂后面最高的山峰,茶汤里倒影着云影天光,没有人知道我与山神之间的默契。
山赐给了我茶和柴火,又给了我最清澈的山泉,还让王维,李德裕们和我做邻居。处于感恩我尽力的使山泉不受污染。据说天地之间有醍醐甘露,有人说那是一种乳品,我觉得那是一泓使人生不起杂念的山泉,是与几位知己一切煮出来的好茶,终南山北麓有冬季,所以没有茶树,好的山泉以嘉茗为知音,正如深得茶心的韵友互为知音,为了寻找那些藏在大山中的好山泉,我们拄着竹杖,背着行囊历时半年,沿着古人曾经的足迹去寻觅那从桃源深处流泻出来的一捧山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