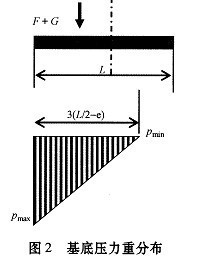也谈“羊羔体”
文/张艳庭
没有哪一届鲁迅文学奖像这一届在网络以及纸媒上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而在这场轩然大波中挺立潮头的莫过于车延高了,甚至他的风头盖过了其他获奖者,以致于让人以为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只有车延高一人。“羔羊体”这一命名也迅速流传,被越来越多的并不关心诗歌甚至并不关心鲁迅文学奖的人所知晓。网民们通过这种命名的方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奖评奖的全民化质疑运动。
与“羔羊体”类似,同样遭遇过被命名的还有赵丽华的“梨花体”。客观而论,赵丽华诗歌的整体水平并不都像是网民们所言“只会按回车键。”但网络就像是一面放大镜,它放大了一个事物的两极:一方面是“随便按回车键”写成的诗歌,另一方面是赵丽华“鲁迅文学奖评委、国家一级女诗人”的名头。此次车延高的情况与赵丽华诗歌事件类似的是,一方面是国家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荣誉,另一方面是“随便按回车键”写成的诗歌。如果说他们的诗遭到恶搞是民众对70年代以来新诗美学的质疑,倒不如说是民众对诗歌纯净性的诉求。有人说这是“诗歌已死”的年代,但诗性却是每个人内心里都追求的一种美好情愫,好诗仍然在代代留传,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定程度上说,诗是每个人在终极意义上都需要的。当有人因为诗歌而获得世俗利益,却又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不负责任时,对他诗人身份的质疑是必须的,而由普通民众完成这一质疑则意义更大。它意味着沉眠于每个人内心中的诗性的觉醒。
然而“羔羊体”的命名不仅仅意在于此,甚至对于更多人来说,他们的矛头所向更在于后者:对鲁迅文学奖评奖的质疑。与《徐帆》等诗作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车————延高的官员身份。官员可不可以写诗几乎是个伪命题,任何人在诗歌面前都是平等的——问题在于,车延高的官员身份在鲁奖的评奖中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更多民众关心的问题。如果只因为获奖者的一些艺术水平不高的诗,那么鲁奖只是一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如果车延高获奖是因为他的官员身份起了作用,那么就是鲁奖的性质问题了:鲁奖到底是全民的文学的奖项,还是挂着鲁迅名头的体制内的行政写作奖?后者与鲁迅的文学精神是截然相悖的。鲁迅的一生是用文学来反抗强权体制倡导自由的孤独的一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行政写作奖岂不成了天大的滑稽和荒谬?真正的文学所倡导的应该是普世价值,而不应该是对权力的献媚。许多民众是从这个出发点来质疑车延高获奖,进而质疑鲁奖评选的。“羔羊体”被命名之后,网上又接二连三爆出了此次评奖中的跑奖买奖行为。具体事件的真实性姑且不论,这种类似官场跑官买官的现象,在当今的文坛中的确是存在的。多年以来,一些国家级文学奖几乎可以说是体制内作家的行政奖,获奖者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单纯文学的荣誉。有利益便有追逐利益者,在这种逐利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本来含义被抛在一边,文学成为了二、三流作家的逐利工具,文学评奖也就成了一场与真正文学无关的名利之争。此次对鲁奖评选的巨大争议,可以说是民众对文学纯粹性的诉求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也可以这样说:这是民众的廉政诉求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投射,而车延高只是一只撞在枪口上的“羔羊”。
任何文学奖的评选都免不了引起争议,因为文学的高下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数字标准。但此次鲁奖的争议与此无关,甚至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现象。在它的重重声浪之下,折射出的是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对精神家园纯粹性的诉求。但这一非纯粹的文学现象必定会因为对今后文学奖项的评选产生影响,而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