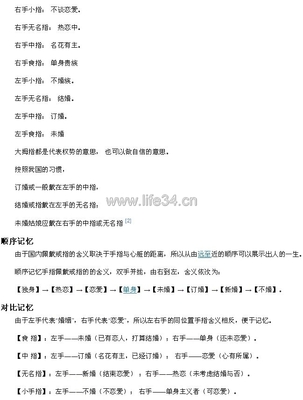昆丁-塔伦迪诺的新片《无良杂牌军》中有一个段落:一个盖世太保军官与一干冒充德国人的家伙玩猜人纸牌游戏,盖世太保提到的都是电影人物。昆丁故意把大量电影史的内容放到了他的新作当中,譬如金刚,譬如傅满洲博士(DR.FuManchu)。
傅满洲博士是在欧美广为流传的一个东方、确切地说是中国人形象。他出自一个英国通俗小说家笔下,后来被好莱坞拍成了旷日持久的系列电影。但遗憾的是傅博士既不是007,也不是黄飞鸿,他是一个集神秘、团伙、残酷、阴谋于一身的邪派首脑,所有的犯罪行径都出自傅博士的策划。自然地,小说和电影的正派人物都是以摧毁傅满洲的阴谋为终极目标。
只所以会产生傅满洲这个东方形象,分析家说,这是所谓“黄祸”在西方文学艺术界的反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欧洲逐渐接触,显然双方也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清政府的无能让中国人饱受欺凌,最后才有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虽然我们的正史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在西方人眼里 ,拳民的行为无不是粗鲁、野蛮和暴力的。这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欧洲和美洲文艺界。
另外,也有很多中国人和东亚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欧洲和美洲,但是他们大多都没有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底层摸爬滚打。所以,在白人眼里,黄种人在欧洲,就像黑人在美国一样,从事贩毒、盗窃、组织团伙与上流社会为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里把黄种人和鸦片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面色蜡黄拖着辫子的瘾君子们都藏在伦敦鸦片馆的烟雾缭绕之中。还是值得庆幸,作家没有把福尔摩斯的最大对头,邪恶莫里阿斯教授打扮成黄种人,表明作家也不是一味的给东方和中国抹黑。
如果说“黄祸”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代表,则傅满洲博士很好地满足了欧美人的心理期待。以至于他的系列电影一拍再拍,直到1980年还有一个《傅满洲的阴谋》出炉,虽然票房已经不可能成功了。
其实,最先我把傅满洲博士和满大人搞混了,因为我也隐约记得后者也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关于这个满大人(Mandarin)的说法很多,有人说这本是一个拉丁词汇,是葡萄牙殖民者首先使用的,用来表示东方(印度以及中国)的官僚。后来以讹传讹,可能也是因为满清的关系,仿佛“满大人”成了一个身穿官服养尊处优并笃信东方哲学(儒或佛)的人物。
如果说穷苦的中国人在西方社会只能混迹于最阴暗的角落,最后听命于他们的首领傅满洲博士,则“满大人”的境遇似乎要好一些,他们会小有资产,会开个古董店,甚至抱着用东方智慧把西方解救出物质泥淖的想法。但是他们脆弱且自卑,也难以和鸦片脱离干系。西方早期的文艺作品里不少角色也能让人看到“满大人”的影子。连老舍的《二马》也是如此。
和傅满洲博士相比,“满大人”的性格和形象都比较模糊,也很难说是个具体的个人。也许,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的《神奇的满大人》是个例外。这幕惊世骇俗的舞剧我没有看过,只是听说其故事情节比较劲爆。满大人被强盗设计劫财,不管对方如何折磨他,满大人始终在追寻诱骗他的姑娘。最后姑娘被感动,拥抱了满大人,满大人这才安心死去。与以往的满大人相比,这个神奇的满大人虽然也没有脱离色欲,但是更代表了一种原始的追求和力量。让人不能忽视。
不论是傅满洲,还是满大人,抑或是神奇的满大人,这都是别人眼里的黄种人形象,说实话,都不讨人喜欢,令人忍不住要反驳。反应过激了,就有了《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等等。或许,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仍然是需要的。有赞为证:
踏遍青山人未老,多情反被无情恼
六亿神州尽舜尧,万里长城永不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