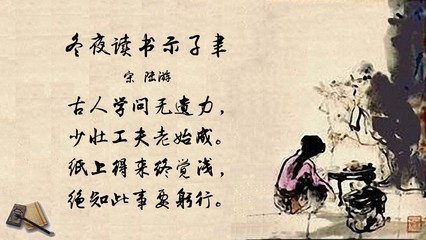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所知道的我舅舅郑揆一博士
林正德
在我写了《被历史遗忘的女画家——追忆我的舅母唐蕴玉》一文之后,我就想再写一篇关于我舅舅郑揆一的文章。我的大舅舅郑揆一,又名启圣,字体仁,1905年4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仙夹乡夹漈村,其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郑玉书,字崇瑞,是著名菲律宾侨领。当我在网上查资料时,颇有些意外收获,发现一是:我外祖父郑玉书是宋朝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世称夹漈先生)的后裔,据郑达夫新浪博客《五绝怀夹漈先生》一文道:“郑樵后裔在福建泉州名山-天柱山下开辟一村庄,名曰夹漈,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学者、工商巨擘辈出;其中郑少坚,成立菲律宾首都银行。居菲律宾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位,国内外银行机构超过四百六十 多家,在国际华商五百大企业之中,排名第二十七名,菲律宾华商之中排名第一名,成为菲律宾金融界的龙头;郑仓满为东南亚面粉大王……;郑玉书为著名侨领,蜚声海内外”;其二是:我外祖父郑玉书的郑氏家族与郑成功家族同一支。《东南早报》2009.4.1《郑成功远祖叫郑昭》(记者朱彩云)一文道:“一部来自漳浦六鳌营里郑振仕收藏的古谱《漳浦营里郑氏族谱》揭秘,漳、泉两地郑氏是亲兄弟。这是一本极其珍贵的史料,翔实记载了漳州古县、漳浦旧镇港、漳浦埔尾等地郑氏与南安石井郑氏系同祖兄弟,且溯源追远,为破解郑成功高祖及远祖之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专家们介绍,从《郑氏宗族史》及郑樵后裔郑玉书的《郑氏迁居各地诸始祖表》中新发现的记载,和营里郑谱的有关渊源出处记载相吻合。/由此,郑成功的高祖、远祖之谜得以破译。”
本人不是族谱研究专家,对这一些都只是看看听听而已。
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中曰:“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也说:“一株树在最初的几年中就从自己的树干中发出了它以后要有的一切主要的枝芽,而以后他们仅仅是繁茂起来而已。同样,我们想赋予一个人一生所有的那些东西,也应当在这个最初的学校(母育学校)中赋予他们。”
据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介绍:“少时曾往菲律宾宿务,协助其父经营振东商行,后回国。17岁以博士员子弟入永春州学,嗣转厦门读中学,后在北京攻读医科。/辛亥革命后,随福建北伐军驻上海、烟台,任军医长。民国3年(1914年)起,先后任驻宜昌陆军十三团医务所主任,驻厦门第十混成旅军医官,福建陆军第一师正军医官和闽浙援粤军卫生部长。民国7年,再赴菲律宾经商。”我外祖父郑玉书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又是学医的,又在海外经商过,他自然深知少儿教育的重要性,很早就把我大舅舅郑揆一送到厦门名校桃源小学就读,当我舅舅小学一毕业,即让他东渡日本读中学、大学,这比现在中国土豪纷纷送子女到海外就读中学要早多了。
昭和四年(1929年),我舅舅郑揆一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结识了我后来的舅母、油画家唐蕴玉。我舅母唐蕴玉在1987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怀念柳亚子先生》一文中道:“先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尤其喜爱接近青年,在东京井之头公园乐天庐整日读书写作。偶游市区,常与留日学生多人如李、殷、甘、袁诸君聚谈。我与夫君郑揆一即在此相识。”“先生平时口吃,但兴头所至演讲时,却气势磅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人感佩之至。”
我舅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回国到上海。1930年,我舅舅、舅母同赴法国巴黎留学,我舅舅郑揆一在他撰写的《留法女画家唐蕴玉》一文中道,他们“途径香港、西贡、新加坡、哥伦布、苏伊士运河,并经过开罗,乘骆驼观览金字塔,再由波特塞港横渡地中海,在马赛港登陆。”我舅舅入巴黎大学历史系留学,专攻太平洋近代史,而我舅母唐蕴玉“到巴黎后她每日往罗浮宫(MusieLouvre)临画,午即以面包充饥,晚间去画苑(Atetier)学速写,旋即考入国立巴黎美术学院,在莱勃及沙巴物教授的画室学正统油画,又去洛特等新派画家处进修,以增进艺术境界。/1930年,我们在巴黎结婚,由何香凝夫人证婚”。(见郑揆一同文)
我舅舅、舅母在法国留学期间,认识了一些中国留法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社会名流,其中有画家常玉。据百度百科“常玉”条目简介:“常玉,本名常有书,1900年10月14日生于四川顺庆(南充市)的富商庭,1910年即与赵熙习画,长于书法的他,1917年入上海美术学校就读,1919年常玉与徐悲鸿、林凤眠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并于1919年赴日时在东京展出其书法作品,而获当地杂志刊载推荐。常玉自20岁(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到巴黎,1921年与徐悲鸿、张道藩等留法学生组织‘天狗会’。至67岁辞世,大致都住在巴黎。此后,他的作品经常在沙龙及各大画廊展出。1938年他曾短期回中国,接着转往纽约,在该地生活了两年。并于1948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作品。该馆同时印行‘瓶花’的彩色明信片。1948年返回法国,直至1966年逝世于巴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常玉40几幅油画巨作,曾于1978起定期举办他的回顾展及学术研究,藉此宣扬他有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成就。”
还有画家张弦,据署名Mezzanine网文《在或曾在法国》介绍:“张弦(1897?1893?—1936):1924年自费到法国留学,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西画。学习之余,以出卖油画、素描维持生活。在巴黎学习时间与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有交往。由于他刻苦学习,学业大进,曾参加世界油画素描比赛获奖,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经当时驻法大使顾维钧敦促,受刘海粟聘请,1929年回国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前身)任油画教授,艺苑研究所指导。1929年,由刘海粟资助,再度赴法进修西洋画,就学罗辛门下。1931年学成归国后,曾受蔡元培之聘先后任教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和中央大学(南京)艺术系教授。1936年在暑假时间返回家乡,儿子出事,精神受惊,肝病复发,在温州白累德医院治疗无效,不治身亡,时年39岁。”
在《中国油画研究系列·唐蕴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中刊有一张我舅舅、舅母与常玉、张弦的合影,足见他们之间有深厚的友谊。此外,该书中还有两张我舅舅、舅母与张弦的合影,这两张照片都是1930年他们一起到野外郊游时拍的,显然他们之间走得很近,可惜张弦1931年就回国了,1936年英年早逝。
我在网上搜索时,意外发现北京华夏珍藏国际拍卖一份焦菊隐文革交待材料《关于郑揆一》,参考价是2000.00-5000.00。据360百科介绍:“焦菊隐(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原名焦承志,笔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后自改为菊隐。生于天津,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北平中华戏剧曲艺学校校长,1937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广西教育研究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重庆社会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总导演。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5年2月28日,焦菊隐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焦菊隐的祖父焦佑瀛,是清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咸丰皇帝的托孤重臣、中国近代史上祺祥政变中被罢官的赞襄八大臣之一。”
我特意将网上焦菊隐文革交待材料影印件放大查看,他交待说:“3.我在法国时(1935-1938)没有认识郑揆一这个人。或者,如果我见过,那一定是偶然遇到,随即忘记了。”
当时,我舅舅郑揆一在巴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而焦菊隐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我以为他们认识的概率极大,只是并无深交。人是健忘的动物,贵人多健忘,我认识多年前的某人,后来又见到他的面,向他提起并提醒某些细节,但其人还是说从不认识我,一点都不记得,这是常有的事,我经历过多次。此外,我还有点好奇,为什么要焦菊隐交待同我舅舅郑揆一的关系呢?而不是其他张三李四呢?那交待材料上戳的是“北京话剧团革命委员会”的公章。
在法国时,每年暑假我舅舅、舅母都要到比利时、荷兰、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处的美术馆观摩各派的杰作,当然,也游览各国的名胜古迹,我舅母也到处写生。有一次,我舅舅到比利时布鲁日近郊的圣安德鲁修道院拜访大名鼎鼎的陆征祥修士。
这个陆征祥是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曾任过内阁总理,其夫人是当时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取消中国“交战区”相要挟,抛出蓄谋已久的“二十一条”要求,陆征祥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同日方的艰难谈判。起初,中方采取“拖延战术”,在谈判时间上拖,在条款上逐条慢慢磨,这样,一拖就是数月,最后,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五七通牒”,不签约即开战,迫不得已,陆征祥代表袁世凯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签字后,举国哗然,国人皆骂他为卖国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战胜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国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对德和约”。1933年,陆征祥夫人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给陆征祥留下遗嘱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作教士一心修行。
这座圣安德鲁修道院始建于1902年,它并不是一座单一建筑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筑风格各异的教堂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兰语称之为“Zevenkerken(7座教堂)”,它属于天主教本笃会。这里绿树葱茏,环境优静,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我舅舅郑揆一拜访陆征祥时,他刚出家没多久,全身穿黑色道服,头上有两条受戒线,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鬓发略显斑白。
他们交谈的内容就是关于“二十一条约”谈判的真实内幕,事后,我舅舅郑揆一为此专访撰写一文刊于某报,我以前曾有该文复印件,可如今却找不到了,只好凭记忆及网上资料说个大概。现在360百科“陆征祥”条目至今还在说什么:“在日本的胁迫下,也因袁世凯急着当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条’,由陆征祥执行签字。”“互动百科”也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总之,就是说袁世凯为了龙袍加身而不得不同意签约。
而陆征祥则如是说:日驻华公使置益民四年一月十八日晋见袁世凯总统,突然将一文书放在袁氏桌上,日使匆匆告辞后,袁氏翻开文书一看,乃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要求,为之大惊失色。袁氏即打电话召我入公府,说有要事面谈。我入府后,刚一坐下,愁眉深锁的袁氏随手取出那份文书,教我先读一遍,他一面说道:“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外交总长)、曹汝霖(外交次长)、梁士诒(交通总长)举行一次密议,商讨对策吧!”我告辞回寓所后,马上打电话给孙、曹、梁三位,请他们晚饭后赶来迎宾馆有要事面谈。开会时,大家议论良久,都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刻接受;另一是开会与日方举行谈判作讨价还价,至于拒绝接受那条路却是走不通的。陆、梁主张谈判,两个主张不谈判。次日,孙宝琦进总统府向袁氏报告昨日会议结果。袁氏聆罢却向孙道:“很好,让我再考虑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孙氏辞出不久,袁氏即召我入府面议,袁氏对我道:“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一谈判才行。”我答道:“这件事太为难,我的精力又不足,总统最好另行选择适当人选。”袁氏道:“精力不足,无关重要,你尽可在会议席上睡觉,我可以告诉曹次长,如在开会时遇你睡觉,须告知日使不必见怪,因陆先生精力素弱,不休息不行,其余由我本人帮你的忙,你放心去谈判好了。”我见袁氏如此推诚相托,只得应允。孙宝琦是日再往见袁氏请示时,袁即表示自己亦主张与日方谈判。当夜孙宝琦即上辞呈,并向袁氏推我继任外交总长。当时袁氏接到日使这份要求文书后,曾苦心研究,逐条亲批讨论的办法,他曾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租借土地,日后还可以想方设法讨回,而文化教育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日本手里,如果让日本对我国人进行奴化教育,那整个中国就无药可救了!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
二月二日下午三时,在外交部开第一次谈判会议,按日本当时给日置益的训令。重在从速讨论,每日开会,逐号(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商议;我则主张逐条讨论,一星期只开会两次。中方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首次会议双方即争持不下。这样,双方虽不断会谈,仍无结果。不料到了五月七日,日置益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声称:“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翌日,袁世凯总统召集会议,他沉痛地说:“今日只有忍受奇耻,接受日本要求,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事已至此,外交部乃连夜准备覆文,并由我面报袁氏,乃定议。该项覆文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对于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如“军器一律限用日本制造,警察中日各半,顾问遍设全国,并要扶助日本佛教传信”等内容,覆文提出“日后另行协商”。当覆文送交日本公使时已是五月九日午后一点了。我在参议院报告后之次日,又往见袁总统,袁氏说道:“陆先生你累了。可是这事结果很好。”我答道:“精神倒还支持得了,不过我签字既是签了我的死案。”袁氏道:“不会的。”我又说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此时也只有报以苦笑,并问我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我答道:“只有参战,到和会上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袁氏说“这句话如今还不可说啊!”
圣茨伯里说:“历史家可以说谎,但是历史不行。”我舅舅拜访陆征祥的文章及家人转述此事,还有网上资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袁世凯和陆征祥有了新的认识,说他们是“卖国贼”显然是不实之辞,他们实际上也是悲剧中的人物,正如陆征祥所感慨“回顾前朝旧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他还在为当年的“二十一条”深深负疚。
1937年,我舅舅郑揆一撰写的以揭露当时日本侵华野心为主旨的博士论文在巴黎出版,为他作序的是顾维钧博士,当时顾是中国驻法大使,他因近年拍摄的影片《我的1919》而闻名,事实上作为当年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对拒签巴黎和约所起的作用不下于顾维钧,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愤怒。在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再说我舅舅郑揆一荣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是福建省永春县第一位学者获此殊荣。说来真巧,1939年,他一回到菲律宾马尼拉时,应邀演讲时事,在结束他的演讲时胸有成竹地告诉他的听众们,姑息主义绝对行不通,欧战非爆发不可,说不定明早你打开收音机时,听到的是欧战爆发的消息,这几句话使他成了成功的预言家,因为第二天早上,收音机真的传来了欧战爆发的消息。
1938年底,我舅舅、舅母一家人先回到香港,1940年才回到上海。1987年12月10日香港《文汇报》刊出一文《记郑揆一·当年是:国民参政员候补立法委员现在是:近代史研究者侨务活动家》,作者吴德铎时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笔名沈舒,该文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目前住在上海的郑揆一博士。郑博士现在七十四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郑博士只才三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的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委”),同时他还是立法院候补立法委员。那时与他一道工作的,有黄炎培、许德珩等,和这些老前辈比起来,他当然是小弟弟,不过,岁月无情,当年的小弟弟,现也已年逾古稀矣。”
在《华侨志》里记载:“民国29年(1940年)/永春华侨郑玉书、尤扬祖等发起集资在福建创办华侨兴业公司,由郑玉书任董事长,郑揆一任总经理。”郑玉书是我外祖父,而尤扬祖百度百科其词条介绍:“尤扬祖(1892—1982),名逢春,字扬祖,永春县达埔镇延清人。著名爱国侨领,曾任印尼望加锡中华总商会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泉州文史资料全文库“郑揆一”词条中说:“抗日战争期间,其父邀胡文虎、许志笙等海外巨商,在南平创办华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郑揆一任总经理。该公司先在当地王台山垦植大型林场,栽种40万株杉木;又经营闽浙赣汽车运输,搞省际贸易。抗战胜利后,总公司移设福州,并在上海、厦门、香港、台湾设分公司,成为集农、商、外贸为一体的大型企业。/商事之余,郑揆一奔走于闽、沪、宁间,与柳亚子、邵力子、何香凝、江庸、陈仪等政要名家结为忘年交,颇得教益。”在我以前福州仓山老家“清庐”曾保存着两张乒乓球桌和一张康乐球台都是以前这家兴业公司关闭后留存下来的东西,如今老房子拆迁都被毁了。
在该词条中还介绍说:“民国期间,郑揆一曾任厦门大学教授、青年军少将教官、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我以前未曾听说我舅舅是青年军少将教官一事,这几天在网上搜索时发现一文《黄维莲荷练兵纪事·——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七十周年》,作者为守望黄埔,该文道:“抗日战争进行到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很多。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知识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干部训练团“团部机关就设在江西省横峰县莲荷村。蒋介石指定由副总监黄维中将坐镇莲荷,主持训练。/黄维还让程兆熊通过关系或私交,先后邀请了宦乡(新闻学)、孙冶方(经济学)、王冶秋(文学)、孙晓村(法学)、郑揆一(世界史)、杨惟义(昆虫学)、陈鹤琴(心理学)、程懋筠(音乐)等一批名流学者来莲荷讲演。每次听学者演讲,学员们都生怕迟到,总是抢先坐到前边听。凡听过他们演讲的人,至今记忆犹新,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听讲时的生动情景。/黄维为鼓舞士气丰富康乐,还亲自审定了一首歌曲,歌词是‘山青青,水洋洋,莲荷山水长。中华儿女来四方,操戈执戟聚一堂。聚一堂,练刀枪,远征三岛来还乡。来还乡,永不忘,莲荷山水青,莲荷山水长。’凡是参加过莲荷训练的人个个都会唱。连当地小学校也都教唱这首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莲荷的干训团东南分团和青年军东南分监部奉令结束,完成了它的神圣历史使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我以为我舅舅郑揆一为知识青年远征军的知青们演讲世界史,也是对抗日战争的一份贡献,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我舅舅郑揆一有个共产党的老朋友梁灵光,这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梁灵光也是福建永春人,与我舅舅是同乡,他1916年生于一个儒商之家,由于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经济一蹶不振,就在这时,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哥哥梁披云把他带到上海名校立达学园继续升学。他在求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因身份暴露被学校开除,他不得不回到厦门。后来,为了争取升上大学,梁灵光又回到上海,寄宿在暨南大学校外学生宿舍,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上海青年学生热烈响应,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他也投入于这股洪流之中,并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入了抗日青年团。1936年,他经组织认可,到马来亚找哥哥梁披云,他进入尊孔中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南洋回国,被党派往苏北组织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1940年,抗战支队被编入新四军,同年入党,历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第一任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参谋长等职。解放后,梁灵光任厦门第一任市长,后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梁灵光被打成“走资派”、“叶飞死党”而被赶出了省委大院。1967年6月,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打范(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倒魏(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浪潮,指控他们是大叛徒,我当时是福建师院附中“×××”红卫兵,我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人云亦云,对范、魏二人是保还是打?关键是弄清他们到底是不是叛徒。我们决定先搞魏的外调,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同组织的同学要搬到省委去住。当时位于乌山路的省委大院里头至少有大小楼房好几十幢,可是,几乎都被五花八门的红卫兵组织所占满,要找个住的地方可真不容易,我们查看了好多楼房,也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最后,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到了10号楼。10号楼的原主人恰巧就是梁灵光,现在被福州大学我们同派红卫兵的人占据,他们也是在外头搞外调,因人手不够,从我们学校同组织借调了两位同学去帮忙。我们找到那两位女同学,跟她俩说清情况,她们就找这里福大负责人商量。而福大的老师很热情,一口就答应了。我们进去与那福大老师握手致谢,他寒暄几句就走掉了,留下我校两位女同学来招呼我们。我在新写实长篇小说《非常十年》(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里写道:“这当儿,我开始打量起这房间来,这楼房楼上三室一厅,楼下二室一厨房一卫生间,地板都是拼花打蜡的地板,不过,这时日这地板千人踩万人踏,原来打蜡的地板已失去往日的光泽,也用不着担心走路会滑倒了。这房间的家具陈设并不豪华,但也不寒酸,该有的也都有,全身镜衣柜、书桌、书橱、轿车椅、转椅……房子的主人×××现在也不知被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他家的家具陈设也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我的眼睛一瞧就往书橱上瞧,按理说一个堂堂的省委书记应该要有可观的藏书,可是,在那玻璃书橱上只摆着毛选和几本毛主席的小册子,大部头的书就只有一本,我是爱看书的,把它抽出来一看,乃是一本精装的16开本的《世界地理》。我心里想,大概×××把书都转移走了,不然,一个省委书记怎么会只有这几本书呀?”
我们在外调搞清魏金水连被捕也没被捕过何来‘叛徒’之说后,没几天,社会上又发生了一起文革事件,即离开了10号楼,不过,我对谁也没说起我舅舅认识梁灵光一事,我对他充满恻隐之心。
梁灵光于1973年冬被解放出来,1975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冬,他依依惜别工作了整整二十八年的故乡福建,奉调中央任新组建的轻工业部部长。1979年4月,中央支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省委提出的建议,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1980年,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北京工作,由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以后又任省长。临行前,任仲夷和梁灵光驱车来邓小平住处,邓小平叮嘱他俩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任、梁果然不辱使命,开创了广东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被称为“任梁时代”载入史册。2006年2月25日7时50分,梁灵光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在沈舒的《记郑揆一》一文道:“抗战胜利后,郑博士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一次,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去台湾检查工作,无意中遇到他的老同学、当时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先生(也是福建人),他乡遇故知,要谈的自然相当多——从刘先生的工作谈到日月潭,从日月潭谈到故乡的溪流也很多,水利资源丰富,也可以用来发电。郑博士要求老同学刘先生以电力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大力支持故乡的水利建设。刘先生满口答应。/在郑揆一的奔走努力下,成立了包括台湾、福建地方当局,和郑揆一经营的华侨兴业公司在内的古田溪水电站筹备处(郑揆一是副主任),准备将一台搁置在台东的一万瓩的发电机,运到距离福州市约一百公里的古田溪,在那里造一座水力发电站。可是在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年头,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只不过修了一条通向工地的公路,和搞一台两百瓩的发电机供工地自用。/古田溪水电站的筹备委员中,有陈绍宽、丁超五等老前辈,福建解放后,他们建议人民政府,古田溪水电站不但要搞,并且要大大的扩充、发展。人民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古田溪水电站,被列为当时华东四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古田溪水电站于一九五四年开始发电。”
古田溪水电站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梯级水电站,应该承认我舅舅郑揆一是古田溪水电站的开发先驱,最近,我在网上查到《古田溪水力发电厂大事记》,它只记载了1949年之后之事,这不能不是件遗憾之事。
在泉州文史资料全文库“郑揆一”词条中介绍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侨联一、二届委员,上海市侨联一、二届常委,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常委,长宁区民革筹委主任。”在沈舒的《记郑揆一》一文又道:“全国解放后,郑博士在上海负责照料他叔父郑崇璧先生的华昌漂染织布厂,公私合营后,这家厂经过改造,成了出名的耀华玻璃厂分厂。郑博士早已超过了退休的年龄,厂里的事他现在不大过问,他现在一方面忙于侨务活动(他是全国侨联委员、上海侨联常委),但他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收集华侨的资料,打算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对我国华侨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国华侨史,是郑博士学术上的多年夙愿。”
有句俗语说:“外甥像舅舅。”我以前还不太感觉,现在人老了,我自觉得自己在体型上同我舅舅似有几分相似。我舅舅郑揆一很喜欢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才几岁大,那时我们家住在福州市仓山区仓山精舍,我舅舅从上海来福州我们家探望我们,有一天早上,他把我整个人脚底朝天地颠倒过来,就这样紧抱着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几天我为撰写此文,想找到这张照片,遗憾的是却找不到了!1962年,我舅舅又来福州,下榻于省交际处的一幢小洋楼里,这是当时福州最高档的宾馆。在我父母带领下,我们全家人都到位于西湖畔的省交际处他下榻的小洋楼里同他见面,他宴请我们在交际处里吃了一顿。
上世纪三十年初期,郑揆一、唐蕴玉夫妇与长女、长子在法国巴黎
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揆一(后中)、唐蕴玉(后左)夫妇与留法画家常玉(后右)、张弦(前排)在法国合影
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揆一(中)、唐蕴玉(右)夫妇与留法画家张弦(左)在法国合影
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揆一、唐蕴玉夫妇在法国合影
比利时布鲁日近郊的圣安德鲁修道院
郑揆一文革交待材料网上拍卖预展
唐蕴玉文革交待材料网上拍卖预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郑揆一(中)、唐蕴玉(右二)夫妇与家人摄于北京岳陵
1979年我舅舅郑揆一赠予作者词典题字
郑揆一、唐蕴玉夫妇在上海市永嘉路600号旧居
上世纪八十年代郑揆一、唐蕴玉夫妇在美国家中合影
郑揆一捐赠《古今图书集成》入驻福建省永春县档案局
郑揆一捐赠《四部备要》入驻福建省永春县档案局
1991年我舅舅、舅母给我们家寄印有唐蕴玉油画的贺年卡正背面拼图
1989年我舅舅、舅母给我们家寄印有唐蕴玉油画的贺年卡正背面拼图
1993年8月16日,“唐蕴玉遗作展”在美国洛杉矶中国文化中心揭幕,左四为郑揆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