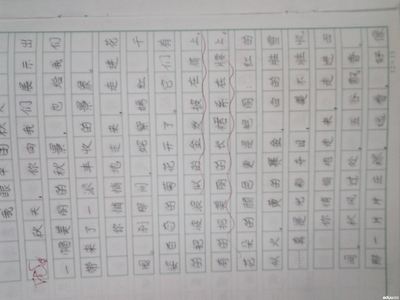少言不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或者说,她主观上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但客观上却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她其实是一个有点害羞、内向的人,不太善于表达,或者总是做相反的表达。她高兴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而悲伤的时候,却往往笑得乐不开支,东倒西歪,她是一个相反的人,所以她认为自己是很难交到朋友的。
有一次,少言却交到了一个朋友。她第一次见到文定中的时候,他一本正经,一眼都不看她。他看她第一眼的时,她就开始脸红,甚至都有些结巴起来。然后她就开始为他两肋插刀,干些挺混蛋的事情。少言认为自己是一个长反骨的人,表面上很温顺,实际上也很温顺。
他说,少言我空了可以来找你玩吗?少言就说可以啊。他就当真来了。四年前,他来找她的时候,还是秋天——北京的秋天非常短,又带着些肃杀的美,这让她误以为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开头。大约是晚上9点多,少言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那条裙子有着强烈的纪念意义,那是天昭从美国给她带回来的裙子。鉴于少言已经比较丰满了,她加了一件淡紫色的开襟。她穿着高跟鞋,慢慢从17层的电梯下来,文定中提着电脑,在茶室的门口已经了小10分钟,她才让他见到她。后来的好几次,他一直在那个茶室的门口等少言。他等待的姿势,很象古代的张生,(少言估计文定中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张生)笑咪咪的,这让她产生了很大的错觉。
少言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太会聊天的人。过去她说过,好人比较容易喜欢我。一名女孩则反驳说,难道我是个坏人吗?!少言不知道搭错哪根筋,把这个话也跟文定中说了。
他和那个女孩的反应不大相同,他笑眯眯地接茬说:我是一个好人。
少言脸又发热了。事实证明,她表面不露声色,镇定自若,到底却是容易乱了阵脚。
那个茶室装修颇为拙劣,放着不搭调的盆景,雪白的墙壁上,装饰极为陈旧僵硬,而灯光则十分惨白,不象是茶室,倒象个大学教室,让人上自习用的。茶水费倒是不贵,整个晚上,就少言他们一桌客人。他们荒凉的茶室枯坐了两个小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那时候少言万分寂寞,他想大概文定中也是吧。不然,两个人为什么要呆在一起那么久呢?
他们聊了很久。文定中简要地介绍了自己。他最需要的是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人,这个女人必须年轻、优雅。他说他最崇尚的女人的品质是优雅和善良。他说,他在印度见过一个党派的领袖,是一个女人,举手投足,那真是非常优雅的。少言不由得有些慌张,又难免以身代入,为了表现得优雅些,她微微挺直了身子,又试图把脖子象仙鹤一样拉得更长些——他和她说这些干什么?
她是一个现实感很差的人,世界格局,国家民主,自己是否活在危险之中,也和她无关。
她每天在家研究怎么褒骨头汤。跟高中时做化学实验一样。
她多少相信公道,人心,正义,相信爱,只是因为如果不相信点什么,就无法面对内心荒芜和孤寂。她因为读的文艺书多了,难免有些浪漫气。她知道张爱玲的小团圆里没有浪漫气,她也看些王小波,也看卡夫卡,但心智并不见长。她得知道文定中并不看文艺电影,也不知道卡夫卡,甚至没看过周星驰,她不免也对他这样孤陋寡闻感到惊诧起来。但她都认为这是他的长处,便对他另眼相看。
到了夜里11点过,他们默默坐了一会儿,文定中说,我要走了。少言慌忙说,你能留下吗?文定中回答总是很快:可以,我可以在你家过夜。
少言一下子就红了脸。她迟疑了一会才辩解说,我是说,你能不能再茶室多留一会儿?
文定中说,他现在暂时居无定所,并不介意在朋友家过夜。
少言有些难为情地说,她也并不介意朋友在自己的家里过夜,只是家里很乱,不便被 参观。
少言始终认为,是自己的错。如果她不穿那条红裙子,如果那裙子不那么紧绷,或者胸前不要露那么多,也许他不会对她有诸多误解。她刚从上一段惨烈的爱情里,象被甩干机的离心机甩出来一样,她神情恍惚。说些不着边际的笑话,她认为都不应该。如果她一早学会一本正经地说话,也许不会出那么多的问题。她时而说正话,时而说反话。反正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她最想说的话,她却永远都不会说。
那一次,文定中并没有在少言家过夜。她在路边,把文定中送上了出租车。她有些多情,觉得人家想在她家过夜,分明是对自己有好感,而自己又因为矜持,拒绝了他,她多少有点觉得对不起别人的美意,多少有些恋恋不舍起来。
正当年的单身男女,若是彼此有了意,是拦也拦不住。而后几天,少言收拾好了屋子,文定中果然来了,带着不离身的黑色电脑包。他倒是熟稔,过来洗澡,穿上少言为他准备的T恤和睡裤,安静地躺在少言的左边,倒是很乖的。他们说了一会子话,说说笑笑的,就跟上次在茶室里一样。少言刻意地和他隔着些距离。她有点担心他来拥抱她,这样她会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他没有。他只是朝向着她,对她说,睡不着?
少言说,是有点睡不着。
他说,有时候做爱可以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少言不知道他说这样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她老老实实地说,她觉得做爱反而是让两个人的距离更远。
不做爱之前,觉得两个人还是很亲,做爱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两个人的关系了。
文定中没有再接茬。过了一会,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悄无声息地睡着了。少言却心跳不止,过了好半天,才勉强睡着了。
第二天文定中醒来,阳光打在他脸上,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的样子,特别象少言沙发上的一只熊。她忍不住微笑了。他起身和她吃了早餐,坐在桌子前,他把他要很快结婚的话,又说了一遍,然后才离开了少言的家。
少言第一次去文定中家是几天后的夜里。她打车到了他家附近,在立交桥下等他。刚刚下了一场秋雨,有些凉了。他在桥上叫她,拿着伞,露出个圆圆的平头。他们一见对方就笑,止也止不住。太寂寞了啊。文定中之后在监狱里服刑时,难免想起那些秋夜。那样短的时光。而少言却流落到了哪里呢?他可能从来不知道,自从他离开了少言,少言几乎为他死去了。
他带她回到家里。他暂时和两个外地女孩子合租一套房,但他从来没见过那两个女孩。他住其中一间10平米的小房间。房子非常简陋,放着房东胡乱配备的柜子,书柜、桌子和床,蔽旧得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租的房子。一大摞红色的人民币,胡乱地放在桌子上。旁边还开着半个西瓜,又放着一把巨大的牛角梳,简直象一把大弯刀。他们和衣躺在床上,被单甚至有些潮湿的味道。上回,文定中躺在少言的左边,这回,他们换了个方位,轮到少言躺在文定中的左边。孤男寡女,一开始两个人还在闲扯,怎么也睡不着。文定中忍不住就过来滋扰少言,把她轻轻抱在怀里。那是文定中第一次拥抱少言。
两个人定了定神,就升腾起了无穷的欲望,仿佛这些必须有这些热,才能抵挡一个寒凉的,下过雨的秋天。
文定中的手慢慢摸索着,到了乳房,盈盈一握,象一只乖巧的小鸟,在他的手心里,小小地盘踞着,非常感人。他慢慢下滑,到了少言的腰,那个腰是细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光滑。小腹微微隆起,曲线柔润,这说明少言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
少言笑嘻嘻地躲避着,不让他进一步掀起她的裙子。这样推挡了几个回合,文定中不免有些烦躁,说,这怎么睡得着?少言觉得甚是好玩。她问,你知道我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文定中说,红色。少言奇怪道:你怎么知道?刚才我看到的,文定中说。他有些气恼,不知道少言到底跑来来做什么。这样撩拨他,却不让近身。
少言说,和我做爱的人,要么给感情,要么就给钱。
文定中说,那我给钱吧。
少言因为自己说话半真半假的,就不知道他说的书真是假,她因为喜欢他,觉得他不但有趣非凡,而且质地相当憨厚,她不由得咯咯笑起来。
她问,那如果你给钱,一周需要做几次呢?
文定中老老实实地说,一周两次吧。
少言怃然道:这还不错啊。
文定中说,你有过特别爱一个人的时候吗?
少言愣了下,柔声说,有过的。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少言说,他结婚了,有了孩子。
那你不是很难过吗?
少言说,是挺难过的。
她难免想起了些往事,把脸转向了墙壁,背对着文定中,眼泪沁出来了些。
文定中也难免想起了旧人的好来,只觉得自己也不是没被人爱过,对自己好过,就觉得自己有负于那些女人。这样的感觉,一闪就过去了。
他过来从背后静静搂着她。她觉得他挺温柔的。他们就这样弓着身体,找到最舒服的姿势,静静地抱了一会儿。她问他的女友的事,他告诉她,她长得很是美丽。不久前分开了。他有想和她复合的意思,但是她结婚了。
少言听到这些,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才好。
文定中觉得自己该收下心,不能玩耍下去了,毕竟时不待我,他还是应该正正经经找个人结婚。这个人肯定不是少言,他和她第一个晚上聊天就知道。就这么觉得。少言太象一个飘渺的蝴蝶了,只是眼花缭乱,没有重心和落脚点的蝴蝶。
他定了定神,说,其实就算你想和我做爱,我也是不会和你做爱的——我刚才是逗你玩的。
他这么一说,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坐怀不乱的了。这倒激了少言,她又凑过去,搂着他,轻声笑着,拨弄他,亲吻他的耳垂。他们这样耳鬓厮摩了一阵子,彼此对身体的熟悉又进了一步。她往下一探,心里也是明白的。只觉得春心荡漾。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道德的,于是都克制着。或者是欲擒故纵着,试探着,跟跳探戈一样,进进退退。你推我挡。他对她只是诧异,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意思。而她只是喜欢他。
半夜忽然下起了大雨,窗帘动来动去的。文定中觉得耍累了,就睡过去了。这厢少言是一点也没睡着,心里一直在跳。
第二日他们起身一起去吃早餐。少言想,这脸上的粉都是残的,有点难为情。文定中看着她的脸说,你脸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痘呢,是皮肤病吗?你去看看医生吧。少言只是难为情地微笑。他们在地铁口分的手。少言是一直拉着他的手走路的。
过了一个礼拜,文定中说,我到学校的自习室上自习,发现很多女孩子脸上也长包,原来大家脸上都是有包的。少言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不解风情的憨包,就越发爱慕他了。
少言去了一趟天津,出差两天,发现自己突然特别思念起这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她给他发短信,他却不时常回,或者回得冷冰冰的。在外贸市场,想起文定中连个简易衣柜都没有。衣服只是杂乱地堆在一把椅子上,还有些皱巴巴的。她有些难过,就给他买了一件夹克,一件毛衣,和一件长袖T恤。她从天津回来,巴巴儿地从南站跑去找他,他开始还不乐意,因为他找了她三次,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她只是跑过去,他在小区门口外面接她。他们走到路灯下,灯光有些惨淡,寒风吹过来,少言穿了件米色风衣,打了个寒战。
她把衣服取出来,先让他穿上一件T恤,然后又套上了那件黑色外套,他显得气宇轩昂的。少言不知道第一次买衣服就买得这么合身,又惊又喜。
她把他拉到灯光下,连声赞叹说,好帅啊。她忍不住抱着他的腰,他的腰真是匀称有力,抱起来这般适意的。
谢谢你的衣服。文定中非常客气地说。他把她送过了立交桥,他们站在立交桥上,看过往的车灯。秋天到了,我心里觉得有点伤感呢。文定中这么说。这秋天是真的很寒凉呢,少言心里有点空荡荡的。她的故事,不都是只发生在秋天吗?她特别希望能够在秋天谈一场真正的恋爱,哪怕只有几天,哪怕只是朝生暮死。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吧?他那么爱帮助别人,心肠一定是很好的。他不会伤害到她。
很长时间以来,少言是这么幻想着长大的,用幻想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不切实际的女人。
他到桥下为她叫出租。叫停了,少言却死活不肯上车。她抱着文定中,颇是不舍,竟然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肩头耸了几下,默默地流了好一阵子泪。
她不肯坐车,他只好走路送她一程。他们沿着北京的北三环走路,旁边的车呼啸而过。他穿着她买的衣服,却不肯领她回家了。他和她牵着手,在北京的大马路牙子上一直走一直走。这是多么奢侈啊。她一直盼望着和一个人这么相亲相爱,心无芥蒂地拉着手。
最后走累了,他打车送他回家。车到楼下,少言就倚在他怀里,依依不舍地说,跟我回家吧。
文定中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只是摇头。他说,他是要找个人结婚的,少言不是那个人。他一开始只是对少言好奇。但是平白无故地呆了三个晚上之后,没有进一步,他的好奇心也就到此为止了。
少言不知道如何是好,笑嘻嘻咬着他的耳朵:不如你给我钱,我跟你睡觉。
文定中却是改变了主意。他还是摇头。
这下少言是真的有些恼羞成怒了,她小声对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趣呢?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她简直要哭出来,就撇下他下车回家了。文定中非常地不解。他不大清楚这个女人,一会不肯跟他好,一会又要和他好,是个什么意思。他反正是不打算招惹这样的女孩。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思了。
那个晚上之后,少言暗自哭了一场。她就对文定中上了心。
他不是那种特别英俊的男人,只是一个普通人,长相颇为中正,他看起来特别温和,特别礼貌和克制,他还看起来很纯真,他的言行无一例外有一种干净的意味。而且他还是年轻的,壮实的。他拿得住她。她简直有些迷上他了,有点神魂颠倒的架势。
他是身怀国家大义、正义良知的人,她却只爱他的肌肤。
他在她的屋子里躺着时候,她就无声地坐在旁边。她不敢端详他,只是因为害怕自己更爱他。不管怎么样。他们当初在一起一定是一个错误。因为无论她做什么,她的爱都无法传达到他身上。这就好比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任何人的命运一样。
她给文定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009年9月9日的晚上9点钟写的。
她声称她需要他的帮助,他不是很善良,喜欢帮助弱势群体吗?她自己也是“弱势群体”呢。
她说自己识大体,等到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妻子,她就自动退出。
文定中回信说:
我总担心会伤害到别人,既然不会,我们当然可以做好朋友了。谢谢你给我的衣服,我很喜欢,这个秋天会经常穿在身上。
少言就假装嗔怪他象奥巴马的外交辞令。她说:“是不是你不够喜欢我?反正我也不够喜欢你,我们扯平了。”她进一步激他说,他怎么伤害她呢?没准是她伤害了他呢?她说,自己从小都是好孩子,还特别渴望能够伤害别人一次呢!她有点撒娇的意味。
文定中9月10日回了信说:
真的是太忙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在一起玩吧,暂时会开心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怕伤害你,也怕伤害我自己啊。我们还是少联系吧。
少言便是婉言地劝他,她写得跟一篇婉约的散文似的,文法颇为完整,为了逻辑上她也尽量自圆其说,她还谈到了金刚经,谈到了哲学问题:
谁爱谁呢?人是很孤独的动物,比星星和星星之间,更遥远,更孤独。
“我不过是过客罢了。”少言反复强调的。她无非是象引诱他的想法,至于实情是否如此,她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又在说反话,说得含混不清,但总是假装可以自圆其说。她自己写完这些信,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目的,只知道要不顾一切地亲近这个人,好象他是一个救命的稻草。其实她的本意是:找个老实人,结婚生子,爱与不爱,只在生活里相互扶持,搪塞过去就行。她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村姑,在大城市里,她只是一个爱情的上访者,苦行僧,她却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城市里的经济情感独立之大方女性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说服与被说服的,又自己说服自己的关系。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欲望合理化。最后,不管逻辑是否合理,欲望跑在了前头。他们只是食色性也的普通的男女而已。在这个时代,要么不快乐,要么不道德。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不道德,居然又相当快乐。
后来,他们好上了之后,少言有一次给文定中写信,写得象一首诗:
有一次你竟然对我说,你喜欢我吗?!你很竟然很诧异的样子!
我心里想:你这个笨蛋,憨包,傻子哟!
这是无庸置疑的啊!我当然是最喜欢你的。你当然是我最喜欢的人。我当然是非常喜欢你的。
我不管你什么来历,什么去向,是否给我幸福,安定,我只懂得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悲白发。
你这个笨蛋,憨包,傻子.
你去哪里找一个那么喜欢你的人啊。你找不到啊。
你根不不深,你没有鲜艳的花朵,没有好吃的果实,你憨头憨脑,就象一颗花生.。
我喜欢你象花生,象罗汉果的样子,还有你白白的,白兔一样的牙齿,你深陷的眼睛还有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还有你一本正经,若有所思的样子,好象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但是其实只是一个憨包啊。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比我更喜欢你。我会给你褒汤,会给你按摩,会做好听的音乐给你听啊。我要花很多的本钱去讨好你,用洗面奶,精华素,还有香水,还有很贵的粉啊。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你是不是爱我,我都喜欢你啊。
如果你去航空,我就去当飞行员;
如果你是乡下人,我就去支教;
如果你是主编,我就给你写稿;
如果你是志愿者,我就是上访的群众;

如果你是通缉犯,我就陪你把牢底坐穿。
如果你单纯,我也单纯;
如果你天真,我也天真;
如果你猜疑,我也猜疑;
如果你不好,我也不好。
你让我一生一世, 我就一生一世;
你不让我喜欢你,我就掉头就走。
总之我听你的。
你要找别人,我就让你找别人
你要结婚,我就让你结婚。
你要是回头找我,我要考虑考虑,然后也答应你。
我什么都随你,都依你
我们只需象2个小孩子一样过家家就行了。
没人知道你是谁
就算有人窃听,也不会有人知道
我有钱啊,
可以当一个嫖客
我象刘胡兰,象秋瑾一样保护你。
我绝对不会让汪精卫来刺杀你。
总之,我不是杨开慧,也不是董小宛
我只是我,在这个冬天,最爱你的女人。
“你有时好象一个小姑娘,挺可爱的。”有一次,文定中在E-MAIL里这么对少言说。这是他对少言说过的最带感情色彩的话,没有上下文,孤伶伶的一句话,象公文的批示一样。通常少言给他写20封长信,他才会给她回特别短的、类似便签条的信,“也许讲什么道理已经没有意义。我只是请求你的原谅。”或者是:“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放下好吗?”
“我放下了啊。”每次少言无辜地对他说,文定中就好象要宽容一个小孩子似的,脸上显出一副无奈的,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他说,你说话完全不算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只陪你这两个月的?两个月后,我要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人。
少言转过身,张开双臂无声无息地环绕了他,就象黑暗中的海潮涌向岛屿。文定中的皮肤非常光滑,少言的皮肤也如同绸缎一样,在黑暗中幽幽泛着蓝光,这一点也深深取悦过文定中。他默然接受了这个冬天的所有夜晚,她所能够奉献出来的,一名年轻女人的全部欢乐。
世道这样凌乱不堪。
到处都在出事。文定中说。他关心着这个世上的国家大事。他渴望参与其中。
人心都乱了。没法子了。少言心里也觉得乱。她抱着文定中,仿佛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她是非常爱他的。他是一点也不爱她,这点少言心里洞若观火。但是她似乎也不大介意。
“我比这个国家还恨你。”少言咬着文定中的耳朵说。
你恨我做什么呢?文定中不解风情地说。
文定中在少言的蜗居里洗完澡,一丝不挂,气定神闲、昂首阔步、堂而皇之地从少言跟前走过,就跟他穿着西服,结着领带,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路过一样。
有一次,少言看到了一张新闻图片,他在和同事们一起在屋子里开会,煞有介事地讨论着什么大事情,文定中虽然只露了一个后脑勺,但少言知道那个后脑勺是谁。她每次想起那个圆头圆脑的脑袋瓜,煞有介事的、呆头呆脑的脑袋,上面的头发短短的,痒痒地刺着她的手心,少言每次都会暗暗笑起来。
文定中小时候练过武术,三十五过后,他身体依然匀称,结实,毫无赘肉。他这样心无芥蒂,招摇过市,却绝无矜夸之意,不管少言是否介意。少言瞥了他一眼就把头别到了一边去,她想说,你凭什么光着身子在我家里走来走去,但她却别过头抿嘴笑了一下。
其实,当初少言也并非不快乐。他给予的男性的欢乐,和他的社会角色一起,给了她许多浪漫的幻想。
冬天很快来临,有一天晚上,北京忽然天降大雪,兼有电闪雷鸣。少言立刻想起了中学时期背过的古诗《上邪》:“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少言想,自己已经见过北京夏天下了冰雹夹雪,上学时坐火车路过黄河,也看到了那条枯干的河水,而四川汶川也地震过了,为此国家也把5。12定为国殇之日,再加上北京竟然冬天一边下雪,一边打雷,她有一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这一点,也是文定中反复告诉过少言的。“你不要对我有太多幻想。”他说。
文定中就这样赤身裸体地钻进被窝里,仿佛这样自然而然。天气是骤然冷的,过几天又要下雪了。这是他来找少言的原因,过了三十五了还孓然一身,他多少怀着一种伤感去亲近她。少言作为女性之一员,是柔软,轻快又温暖的。她向他仰着脸笑,嘴角出现两个浅浅的梨窝——他不是没有动过心。
文定中在同僚眼里,是一个极其枯燥无趣的人,他从来不去看电影,也不听音乐,更谈不上关心艺术,他虽然经常要谈论国家的前景,民主的意义,等等,枯燥而重大的话题。少言仪态万方地向他走来,简直就象仙女一样。
他长得呆头呆脑。但他第一次跟她说话,她就开始脸红。他们两个好上之后,她给他取过各种外号。出于一种喜欢和宠爱。有时他说,我是不是你的宠物?
是的。她这么看着他,笑吟吟地大声对他说。
他不是每天都来找她的。她在一种被悬空的日子里过了一段时间,恍惚着,象个梦游的人,有一次她把身份证和钱包全丢了,还有一次,她在三环上游荡,差点被车撞死。那尖利的刹车声在她耳边盘桓了好几日。因为她知道他不爱她。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第一次他进入她的身体时,她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她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已经这么大了,还是不能真的面对现实,却象一只鸵鸟一样,回避时光的盘查。
关于他并不爱她的现实,她并不是不知道,可她还是怀着侥幸去试探。一个人总是在试探这个世界的温度,脸上必然是一种惶恐又失落的表情。
少言脸上是这样的一种表情,这样的表情让文定中迷惑不解,他却不知道自己就是原因之一。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文定中并不承认自己是那个人。他认为自己一开始,就已经和少言讲得明明白白。
“有一次,我梦见了警察。”
“要是你坐牢了,我就陪你一起坐牢。”少言对文定中说。
我可以在牢里陪你睡觉。少言说。
文定中苦笑了一声。
年轻的时候,文定中不是没有为过那些受苦的人们流下过眼泪。但是年事渐长大,他知道这些人苦难是无穷尽的,而且其实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也无法解决。而他与那些热血的同仁们的力量如不过是蜉皮撼树,许多个夜晚,他这样毫无顾忌、长驱而入,盘桓在她的领地,幽暗,神秘,深不可测,但是充满了欢乐。仿佛那些所有下等人留给他的焦虑、愁苦,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少言紧紧拥抱他的时候,仿佛要把他永远嵌入身体里去,仿佛他们是乱世里一对苦命的鸳鸯,仿佛她穷尽一生才找到这么一个适当的人儿,把自己放心交付于他。她对他好,则他对这天下苍生好。等于她间接为人类贡献了自己。她又一次为自己的想象所感动。
那天晚上,文定中并没有和过去一样回应少言的拥抱。他隐隐想起,他与少言已经纠缠了一段时间。少言于他而言,象一团不稳定的雾气,太阳出来就会消散。她有些不谙世事的横冲直撞,任性,且对世界心存冒犯和忤逆,并不十分稳定。他不明白她为何眼睛里偶尔会流露出恍惚和迷惘。她不够理性,不接地气,有点游离,不稳定。
实际上他多少对另外一个年轻女子还有印象。她叫清彤,比他小了10岁,他们过去见过面,他见识过她的干练的作风。他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他那时还有一名女友叫程怀玉,所以他没有对清彤多想。清彤看起来持重些,面相安静,有些乏味,他的朋友认为她长得并不美,但是文定中倒觉得没什么,她可能会比较适合做一名妻子和助理,帮助他做更多的公众的发言,他确实需要这么一个助理,就跟他的前女友程怀玉五年里为他做的一切一样,他发号司令,她是他的执行者以及行政秘书。怀玉如春蝉一样,为他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毫无底限地崇拜他。他和怀玉分手后,怀玉很快就和别人结了婚。
文定中觉得他等他忙完这一阵,稍微稳定下来,就要去找清彤,试探她的意愿,是否愿意和他交往。他的父亲早早过世了,哥哥们都已经成家,有些还在国外做生意,同事们都尘埃落定,他今年已经过了35岁,必须锁定目标,在半年内迅速结婚。不管他对社会有多少乌托邦式的理想,他到底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可能娶少言为妻,她一笑一颦,都不让他具有安全感。
文定中认为少言是果敢和坚强的,所以他对她也是坦然的。他数次告诉她,她不是他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且他已经有了别的可以物色的对象,他准备和她去表白。一开始,少言不是没有过独自流泪,但她很快接受了现实。她想,不管怎么样,每天晚上,这个干净俊朗的男人还是来到她家里来洗澡,和她扯些闲话,共话巴山夜语。有一次早上醒来,文定中颇为深情地说,这些现实中的困难我都不怕,我只担心,如果我离开你,你该怎么办?他这么文艺腔,倒让少言有些好笑起来,觉得这个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不过是两个人凑在一起相互温暖,也许是爱情,也许连爱情都不算。于是少言就把头拧过一边,说,我不会死啊。
她觉得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他拥抱她的时候,就象拥抱着天下和苍生一样的。好象他的情怀,就真的有那么大似的。如果身体的交汇久了,又不是草木,怎么会随意弃她不顾呢?他们几乎是一对反义词。他平常不苟言笑,和她一起却时常笑得象个柿子一样,那天真的神态打动了她。他是在进退维谷,非常孤独和一筹莫展的时候,少言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美人救英雄——出于一种少年心气,她不是不迷恋这样的戏剧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有一天晚上,梦见了警察来追捕他,他们化装潜逃,跑过空无一人的菜市场,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开始逃亡,在公路上竟然被警察检查证件,这简直是一定的……他们根本没做错什么,却要这样开始一起亡命天涯了,他们的命运就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和这个经济萧条时代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这多少有点《雌雄大盗》,或者《追捕》,有点公路电影里的意味了,而在当时,居无定所的文定中就安静地躺在她的身边——一个国家敌人。呼吸均匀又安静,象一个大孩子,这让她异常感动。在他心情不错的时候,他们还不失时机地温存一番。革命是爱情的催情剂。他克制又有力,并不孟浪轻薄。因此这些快乐似乎来得分外纯净。她也没有其他秘密了,她只得这么一个人。她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大公无私,勇于牺牲自己,刻板,几乎没有幽默感。她对他产生了许多柔情蜜意,她决定继续他们之间的游戏,不管他给她制订了什么样的规则,也不管这个游戏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