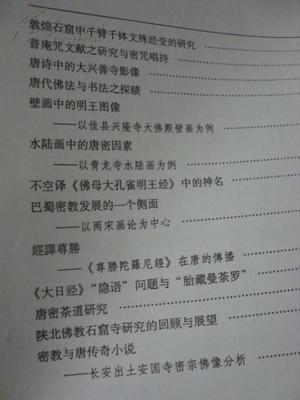老庄,即老子与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都“以虚无为本”,也就是倡导一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这似乎决定了老庄不会有什么文学观或文学主张。但实际上,老庄思想却又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似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视文艺为“雕虫小技”的中国封建社会,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多是仕途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此时的境遇,比较容易接受愤世疾俗、自我解脱的老庄思想。
第二,老庄哲学强调自我,崇尚自然,否定人为的束缚而主张自然天籁。这对束缚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种种框架、模式,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老庄为阐发其虚无主义世界观而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思想观点、讲述的一些寓言故事,如果抛弃其中神秘主义的成分,也确实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某些特征,给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故而他们的学说特别能在艺术和审美活动方面,发挥较大的影响。
第三,老庄虽然口头上否定文艺,但他们自己文章华美。刘勰称老子《道德经》为“五千精妙”。鲁迅先生评论庄子文章曰:“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他们的文学成就,使后人心驰神往、竞相效法。
老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复杂的。可以说,它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孔孟之道一起,共同铸造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以不读老庄;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也不可以不读老庄。老庄思想中关涉文艺问题的一些言论,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文学理论研究重要的思想资料。
老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年辈略早于孔子。《史记》上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任东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即掌管图书的小官,著有《道德经》(即《老子》)。但也有人认为春秋末期那位思想家老子实名老聃,李耳是老聃的后人,生活于战国中后期。《道德经》其实是李耳所作,而托名于老聃。但无论哪一种意见,学术界一般公认《道德经》代表了老子的思想,是研究老子思想的可靠材料。
老子生当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边的。这与孔子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样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图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孔子不同,他是以无可奈何的悲观心情来看待眼前的社会变化,用消极避世的办法来以退为进。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所谓“道”是一种超然于物质世界之外,而又生成和制约着世间万物的绝对精神。他鼓吹天道自然无为,这固然可以引申出反对宗教目的论的积极意义,但老子的本意却是要人完全听任自然的安排,反对社会人事的任何作为。老子提出了一套“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使人民无知、无欲的愚民主义统治术,为此他反对人类的一切文化学术,并以此作为挽救本阶级覆灭的药方。
老子根本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把认识完全看作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他提出所谓“涤除玄览”,就是用神秘主义的直观方法去体验“道”。老子学说中包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思想,这是老子思想的精华。他看到美丑、难易、长短、高下等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是,他把对立面的统一夸大成为绝对,同时忽略了条件在对立面统一中的作用,从而使他的辨证法走向消极。老子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动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他消极的辨证法,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倾向。
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希望回到原始社会的淳朴生活。因此他反对一切文化学术,并反对高谈文化学术的“圣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老子反对文采和音乐,反对言辞辩说。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第十二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第八十一章》)等等。老子的这些言论,对于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利用虚伪的礼乐教化来欺骗和奴役人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造成这种情况,并不是学术文化本身的罪过。老子一概地反对知识和文化,颂扬原始社会的蒙昧状态,乃是违背历史前进方向的反动观点。
老子从根本上反对文学艺术,这一立场决定他不会对文艺发表更多的言论。但他为阐扬其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提出的一些命题,论述的一些观点,如果把它们从其错误体系中剥离出来,却可以从中获得有益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资料。
比如,老子认为自然之道是一个浑然的整体,用语言和概念是不能概括和表现的,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二章》)“莫之名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基于这样的认识,老子在艺术上提倡一种浑然天成的全美境界:“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所谓“大音希声”,与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天籁”是一样的,都是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代替自然的“全美”。白居易《琵琶行》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但是,“无声”与“有声”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得而益彰的。老子以“大音”来反对一切部分的、具体的美,显然是错误的。后世文论家正是扬弃了老子学说中的谬误,而汲取到有益的思想成分。象钟嵘《诗品序》所提倡的“自然”和“真美”;元结《订司乐氏》所说的自然“全声”之美;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主张的“以全美为工”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老子思想对后世文论的积极影响。
老子在阐发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时,提出要“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虚静”说虽有“绝圣弃智”、消极出世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着在认识道的过程中必须排除一切既有观念干扰的正确的一面。这一见解对后代文论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象陆机《文赋》所谓“收视返听,耽思傍讯”;刘勰《文心雕龙》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司空图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二十四诗品》);苏东坡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送参寥师》)等,都是对老子这一思想在创作论领域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第二章》)的观点,对后世文艺创作中虚实相成、巧拙相济的主张,也有直接的启示。他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第二章》)这一具有辩证思想的美丑观,对后世美学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老子主张“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第三十八章》)。这种思想虽然本质上是违反历史发展进程的,但后人将其应用到文学批评上,却成为反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矫揉造作的思想武器。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人。他的生卒年已不可详考,一般认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86年前后。庄子曾作过家乡的漆园吏,但没干多久就归隐了,以后终身不仕,过着贫困的生活。相传楚威王曾派两个使臣带着礼物聘他为相,庄子却坚辞不受,说自己不愿作官,只图精神上自由快乐。
庄子对功名利禄如此超然、淡漠,其根源在于他对社会、对人生的大失望和大悲哀。庄子承袭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但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奴隶制度虽已趋向崩溃,但还没有彻底没落,老子还想以“无为而治”的药方来挽救奴隶主阶级。而到了庄子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崩溃,奴隶主阶级的覆灭已成定局,因而它的思想家庄子也随之完全绝望了。这样,庄子的虚无主义理论就走到比老子更加极端的境地。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的思想,但进一步发展了其中的唯心主义的神秘成分。他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但随即把这一主张引向了宿命论。他认为人世间的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等等都是命定的,要求人们“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指出人们对事物的贵贱、大小、有无、是非的判断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所采用的标准不同。但是,他认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是相对的,没有客观标准而言。因此,人们对事物的美丑、善恶、贤愚、是非进行评判争辩,或者为其中自己认为好的一面进行奋斗,都是无意义的。既然世间的一切都是命定的,一切对立的方面都是相对的,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那么,人生在世最好是无知、无识、无为、无欲,甚至把自己也忘掉。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只有这样,把自己与万物混同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才能达到自在逍遥的极乐境界。庄子文章所反复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这是笼罩在庄子学说上的阴影,是我们在研究庄子思想时必须注意剔除的思想糟粕。
庄子所著《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现存33篇。汉以后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作,外篇和杂篇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作,甚至掺入了其他学派的作品。
庄子同老子一样对文学艺术采取否定态度,并且说得更为具体。《胠箧》篇曰: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老庄提出文艺否定论,有其阶级根源和实际的政治目的。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属阶级的没落,他们往日的享乐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就以“无美”为“至美”、“无乐”为“至乐”的理论来求得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人民有了知识文化,就会犯上作乱,因此提出一套“绝圣弃智”的理论来推行愚民政策。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老庄的文艺否定论,特别是庄子在《去箧》篇中所表达的“绝圣弃知”的思想,又是针对着儒家的礼乐之道提出来的。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思想派别的斗争,庄子对儒家仁义礼教的批判,也确实触及到统治阶级利用虚伪的礼乐教化欺骗、奴役人民的罪恶本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批判的锋芒,有时是相当尖锐的。
为了阐扬其否定一切学术文化的主张,庄子提出了“言不尽意”论。他在《天道》篇中讲了一个轮扁斫轮的故事。车轮匠扁说齐桓公所读之书都是“古人之糟粕”,他解释道: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言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见解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斫轮的方法不能用言语传授,但另一方面又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等等,这实际上还是将斫轮之术口授于人。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正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为了交流经验、传递思想感情而创造出来的。认为人在实践中获得的实践经验不能言传,把一切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都看作是“糟粕”,是很荒唐的。事实上,庄子一方面鼓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另一方面却又洋洋洒洒地以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宣传自己的哲学,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学说的诡辩性质。不过,轮扁斫轮的故事也告诉人们,要掌握事物的规律,必须亲身参加实践,这却是很精辟的。此外,“言不尽意”的观点尽管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宣扬庄子的文化否定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接触到语言艺术审美特征的某些奥秘。对于艺术来说,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从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中,多少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睿智的闪光。中国古代文论历来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加以追求的所谓“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等等,都可以从庄子思想中找到渊源。
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主张保持人的天性、本色,反对人为的强制与束缚。反映在美学观点上,就是追求朴实无华的自然之美。老子说过:“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全书也贯穿着崇尚自然的思想。庄子把声音之美分为“人籁”、“地籁”、“天籁”,认为最上等的是“天籁”,即块然自生、丝毫不受外界影响的自然之声。《天道》篇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联系到老庄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和复古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来看,这种自然天籁的审美理想无疑是包含着反动性在内的。然而,作为美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思想资料,后人用它来强调作品的自然之美,反对雕琢堆砌和矫揉造作,却又产生过一些好的作用。
《庄子》书中有不少谈技艺的寓言,除上面提到的“轮扁斫轮”以外,还有“庖丁解牛”、“佝偻承蜩”、“津人操舟若神”、“吕梁丈夫蹈水”、“梓庆削木为醵”等等。庄子讲这些故事的本意,是为了宣扬其神秘主义的不可言传之“道”和“养生”、“达生”的道理的。从本质上说,庄子要求人们“虚而待物”,忘怀一切,以绝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事物,自然也不必去搞什么文学创作。所以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是教人们怎样进行创作。但是,如果撇开庄子神秘的“道”的学说,把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却可以从中引申出关于如何精通技艺、熟练掌握创作技巧,以至达到“神化”境界的合理见解。
首先,庄子讲的这些寓言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有其“道”,也就是“有数存乎其间”的。人们要想驾驭事物,获得精湛的技艺,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客观事物的“道”,而不能凭主观意志胡为蛮干。正如“吕梁丈夫蹈水”寓言所说:“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其二,要掌握“道”,达到神化的境界,必须有长期的实践功夫。车轮匠扁说他“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承蜩的佝偻老人说他练功达到“累五而不坠”的境地,吕梁丈夫说他“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其三,要获得高超的技艺,还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佝偻承蜩”)、“齐以静心……其巧专而外骨消”(“梓庆削木为鐻”),都是讲必须执着专一、心不旁骛,才能在技艺上达到熟能生巧。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也是适用于文学创作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一段话,对庄子思想和文章风格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
这是庄子后学对庄子思想和文章风格的概括,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关于浪漫主义精神的论述。它对后世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