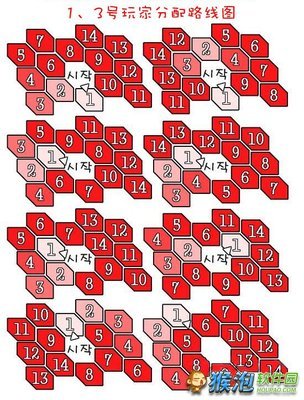崇俭第八
纵观古代帝王,凡创业之君,莫不以俭约而兴;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故古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
夫俭者,去奢从约之谓,丰国富民之本也。考诸今古创业垂统之君,莫不以俭约而兴;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其兴亡成败,载诸简册,昭昭然可为鉴矣。故太宗以俭居戒盈之先,岂无意哉?虽然,俭固近于吝矣。俭不中礼,是为吝也。虽有周公才美,骄吝犹不足观,况其他乎?此所以《蜉蝣》刺其好奢,《蟋蟀》刺不中礼也。然则其何以行之哉?曰语不云乎?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此是明王之威德,至圣之格言。依而行之,吾无间然矣。
【原文】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史记》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富民之要,在于节俭。又《诗》之《葛覃》谓后妃之本,躬俭节用,化天下以妇道。后妃犹能以节俭化天下,而况其圣世之君乎?节者,不伤财、不害民之谓也。]富贵广大,守之以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夫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此乃富贵广大之极矣。若不守之以约,未有不失之者也。《文子》曰:富贵广大,守之以狭。亦从约义。]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以是知古之圣王,冕而前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聪。明所不见,聪所不闻,非自壅遏也。防闲其淫声谗语、好色奇玩,以乱其耳目也。《老子》曰:君子以盛德,容貌若愚。亦此意也。又《文子》曰:聪明广智,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魏太子击谓田子方曰:“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贫贱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按:《说苑》贫贱作“贫穷”,安往而不得下有“贫穷乎”三字。]不以德厚而矜物。[《系辞》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矜,伐也。《老子》曰:盛德若不足。古昔圣贤,进德修业以务滋崇,岂敢矜物乎?]
【译述】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古代的圣王,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
【原文】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墨子》曰:尧舜德行,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师古曰:屋盖曰茅茨,茨以覆居也。采亦作棌,柞木也。]舟车不饰,[《白氏六帖》曰:门闾舟车不饰,俭也。]衣服无文,[东方朔曰:衣缊无文。《语》曰:恶衣服。又《礼》曰:节丑其衣服。皆言不用文绣也。]土阶不崇,[《墨子》曰:尧舜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故不高也。阶,陛也。]大羹不和。[《礼器》曰:有以素为贵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疏云:大羹,肉汁也。不和,无盐梅也。太古初变腥,但煮肉而饮其汁,未知调和。后人祭必重古,故但盛肉汁,谓之大羹不和。
以上六事,皆言上古明王崇俭也如此。]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言圣人如此质素,非是憎嫌荣华,鄙恶甘美也。乃欲居以淡薄,施以节俭,以身为天下先。然后其教不严而治,不令而行也。]故风淳俗朴,[《说文》曰:上以化下曰风,下以习上曰俗。淳,厚也。朴,实也。]比屋可封。[《史记》曰:尧舜之民,比屋可封。此云圣世之君,躬行节俭以化民,下观而化,相习崇俭。故家给人足,礼义生矣。然后尊卑之序得,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如此,则家稷契而人皋陶,故辟止刑错,比屋可封也。比屋者,《周礼·地官》曰:五家为比,有九比之数,小司徒掌之。六卿大夫于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比,联比而居也。比,毗至反。]斯二者,荣辱之端。[二者,谓奢俭也。]
【译述】那些明君圣主们,常常用茅草盖了房子,都不去修剪得漂亮一些,用柞木立了柱子,都不去砍削得光滑一些,甚至坐的车船也没有装饰彩绘,穿的衣服也一点都不华丽。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去建造高大豪华的厅堂,而且连吃饭都只图饱腹,不求味美。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憎嫌荣华,讨厌甘美,是希望能率先垂范,用淡薄节俭的风尚为天下百姓作榜样。于是,风俗纯正厚朴,邻人和睦相处。因此,骄奢还是节俭,是荣辱的开端啊!
【原文】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奢侈则危,节俭则安。犹声响形影,未尝相远也。行其俭,其身必安;行其奢,其身必危,故云由人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刘子曰:将收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者,情欲之路,嗜好之府也。目爱彩色,命曰代性之斤;耳乐淫声,命曰攻心之鼓;口贪滋味,命曰腐肠之药;鼻悦芬馨,命曰熏喉之烟;身安辇驷,命曰召蹶之机。此五者,所以养生,亦所以伤生。言当收敛而闭之,庶得寿命。嘉,言远而不损耳。]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刘子曰:身之有欲,犹树之有蝎。树抱蝎则还自凿,身抱欲则反自害。故蝎盛则木折,欲炽则身亡,故云凶源。蝎,食木虫,犹蠹也。]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拾遗记》曰:岱舆,一名浮折。北有玉梁千丈,驾元流之上,峰傍有丹桂。唐《艺文类聚》曰:桂蠹不知所淹留兮。又,《汉书》南越尉佗贡桂蠹一器。蠹,食木之虫也。按:《拾遗记》无一名浮折四宇,注误。]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蔡邕《释诲》曰:惧烟炎之毁熸,何光芒之敢扬哉?烟,炎火之微细者。言常惧微细,以致毁灭。杜预注《左传》曰:吴楚之间,谓火灭为音子廉反。炎,音焰。言桂蠹虽小,终损荣芳;火烟虽微,必滞光焰。郁,幽也,滞也。又郁遏、郁悒、郁结、郁郁,皆言不得伸之意也。]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言志之出骄,犹桂之抱蠹;心之生欲,犹火之含烟。若不防微杜渐,节遏其骄欲,必至于志倾身丧也。]故桀[夏王号。谥法曰:贼人多杀曰桀。]纣[殷王号。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肆情而祸结,[言桀纣之君,纵肆情意,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积酒成池,屯肉为林,置炮烙之刑,行长夜之饮,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残贼暴虐,汤武兴矣。故曰祸结也。]尧[唐帝号。谥法曰:翼善传圣曰尧。]舜[虞帝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约己而福延,[谓尧舜恭己无为,俭约是务,是以太平之福延长也。]可不务乎?[桀纣所以亡,谓不能节遏骄欲也;尧舜所以兴,谓其躬行俭约也。一戒一法,可不务为俭约乎?]
【译述】骄奢还是节俭,关乎平安和危乱,而这一切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
如果能清心寡欲,美好的命运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相反,欲望横流,就必然要生出凶乱。所以,丹桂尽管美艳芬芳,假使生出蠹虫,最终也会变成朽木;红色的火苗虽然明亮爽朗,倘若被细微的烟尘所覆盖,终究也将熄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防微杜渐,始善敬终,骄奢就会不招自来,恶欲就要急速生长。骄奢和恶欲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势必要导致身死国灭的惨剧。夏桀商纣因为纵肆情意,倒行逆施,从而引火烧身,自掘坟墓;唐尧虞舜却因为约己修身,顺乎民心,从而使帝业辉煌,江山永续。比较一下桀纣的败亡和尧舜的兴盛,难道不应该更好地躬行节俭的良方吗?
崇俭释评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这两句话最集中地道出了这样一条真理:在俭朴和奢侈之间,人们只有正确地掌握好分寸,既不因为贫困而吝啬,也不因为富有而挥霍,才会出入有常,进退合度。
成由俭朴败由奢。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不仅自己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还不断拿这个道理去教育自己的臣民和子弟。但不幸的是,不只是受教育者,就是教育者本身,也常是嘴上说的一套,背后做的却是另一套。当天下安定,国阜民康之际,那些曾经冷静清醒的皇帝们,也都不可避免地一个个陷入物欲横流、暴殄天物的泥淖,成为后人的反面样板。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反省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崇尚俭朴的必要性到底何在?
《贞观政要》里有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珍奇的玩物和邪淫的技巧,是亡国的斧子;珠宝玉器和华丽的锦绣,其实也是迷乱人心性的毒药。我私下看见陛下您服用和玩赏的都是一些少见而纤巧的东西,好像是从大自然中变化出来的;人们贡献给您的珍宝奇物,又如同神仙制造的那般精美。这些奢华的东西尽管在世俗之中显得那么光彩夺目,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也确实败坏了淳朴敦厚的风气。由此可知,漆器虽然不是引起叛逆的方术,但夏桀却因制造它而导致了诸侯的叛逆;玉杯又哪里是招致灭亡的手段,但商纣也因使用它而使国家灭亡。要考查奢侈靡丽的根源,就一定要遏止它们。在节俭方面制订了法令,还担心会滋生奢侈;在奢侈方面制订法令的话,又怎么能约束后人呢?只希望您能详察不显著的事物,智慧远达广阔的地方,在麟阁中研究深奥的秘密,从读书人那里探求幽深难见的事迹。历代君王治理与祸乱的踪迹,百代安危的经验教训,兴亡衰乱的命运,得失成败的关键,原本就包容在心胸之中,重复在视线之内,这是陛下内心长期考察的结果,无须臣妾在这里绕舌。只是明白这些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不易实行。人们总是在功业卓著时心志骄傲,在时势安定时贪图享乐。只希望您能抑制心志,善始慎终,纠正轻微的过失用来增添高尚的道德,选择今天的正确来取代昨天的错误。那么您的美名就会远播万代,与日月一样无穷,鼎盛的事业也会长久不衰,与天地一样永存!”这篇议论旁征博引、借古喻今,真可谓高屋建瓴,精妙绝伦!但它却并非出自太宗的股肱大臣之口,而是来源于一个后宫嫔妃徐惠的规劝。也许是女姓的心灵更为敏感吧,因而也更能把奢俭的利弊讲得如此透彻。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太宗本人关于俭约兴邦骄奢丧国的论述也同样发人深思。“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太宗这样说了,那么他自己究竟做得如何呢?“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凭心而论,唐代到了贞观年间,国力已逐步发展起来,不用说建一个楼阁,就是造一座宫殿,财力的花费也不会形成什么负担。何况太宗又患有气喘病,在夏秋交替,气候无常,不断受到暑气和雨气侵扰的时候,单从一个普通人的健康需要,也应该改变一下居住环境。可是大臣们劝来劝去,还是被太宗拒绝了。真可谓是令行禁止,身教重于言教。
皇帝既然能以身作则,大臣们就更能严于律己了。不妨仍就引述《贞观政要》的记载:“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征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征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斋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看看吧,这些大臣们生活得多么可怜!上至副宰相,下至中央的各个部长,包括皇帝的顾问在内,没有一个人有所气派的房子,不是面积狭窄,就是破败低湿。但大家都能安居乐业,以俭朴为荣。这些人的清廉寒素与安贫乐道的品格和精神,不用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会令人感佩不已吧!如此动人的情景,又与那些人则华屋,出则肥马的豪奢之举,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许多官吏,面对这样一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超凡脱俗的伟大灵魂,大概会感到汗颜吧?不错,确实有许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其所作所为,分明就是老爷。
世间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又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身居高位的领导者,只要说到做到,而且真正实行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又何愁自己的主张和政策难以通行呢?领导者如果不徇私情、奉公守法,又何惧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呢?
每当读到唐代贞观时期的那段历史,我总是禁不住神往太宗与其臣子们那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乐相处、共理国是的美好情景。尽管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来揭露这种君臣关系的虚伪性,或者我们可以用一千双眼睛去挑剔他们这样那样的毛病,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君臣的和睦团结、风气的纯正俭朴、德操的崇高伟大如此等等,是密不可分的。那种上能导之,下能行之,去奢诫躁、勤俭办事的崇高风范,不是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吗?
毫无疑问,唐太宗是封建时代少见的开明英主,“贞观之治”也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圣世。英主的缔造和圣世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不能被人忽视的缘由,必须得归结到崇俭上去。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俭朴二字。要知道,俭朴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风范,它永远导引人们不断迈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永远匡正人们不要走向假丑恶的歧途。为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重温太宗侍御史马周的一段著名论断:“臣观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
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
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败不作也。”
国有明君,则朝有贤臣。唐太宗能有马周这样的贤臣,难道不是他的福份吗?而马周能有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同样可以无憾
赏罚第九
告诉你赏罚的秘诀:如果奖赏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深受鼓舞,就一定去奖赏他;如果惩罚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引以为戒,那么就一定去惩罚他。
酬功曰赏,黜罪曰罚。《周礼》曰:刑赏以驭其威。赏罚,国之大柄也。《左传》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福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又《汉书》曰:赏及无功,无以劝善;罚及无罪,无以惩恶。唯赏与罚,不可不当。赏一人而天下悦者,赏之;罚一人而天下惧者,罚之。赏罚又当必信也。有功者,虽仇亦必赏;有罪者,虽亲亦必罚。故孔子曰:治国制民,不隐其亲,此之谓也。唯如此,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矣。唯天下之至公,其圣王能之。按:注末句,疑有错误。
【原文】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晋《礼乐志》曰: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以上天化育万物,如人君抚御庶众。]天以寒暑为德,[寒以成之,暑以长之。寒暑,天之德行也。]君以仁爱为心。[仁以生之,爱以养之,故人君当以仁爱为心矣。故《记》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以先行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故曰君以仁爱为心也。]
【译述】天地养育万物,就如同君王统治百姓。--如果说上天以严寒和酷暑作为德行的话,那么君王就应该以仁慈和恩爱作为心愿。因此,不论天地的寒暑如何更迭,君王的仁爱之心应该始终不渝。
【原文】寒暑既调, 则时无疾疫;[疾,灾也。疫,民皆病也。寒暑调,谓六气和也。六气和,则时无疾疫。《左传》曰:天有六气,淫则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也。]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论衡》曰:儒者论太平应瑞,风不鸣條,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又《春秋说题辞》曰:一岁三十六雨,天地之气宣,十日小雨,十五日大雨。言其均匀也。又《乐记》曰:风雨不节,则饥。谓风雨匀,则五谷登稔;风雨不匀,则五谷不登稔。不节,不匀也。故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盖谓人君体天地之道,以仁爱下施。故寒暑调,风雨节,而民无疾疫饥寒之厄,故不至于凋弊也。以上言至治之时,民不犯法,虽有赏罚,无所施矣。]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孔丛子》曰:赏罚是非,相与曲谬,虽十黄帝不能治也。言若教令失度,政必乖违,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蹈于不法者多矣。如此,若非赏罚,不能制矣。]防其害源,开其利本。]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此为教民之道也。或有不遵其教者,则有赏罚存焉。以下皆言用赏罚也。]
【译述】天地的寒暑如能调和不乱,适得其时,一年四季人们就不会生病;自然的风雨如果时起时伏,变幻无常,一年之中人们就可能会挨饿受寒。自然和人间的道理往往是相通的,君王如果以仁爱为怀,常能哀悯百姓,那么人民就会安居乐业,体健事成。相反,如果朝令夕改,是非混淆,人民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从,这是发号施令者应该特别警惕的教训。防止百姓不去触犯法律,又能使他们各务其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实行公正的赏罚。
【原文】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公孙宏曰:罚当罪,则奸邪正;赏当功,则臣下劝。威,服也。化,劝也。]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后汉荀悦《申鉴》云: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在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刑不滥,而威立矣;赏不僭,而化行矣。既不僭不滥,则为恶者知所惧,而为善者知所劝矣。]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汉祖之于丁公,是适己者,不唯不加于禄,又且罚之。不如是,不忠之臣无以惩矣。]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汉祖之于雍齿,是逆己者,不唯不施于刑,又且赏之。不如是,其沙上偶语者皆叛矣。]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文子》曰: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功当,故不以为德。]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文子》曰: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罪当,故不以为怨。按:以上注中引《文子》语,皆今《文子》所无。]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此引《尚书·洪范》之辞以证之也。偏,谓偏于己;党,谓党于人。荡荡,广大貌。言赏罚得中,不因喜怒。故无偏党之私,则王道荡荡然,如天地之广大无极也。故云此为赏罚之权也。权,秤锤,量轻重不失其平也。]
【译述】赏罚必须要明确,而且要适时适度。要用惩罚罪恶,防止小人们作奸犯科;也要用奖赏有功,劝导守法者行善立功。威慑的力量一旦形成,做恶的人就会感到畏惧;奖赏的制度一旦确立,行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赏罚严明,自然就会起到劝善止恶、行善备恶的作用。有的人尽管能顺应君王,但他的行为只要不利于大政方针的施行,或者有时竟然是带了坏头,那么就绝不能因为他会讨自己欢心,而给他加官进爵。如汉高祖对待丁公即是如此。丁公当年作为项羽的部将,曾与刘邦遭遇,情急之中,刘邦以两贤不相害的道理谕导丁公,结果使丁公解除了对自己的包围。楚汉战争结束,丁公以为自己曾经顺应过刘邦,才没对刘邦形成威胁,于是前去拜见刘邦。没想到刘邦在全军面前以不忠之罪斩掉了丁公。在刘邦看来,丁公虽曾经对自己有恩,但作为项羽的部下,丁公的行为又是不忠诚的。至于说到刘邦之所以恩将仇报的动机,其实是再明显不过了:杀鸡儆猴!相反,有的人虽然拂逆君王,但他的做法只要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或许有时竟然能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那么就绝不能因为他惹自己厌恶,而对他滥施刑罚。还以汉高祖为例。当刘邦取得天下大封功臣之际,许多大臣因封赏不均在沙地图谋叛乱时,张良劝告刘邦,如果给高祖的仇人雍齿也行赏,大家见到这种情形,就会认为高祖对仇人都这么宽厚,自然更不会亏待他们。刘邦照计去做,果然平息了纷扰和骚乱,没有因此而引出意外。由此可知,作君王的必须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智慧和胸怀,而不应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一切应从社稷安危出发,不必计较个人恩怨。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受奖赏的人不一定去感激君王,之所以受奖赏,是因为自己建立了功业;同样,受惩罚的人也不会去怨恨皇帝,之所以受惩罚,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这正如《书》中所说:不要偏于私情,也不要结党营私,君王的事业就会畅行无阻,皇帝的美名就会百世流芳。这就是赏罚的重大意义啊!
赏罚释评《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东汉荀悦也说: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这两种理论,既为我们指出了赏罚的原则,也为我们阐明了赏罚的作用。赏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心的向背和统治的成败;也正因赏罚是如此关键,所以使用起来也就更须异常谨慎。难怪唐太宗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自古帝王都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为此,他殷切地告诫大臣们说:“我听说周代和秦代,在最初取得天下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周朝因为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八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使用严刑酷法,所以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做善事可使帝业永久,而做恶事则天命不长吗?”太宗的对比之论,其核心仍在强调赏罚的意义。翻开一部中国古代史,因赏罚不公而导致祸国殃民的记录,真可谓俯拾皆是。赏罚既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道德行为。尤其是在古代,当行政权和司法权尚为一体之时,行政者的道德准则和修养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其司法行为表现出来。仁惠之君,常能宽简爱民,重赏轻罚;暴虐之主,则往往苛酷残民,轻赏重罚,或竟至于有罚而无赏。因此,身居九五之尊的帝王们,只有正确处理好君臣关系,掌握好赏罚原则,才会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就我所知,最早在理论上比较全面而深刻地阐释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当推战国时代的孟子。他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这虽然是一种朴素的辨证法,但却一语道破了治国安民的天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一般只狭隘地把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君臣之“臣”理解为“大臣”,其实扩展开来看,这里的“臣”显然已包括了庶民百姓。君王的爱憎好恶,决定了民心的得失向背。爱憎好恶又如何体现呢?自然仍要用赏罚。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能够做到像《礼记》所说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并进而使赏罚公正无私的帝王,自古及今,确如凤毛麟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魏征曾说:“因官职与地位不相称而受罚,罪过不在臣子自身。否则,要想让他们抛弃私心杂念而各尽其力为国服务,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也不能因小罪而受罚。委任大臣以高位之后,却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就会使那些拿着笔杆子并善于窥测风向的文官们,深文周纳,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为大臣定罪。”魏征的话,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在施行赏罚的时候,一定要看主流,看大节,而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相反,如果尺度掌握不当,就会制造冤假错案。今天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苦了奉公守法的,提了溜须拍马的”。除去其中愤世嫉俗的因素,我们不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赏罚不公的讽刺和批判吗?
东汉时,著名文学家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写道:“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同样的意思,魏征说得更为具体更加透彻。他在给唐太宗的一封奏疏中说:“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这些警策之论,在今天也确实不可轻视啊!可是,环顾现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许多单位,许多部门,有许多领导人物,不是从事业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利益和目的出发,在奖惩之时,推行顺我者赏,逆我者罚的强盗逻辑。
流风所及,阿谀献媚者得以高升,尸位素餐者得以保名,察言观色者得以重用,而正道直行、耿介忠厚者却受到冷落甚至打击。赏罚不公,是非不清的荒唐做法,不但败坏了风气,玷污了法律,更为严重的是使事业停顿,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危害之烈,难以预料!写到这里,唐太宗的谆谆教诲又萦绕在耳际,他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如参读《旧唐书·太宗本纪》,我们还会从正面认识到太宗善于赏罚的光辉范例。“贞观五年..秋八月..二十一日,开始规定地方判处死刑,要复奏过三次后而无疑义方可执行,京城判处死刑,则要复奏过五次万无一失后才能执行。执行死刑那天,皇宫的玉膳房只能上蔬食,管宫廷音乐歌舞的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得演奏。”“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审核囚犯罪案,把死刑犯290人都暂时放回家,要他们第二年秋天再来受刑。后来这些死刑犯都如期归来,太宗于是下诏全部免罪释放。本年,党项羌先后归附的有30万人。”“贞观十三年,..从去年冬天到这年五月,老天滴雨未落,五月十二日,太宗鉴于旱灾严重,自己贬抑而不在正殿听政,令五品以上官员上书议论政事得失,自己则减少膳食,停罢百姓的无偿劳役,派使者分头去救济抚恤,并为百姓申理冤屈,天于是下雨。..”判处死刑,历来是最大的也是最重的惩罚,太宗为避免伤害无辜,特别下令要多次复核。又因为死刑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从而引得太宗不忍下手,一律宽赦,其谨慎之心,仁慈之德,真是溢于言表。在封建时代,皇帝即是真理的化身。而老天下不下雨,本是自然现象,与皇帝本人并没关系,但太宗却把天灾视作人祸,甚至用减少膳食、自我贬抑这种近乎残酷的手法惩罚自己,这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可是作为举手投足可为万世法的天子,用得着去玩儿这些花架子吗?行赏罚而至于罪及自己,避天灾而至于惠及下民,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今天那些好委过于人、争功于己的领导者与太宗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我们也似乎可以理会,“贞观之治”的家给人足、天下太平的美好景象,原来就是靠这样的感天地泣鬼神的义举换来的啊!
与太宗勇于惩罚自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太宗为能摸到实情、为听到真话,更为能得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又不知奖赏过多少个他的大臣们。有兴趣并且愿意的读者,可以用数学统计的方法从《贞观政要》及唐代别的典籍里去查证这个事实。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在太宗所有的大臣里,魏征是被奖赏次数最多额度也最大的一个。细心的读者更不妨去作一个个案分析,看看太宗到底是怎样不吝其财地去奖赏他这个“智囊”的。天不下雨,太宗要惩罚自己;洪涝成灾,太宗也要惩罚自己,地震发生,太宗还要惩罚自己。史官们的记载或许不免粉饰,但再粉饰,也必有所据吧。要知道,这些记载太宗都是亲眼看到过的,他总不会去不顾事实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欺骗舆论和民心吧。大方地赏人,不断地责己,把赏罚大事当作国计民生的根本,大哉,太宗!贤哉,太宗!
由太宗之贤,我们又不能不说到长孙皇后之贤。《贞观政要》载“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廖,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透过这一段母子对答,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识大体明大理的贤德的皇后形象。在古代,皇后病危,一切方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长孙氏却不因一己的性命安危而扰乱国家大法。她深知,无端地赦免囚徒,无故地度人入道,这无异于滥施赏罚,因而她宁愿扮演一个法律的自觉维护者和模范执行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