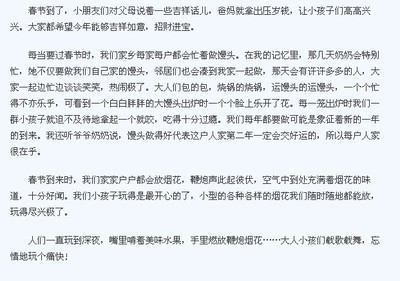摄影:心尔夫人
近来吃的大米,做饭软硬适中,还有股淡淡的香气。可到了买米的时候,偏又忘了牌子。而同样价格的大米有好多种,只好凭印象瞎蒙:“买秦香玉。”老板娘犯了愣怔:“没这个牌子呀……”想了好一气,打量我一眼,才迟迟疑疑的说:“是泰香王吧?”瞧我这记性。老板娘见我不好意思,安慰道:“像你这个岁数,我们村好多人都不识字,没文化,少烦心,照样快活一辈子。”
坡翁道:“人生识字忧患始。”老板娘的意思庶几近之,不禁让我刮目相看。所以没解释,一是无此必要,再则说错别字也不算丢人,谁让老祖宗造恁多字呢?关键是谁说错别字,和对错别字的态度。
关于错别字,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位白字先生,正读《水浒传》。人问:“所读何书?”答曰:“水许。”“所写何人?”白字先生道:“有一李达,手拿两把大爷……”闻者无不绝倒。
如果说这是瞎编的,那冯梦龙所纂的《古今笑史》里,“琵琶果”的故事却有名有姓:“莫廷韩过袁太冲家,见桌上有帖,写‘琵琶四斤’,相与大笑。适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问其故。屠亦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为当年识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屠赏极,遂广为延誉。”因错别字而引出一段佳话,可谓雅人深致。
别的不敢夸口,但在错别字上,我向来闻过则喜。不论场合,也不管人之多寡,一经指出,由衷感谢。外甥女焱子,是中学语文老师,上周还帮我纠正了狡黠的黠字。我念“吉”念了好多年,汗颜。
推己及人,我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有位同事,性格倔强,兴许是我方法欠妥,为他纠正了错别字,他不仅不谢我,还发了小脾气:“我知道你说得对,也知道我念得不对,但我就是不高兴。”二回他又错,我心里为他着急,但再也不敢造次。——怕他生气。
谦虚的人也有。一次参加朋友婚礼,有个主持人口才颇佳,说得天花乱坠。但出了两次错。一错是说新郎的父母含辛茹苦,把呱呱落地的新郎拉扯成人。呱呱读为瓜瓜。这错问题不大;另一错说新娘亭亭玉立,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错问题就大了,即便这次蒙混过关,下次呢,下下次呢?总有挨耳光的时候。我写了张纸条,折好,递了上去。没想到开宴后,主持人特地来敬酒道谢,极为客气和诚恳。这样的好青年,罕见。孺子可教也。
这种主持人范围小,环境又嘈杂,听众注意力也不集中。若换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记得很久以前,一位播音员将海獭读作“海赖”,这不过是一种动物的名字,又无关国计民生,但前几天仍有人提起。至于播音员的姓名,反倒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件事就非同小可了。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主持欢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连出三错。先是把赠送宋楚瑜的书法作品说成“捐赠”,接着又不认识篆字书体,当读到黄遵宪《赠任父同年》这首诗的第二句,“侉(写的是单人旁一个瓜字)离分裂力谁任,居然卡壳。顾秉林不仅是校长、教授,还是中科院院士,有此三重身份,实在让清华蒙羞,让中国蒙羞。而这次活动又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这洋相就出大了。——地球人全知道。其实,稍做准备,这些错误都可以避免。治学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我少年时即参加工作,进了一家街办工厂。同事们文化程度不高,认错字是家常便饭。有天,小伙伴成义告诉我们,电影院在放一部电影,名叫毛个个。毛个个,什么意思?下班去看,原来是纪录片《毛竹》。此后,毛个个就成了成义的绰号。
还有一次,同事小罗的男朋友请她看电影,她有点炫耀的意思,拿出电影票,说电影的名字叫少家兵。少家兵是什么兵?不是什么兵,而是《沙家浜》。女孩子脸皮薄,不敢为她取外号,但结婚典礼时,还是有欠厚道的人,说起这段故事。
我运气好,烧窑的熊师傅以前是个语文老师,犯“政治错误 ”遭贬于此。有他教诲,加之我又好问,闹的笑话不多,幸没留下什么话柄。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直言如我者,也不是任何时候都为人纠错。曾陪朋友去见他舅。他舅特严肃,特正统,喜欢教训人,口头禅是:“嗯,思想不能太狭义;嗯,心胸不能太狭义。”不能狭义那就是广义,蕴涵什么玄机呢?莫非有深意存焉?出来问朋友,他没好气地说,鬼的玄机,就是狭隘。怎么不告诉他呢?朋友说,不敢。他反问我,实话实说,我也不敢。
更有离谱的,明知故犯。开政协会时,一位副主席喜欢说“温嚷”。提案不少,“温嚷”的次数就多,听得人心里别扭。没想到分组讨论时,我们的组长也让我们“温嚷”。组长是我的笔友,隔三差五在刊头报尾发文章,他的“温嚷”让我忍无可忍。我说,你不会连酝酿也不认识吧?他左右顾盼,拉我到一边,悄声说:“领导说‘温嚷’,你偏要酝酿,这不是出风头,和领导唱对台戏吗?”
我闻之愕然。暗忖:如果有人编《新笑笑录》,这倒是一则不错的素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