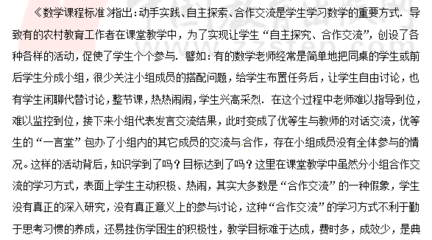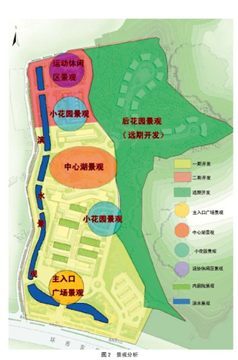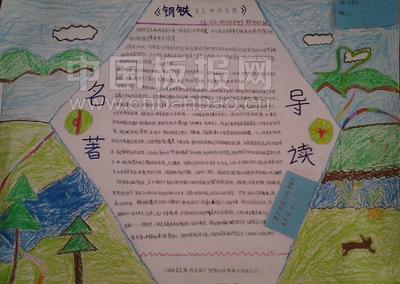“在伤口上开出朵花来”
——浅谈伤痕文学
摘要:“十年浩劫结束,噩梦醒来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在明暗交界的境地,感情却已经复苏。”十年文革的历史浩劫中,是非正义,道德伦理,价值感情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无数的个人和家庭分崩离析在悲剧的黑影下。文革,给每一个幸存者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本世纪70年代末,一种描写文革伤痕和个人与家庭悲剧命运的文学——“伤痕文学”在文革结束之后就应运而生。一般来说,伤痕文学以北京作家刘心武197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班主任》为开端。而它的名称则来源于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的面世,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闸门,迎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春天。虽然,由于时代变幻的激荡人心,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刚结束的文学先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伤痕文学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革阵痛之后,那些留下的伤痕可以在每个晚上清清楚楚地从头到尾再疼一遍。但伤痕文学却坚持着,要在这些伤口上开出朵花来。
关键词:伤痕文学文革背景《班主任》《伤痕》意义局限性
正文: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兴起了一场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这场文学思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史上也具有深刻意义。很多时候,我们要听到大风呼啸过峡谷,才知道那就是风。我们相信时间会荡涤,证明一切。30多年过去了,而今再回首,对于伤痕文学,我们还要细看,细评。
一,伤痕文学的时代背景
十年“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波澜曲折。汹涌的政治浪潮一个接一个打过来,世界混乱了。是非正义,世人没有分辨的想法,尺度和能力。道德崩坏了,礼乐也已尽失。大揭发,大批判,大义灭亲,人人自危。家人朋友老师学生,最亲近的人转眼之间可以变为最陌生的敌人。不能自我选择的身世和家庭背景,是送我上青天的好风也是敲响灭顶之灾的丧钟。知识和文化,学历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罪恶和负担。牛棚里住满了面容沧桑身体虚弱的知识分子,拥挤着分分秒秒的自我轻贱和被轻贱。思想在牛棚外戛然而止了。那段黑暗癫狂的岁月和时光,苍老悲催了一代人。饱受苦难折磨的国民内心伤痛层层覆层层。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悲愤,痛恨,后悔,遗憾,太久了太重了。那些刻在心里的道道伤痕像个倔强的孩子,不肯愈合。这些情感都急于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要像澎涌而出的岩浆和激流,决堤之后,恰似天上来,不可阻挡不可忽视。绷紧了的皮筋总会断掉。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真理的标准”讨论日趋白热化,思想开始解放。文学要走回正途,康庄大道似乎有了方向和蓝图。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下,国民内心郁积的万千愁绪和伤痛必然会在文学领域中留下沉重的脚步和声音。文学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使命和根本规律。社会主义新时期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在这样惨痛沉重的背景之下喷涌而出,非但不足为奇。相反,如果彼时文坛依然固我“一潭死水”,却是不可思议的了。当政治开始解冻,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伤痕文学的兴起
1977年,《人民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北京作家刘心武的一部短篇小说《班主任》。某中学的一名教师张俊石,他带领着好学生石红,团结了班上思想正确的广大同学,同深受反动路线和错误思想浸淫的学生谢慧敏和宋宝琦进行斗争。张俊石在文中是正义的化身,是正确思想路线的坚持者和宣传者。他尽力挽救着在四人帮的毒害下不学无术,和把《牛虻》当成“黄书”的中学生。最后文章是以张老师充满信心结束。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今天看来很平实普通,甚至很稚嫩造作。但穿越回归至那个年代,这篇小说无疑契合了当时的心声和主题。作品的整个结构和情节,都试图服务于一种“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不由使人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80年代的这场启蒙潮流确实和“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两种时代背景和国民的心灵,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当时的文艺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革对于青少年心灵世界的毒害和压迫,震撼了浩劫中幸存者苦难者的心灵,打开了他们回顾伤痛的记忆闸门。正是因为“时势造英雄,英雄需时势”,这部小说,在当时创下了蜚声海内的盛绩,并使得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但这部小说只是启动了伤痕文学,自身却并没有成为伤痕文学。因而,它其实也就不能被称作是伤痕文学的正式起点。
1978年,上海复旦的一名大一新生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因为植根于“文革”刚结束的时代背景,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如果说《班主任》还保持着光明的基调,而卢新华的《伤痕》则是将光明的基调转变为了忧伤。《班主任》因为发出了时代的新声,而且沿用了“文革”的模式,所以受到了举国上下欢迎。而《伤痕》因为背离了“文革”模式,发表时就曾经遭遇过险阻,发表后更是引起了海内的震惊和激烈的争论。但正是因为《伤痕》的这种转变和突破,才正式启动了一种特属于某个时代的文学思潮。
也许,《伤痕》正是像一块石头,因为投进的是一潭被遮盖、扭曲的伤心死水,所以激起的波澜就从时空两个方面一波一波地荡漾开来。随后,一批和《伤痕》有着相似主题的小说纷纷涌现。自此,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思潮,开始在文艺界兴起,发展,繁荣。而这种文学思潮,在整个读者群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思考和研讨。
三,伤痕文学的发展
继《伤痕》之后,反映文革伤痛的大量伤痕文学作品涌现。作者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宣泄和控诉:各个阶层,青年,知识分子,老革命干部,商人,护士,农民;各种社会苦难折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样的情感,悲伤绝望,激动怨恨,庆幸感慨。写青年(红卫兵,知识青年)的伤痕文学作品就有,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胡月伟、杨鑫基的《疯狂的节日》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其中,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在早期的伤痕文学中是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作品。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虽然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在艺术审美价值上其实是十分稚嫩的;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更是题材广泛内容翔实,有茹志娟的《家务事》、肖平的《墓地与鲜花》、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王蒙的《布礼》、李国文的《月食》、宗璞的《三生石》……。这其中,像茹志娟之前写过著名的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百合花》,宗璞写过《红豆》反映知识青年面对革命和爱情如何抉择,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也是对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一些官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伤痕文学中还有一些写老革命干部的,如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莫应丰的《将军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一般认为,莫应丰在1979年出版的《将军吟》是伤痕文学中,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的准备时间一般较长,所以伤痕文学最初大多是短篇。
像青年,知识分子,老革命干部是和“文革”伤痕直接相关的三大阶层。不过后期的伤痕文学题材突破了这三个阶层,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写商人的,代表作是方之的《内奸》;写护士的,就有刘克的《飞天》;写农民的,有韩少功的《月兰》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甚至还有写少数民族的《甜甜的草莓》。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取得了较高审美艺术价值的伤痕文学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屏或是改编成电视剧。像古华的《芙蓉镇》,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以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它们被制成影片放映之后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场曾经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伤痕小说”看来已经是午夜梦回后的冷汗和泪水。所以,早期的伤痕文学作品基调和底色大致是阴郁低沉的,充溢着文革刚结束之际的愤恨和不平。这些早期伤痕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荒诞不羁的故事,或以真实而残忍的场景描述,反映着类似的主题——十年动乱浩劫摧毁了中国人民的内心长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人性的真善美被扭曲变畸形,只有假恶丑横行当道。极左的路线和思潮泛滥,像是铺天盖地而来的黑色云层,吞没了理性和良知。人生变为了曲折和痛苦。感情只是拿来消遣,利用和背叛。命运只剩下无谓的纠缠,反复和无常。这统统都是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初关于血和泪的经历,认知。所以,他们极度否定和批判崇尚激烈奋进的左倾路线、政策。他们对于未来,苦闷彷徨,失落迷茫。他们用一个个汉字哭诉压抑了十年的折磨和苦痛。伤痕文学作家们在此时,几乎是肆无忌惮的宣泄着自己长期抑制的悲愤和怨恨。他们叙述故事,带有浓烈的个人伤感情绪。每一处遣词造句,都真实的再现和控诉了那个年代的焦灼,扭曲,病态和残忍。细心读来这些作品,再联系那个时代,确确实实是“字字血句句泪”。
不过,这些早期的伤痕文学因为感情过分“充沛”,在艺术价值上其实失了水准。就像刚刚从极度令人恐慌的梦境中醒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倾诉。因为情绪太过急切,叙述的语言在不可知不可控的的情况下言就会混乱,就会变得矫揉造作。后期的伤痕文学作品,渐渐成熟起来。像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以及冯骥才的作品,后期都在试图突破情感的个人局限性,表达出对于整个人性的深刻思索,讨论和关怀。在这种背景下,也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对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规模巨大的文艺思想讨论。
四,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局限
1,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
文艺创作总是能够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偶然反映必然,通过一人一事反映千家万户。伤痕文学也不例外。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的面世,是历史发展至某个特殊时期的必然现象,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虽然这种开端是在饱经了风霜和苦痛之后的血泪控诉,但它的历史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份沉重的时代背景,显得更为厚重和深沉。
首先,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又重新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沿袭至政治的“假、大、空”习性,使文学返璞归真。伤痕文学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关于丑,恶和乱,写出了赤裸裸,酣畅淋漓的真实。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从一个家庭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姐弟,或亲朋、师生在文革风暴面前的遭遇及其纠葛,再现了那场空前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触及了那些悬而未提悬而未决的问题。“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到底“四人帮”的性质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四人帮”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它究竟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造成了罪恶和危害?如何防止悲剧的重演?这些问题,文艺有责任要给予回答。比如最早的《班主任》就通过塑造宋宝琦和谢惠敏两个饱受“四人帮”极左路线浸淫的青少年形象,提出了要关注拯救青少年心灵创伤的问题。而《伤痕》则是通过王晓华及其母亲的悲剧命运,提出了必须彻底废除林彪、“四人帮”的“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专制的问题。这些小说,以悲怆苍凉的艺术笔调,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着生活的真实历史的惨痛。为人民立言,表达人民的心声的伤痕文学,一经问世,自然就能获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其次,伤痕文学一改以往空洞的说教文艺观,反而强调了情感宣泄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伤痕文学中经常弥漫着浓烈的个人情绪,混乱和迷惘,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被宣泄到了极致。在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劳苦大众憎恶空洞的,“高屋建瓴“的,所谓概括性论述性的假言假词。说教式的文学,已经没有存活的空间。伤痕文学再次回归情感,以情感人,以情教人。没有站在高处冷冷的思考和教导,伤痕文学只是写出了自己的伤痛和悲伤。他们更多的是寄予了一种期盼,盼与国民一起回忆和倾诉属于他们的那些过去。
还有一点很重要,伤痕文学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第一个悲剧思潮。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中美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文学在中国,其实一直不是十分盛行。当然,这跟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国民性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盛行,文学被严格要求只能反映现实,歌颂现实。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学,在中国似乎没有任何迹象。但文革本身其实就是一场世纪大浩劫,社会大悲剧。一旦文革结束,经受了巨大创伤内心积怨很深的国民,情绪喷发之时,也就是悲剧诞生之际。伤痕文学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文学思潮,首次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伤痕文学中,一些作品的悲剧色彩比较浓厚,有西方悲剧的影子。著名的如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主人公严凉与穆兰,都是文革时期“根正苗红”血统论的受害者。在已经处在疯狂边缘的人群和社会里,他们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内心伤痕累累。后来,他们两个人在一条小河边相识。爱情并没有抛弃两个可怜的年轻人,他们相爱了。在风雨重重之后,相爱的两个人终于结合。但命运从未放过他们,噩梦在短暂的幸福之后尾随而至。历史无情的分开了他们,又狠狠的捉弄着他们。现实太过残忍,明晃晃的姐弟关系劈开了甜美的梦境。作者想要展现的一种来自历史的悲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还有一些伤痕文学作品也都或多或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悲剧意识和悲剧色彩。
2,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
伤痕文学固然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否认,因为伤痕文学是文革刚结束之后兴起的文学模式,它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
一方面,在艺术价值上,伤痕文学显得比较青涩和造作。伤痕文学整体的艺术成就不是很高,它的巨大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历史意义而非纯粹的艺术审美价值。许多作品因为情感饱满激烈,呐喊直白冲动而显得流于肤浅。作家经常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中,有意无意地穿插大量的心里独白或倾诉。以上文的《在小河那边》为例,文中有这样一段内心呐喊和觉悟。“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样的一段话,在现在看来政治性很强,也过于直白。另外,伤痕文学的很多作品有些情节十分离奇,也过于偶然,人为雕琢的痕迹很重。像《在小河那边》中的乱伦悲剧虽然惹人叹息,但因为其中偶然性的因素比较大而使得情节的安排很不真实。读者无法在阅读之后,内心产生震撼和深沉的情感波澜。而小说的最后,又是以匪夷所思的喜剧结尾——原来,严凉与穆兰并不是亲姐弟。这样的结局固然是皆大欢喜,但因为太过突兀和虚假,整体的艺术价值就下了一个层次。其中,还有一些作品也因片面地渲染鲜血淋淋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和非议。
另一方面,伤痕文学虽然旨在表现、批判和否定文革,但力度和深度是不够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哭诉”是伤痕文学的主调。这些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宣泄个人情感谴责部分政治弄权者,却缺少理性的思考和深层次的寻根问底。伤痕文学作家的思维视野还停留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中,这就严重影响了作家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因而,他们无法对文革做出整体的,本质的,深层次的反思和评判,也缺乏对于文革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的探寻和解答。像宗璞的《我是谁?》中的韦弥最后选择用死的方式来对抗人的尊严,价值被侮辱,驱赶和鞭打的现实。伤痕文学确实宣泄了长达十年的创伤和痛苦,但也止于此,他们并没能对现实和自身作出更为理性和全面的反映。伤痕文学表达出了灵魂的痛苦,却没有深入到这痛苦的背后去找寻根源和解决的方法。因而这痛苦也就流于了表面,成了一种没有内容的矫情。同时,伤痕文学虽然再现了悲剧意识,却显得表层化。悲剧在于撕破美,但绝不止于此。深华悲剧,需要在真实表现灾难的同时展现崇高。天地为炉,万物为钢,谁不是在受折磨?但极致的悲剧关键点在于,是受难者的美好遭到了毁灭。并不是所有的受难者都是美的体现者,都能在经受痛苦之后引起读者的共鸣和震撼。伤痕文学中的悲剧性就明显地存在这种弱点。一些伤痕文学作品虽然体现了悲剧的意识,但还不够强不够深刻。在阅读作品时,面临一个个惨无人道,接踵而至的劫难,读者内心徒添同情但缺少心灵的震撼和洗礼。
“十年浩劫结束,噩梦醒来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在明暗交界的境地,感情却已经复苏。”1977年,伤痕文学开始出现,80年初就渐渐进入了尾声。伤痕文学固然有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暇不掩瑜,从整体上来看伤痕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确实是巨大而深刻的。相信历史会铭记住的,那一段民族浩劫之后,属于整个国民的伤痛和伤口上的那朵白花。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3,叶穉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浅探》
4,“伤痕文学”百度搜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