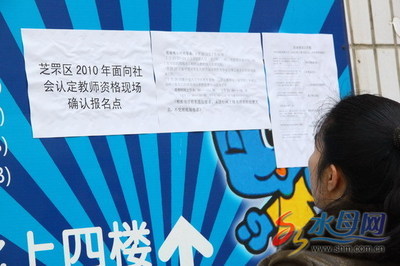他很帅气。一身皮衣一条黑星围巾现身在上海的风雪里,看上去跟“教授”这个称呼远不相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1976年出生,今年刚35岁,眼角只有微微的皱纹。由于他一笑脸上会现出两个酒窝,博客上那张大头照显得很圆润。
事实的另一面是:他确实只是个讲师。他带过的学生都成副教授了,尽管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或许远不如他。
两年前,杨师群教授“遭两女生举报反革命”事件时,他还在学校教务处副处长的位子上,正好被派去调查这件事,给两个女孩做笔录。举报杨师群的,其实是她们的父母。他提问题的方式很独到:“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到杨老师说叉叉功的事情”?
自然,答案是肯定的。杨师群遂平安无事,今年正常到年龄退休。
这可以算是杨老师为此事受到的一点影响。否则,像他这样的教授,一般是返聘的。他说。
一般是返聘的,这个定义原本也属于他。作为一所中国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如有变动,一般都是平调或升迁,很少直接被撤。而他不仅是被撤,连作为候选人续聘的资格都没有。
官位没了,讲课的权利也没了。作为硕士生导师,他不能给自己的硕士上课,也不许给本科生开课,只能去上夜校和函授的课。
2009年,他的年终评定延迟了一年被宣布不合格。这一年,他总算是合格了。口头宣布的。
他已向学校打过报告,要求恢复上课的权利。尚无下文。
他本是很平凡,也很受学生欢迎的一位教师,终日在民法、信托法和证券法的漩涡中打转,指导指导《胎儿的权利保护》《论海运提单法律属性及贸易实务规则之例外》之类的论文,过着从书房到教室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课的日子,他基本上都闭门谢客,在家读书。
2009年,他去新加坡访学三个月,《联合早报》约了他写评论专栏。一开始写几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无声无息。直到那几篇《中国应该去马克思主义化》《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李庄认罪背后的丛林法则》惊雷般先后爆出。他的生活从此改变了。西政校友贺卫方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给他写来信,用了“振聋发聩”等词。这让他很扭捏不安。
上网百度一下自己的名字,扑面而来的是“洋奴”和“精英叫兽”,他笑笑。一如他看到自己的头像被某个左派网站加了一个绳圈的时候。
听说能和他吃饭,年轻记者们无不趋之若鹜,但没人想真的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也有记者来采访他。外媒他谢绝,内媒的选题基本上都被主编们自己毙掉了。这一段,他自己也很自觉地停下文章的写作,“避一避”。
他说话中气很浑厚,很刚正,带着一股年轻学人的认真劲儿。马克思的书,他都一本一本认真读过,有的还是英文版。为了写批判的文章,他还研究了从生物进化论到量子力学的各种跨学科理论。并不断反思自己在某篇文章、某个段落所举出的某个范例是否不那么恰当。
他自称休谟的信徒。我问他:你是否不可知论者?他点头。
在文章中,他多次表露这类观点:人类怎么能凭已知的经验,来为未来的事物作出规律判断、并认定这种规律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怀疑、不可否定的真理呢?如果是,那它就不是科学了,而是神学。
来上海的头几年他做过律师,因此买了一间小房子。为了投身学术尤其是他喜欢的哲学,不干了。但执照一直留着。一些做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朋友早已相互约好,万一他真的被迫离开学校,就由其中某位收编他。
“这个年代还饿不死人吧”,他说,早已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其实他根本不必做这样的准备。只要写一则短短的“思想认识”,检讨一下自己对“学术无界限,课堂有纪律”的认识不足,什么都可以恢复。他回答说:我不愿意那么分裂的活着。
学校一位领导私下里对他讲:张雪忠,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倔!我都恨不得替你写个东西,帮你检讨几句。他笑笑,谢绝了。
他很理解学校受到的压力。据说,市委书记把他写的文章打印出来,砰砰啪啪拍在校长面前。还有中央大佬插手过问。所以,他也没有想过要改投别处。
他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对政界、商界、学术界的精英们,那些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做高瞻远瞩目光坚定状的大佬,颇多陌生。他的那些文章也没有招来多少学术价值上的探讨或曰责难。
可能是因为都太短,他们认为不值得反驳吧。他猜。
也可能是他们无话可说。你想想,人家搞了一辈子马列,被你咣当一声宣布是虚度人生,让人情何以堪啊。他无语。
他交往的很多人都是法律界的。这很正常,搞法律的人,肯定都要接触到司法的精神实质,思考司法体制的终极走向。因此,敢于公开为他鸣不平的人,也多数他们。
他被停课后,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说:大学当以倡导多元、兼容并包、质疑批评为本。传授说一不二的知识的地方,是小学的算术和几何课堂。“如果华政仅仅因为张雪忠老师发表的几篇商榷文章,就解聘其教职。那么,华政显然就不配叫大学,而应当正本清源,改挂‘华东政法小学’的牌子。”
他是江西一个小镇的儿子,17岁师范毕业,又从中专生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当上大学教师。他很感恩。不加入任何党派,也不参与现实活动。某某被解聘了,某某被盯梢了,某某又被国宝请去喝茶了,这些外人看来离他近在咫尺的事,他自己毫无察觉。
他从没有想到要离开 上海,更不准备出国。
我们搞的这些研究,在国外是没有市场的。人家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搞得很明白了,现在根本不屑于搞这种基础理论的问题。马克思在国外很多哲学史里,也是不被收录的。人家不认为他是哲学家。他的学说很模糊很粗糙,不成体系,而且纯粹是来自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摘录组合。
他正在逐一收罗和阅读哲学著作,最远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为了写一本系统批判的书,已经有了十几万字。
他的大部分博客都被删得干干净净,最近喜欢上了微博。不仅因为它传播快。更因为它能让每一个人都发声。
对“你认为还有多少年”这样庸俗的问题,他沉思一下,说:这个不好讲。可能要看技术的进步速度。
“我真的认为我的文章没有多少价值……真的,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