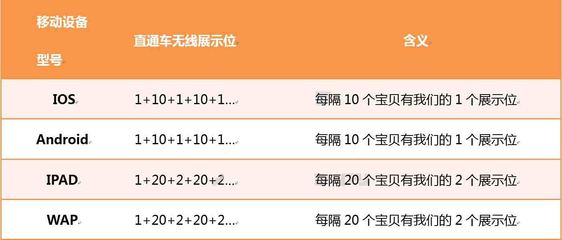在儿时的记忆里,得胜堡有一座老油坊。它与《天工开物》中记载的榨油作坊如出一辙,甚至更为古老。《天工开物》记载:“凡取油,榨法而外,有两镬煮取法,以治蓖麻与苏麻。北京有磨法,朝鲜有舂法,以治胡麻,其余皆从榨出也。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而中空之。其木樟为上,檀、杞次之……”
要说这老油坊有多老,得胜堡老人们的普遍说法是清朝咸丰年间本村一个大户人家创办的,也有说是乾隆年的。单看那个长四米、直径近一米的圆木油槽就可知它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盛夏的一天,我从塞外回到得胜堡,沿着雨后泥泞的小路到坐落在堡墙边的老油坊去访古。放眼望去,得胜堡的颓垣残墙面目依旧,顽强地站在那里好像在向人们证明它的存在,但依墙而建的那座老油坊却面目全非了,屋顶已经塌陷,屋墙也被土石和蒿草将其一半掩埋。唉,时光的流逝使这座老油坊几近灭绝,我那梦境中的故物是最经不起岁月的冲刷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还没有进入雁北,一切劳动不是靠畜力就是靠人力。儿时觉得最累人的活是用碾子推面,最有趣的活就是榨油了。那时,舅舅家对面就是这座老油坊,一出院门就能看得见。这油坊不仅给本村人提供方便,同时还兼顾着方圆十几里的众多百姓人家。
说起这古老的榨油技术十分有趣。一般榨油都选择在秋冬时节,因为榨油是相当酷热的活儿,夏季节热得人受不了。榨油首先是选油籽,用筛子去除瘪籽和杂质,然后炒料。架起柴火,将油籽倒入一口很大的锅中,用木质小铲不停地翻动。炒料的火候不好把握,炒不到位,出油率低;炒得过头,不仅出油率低且榨出的油味苦。因此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炒好的料要及时凉开,否则里边的油籽就会变味。接下来用石磨将炒熟的油籽磨细,再放入蒸笼里蒸半小时左右。
在榨油的工序中,“箍饼”挺有看头。碾碎的胡麻籽蒸熟之后,“油鬼子们”抽出一把整齐的麦草,平铺进油圈,然后扯起蒸笼上的布袋,将滚烫的胡麻籽便倒进了用麦草铺底的油圈中。然后弯背躬腰,舞蹈似地围着铁圈颠着,把油饼紧紧地踩在脚下。当升腾的蒸汽与穿堂而过的阳光相遇,在里面忙碌的油匠们,便成了一道风景,好看极了。
与其说是榨油,其实是“压”油。油槽是一根大约四米多长,一米多粗的木桩,内部掏空,中间有凹槽。榨油时,油匠师傅先将油饼整齐地码入油槽里。然后两个壮汉各自站在油槽的一头,手抡着木槌,用力向下打击木楔。“咚、咚、咚……”左右一唱一和,有节奏有规律,沉重却也和谐。两人默契地配合着,每一次重锤落下,那沉沉的响声传得很悠远。
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胡麻油在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嗞嗞”的声响。随之空隙加大,木楔不断增多,锤声加重,两人演变成了三人同台。
即便冬天,他们也只穿了一件背心,饱绽的肌肉裸露着生命的强悍与力量。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顾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流出了醇香的胡油,如流水般清醇,亦如春天的雨帘,清新而绵密。三个汉子的火热场景和着油槽缓缓流淌的胡油,淅淅沥沥,生动而壮观。
中途休息时,油坊的人们将榨出的热油舀一勺倒在炒锅里烧烧,再取出来时带的馍馍放到里边,“嗞啦”一声,那个香呀,远远都闻得着,常惹得孩子们流口水。有时他们看我们那个馋样,就抓一把炒熟的麻籽打发我们。
油坊是男人的天地,女人视油坊“妖魔鬼窟”。女人从不进油坊,即使在油坊跟前做农活,也不敢随意瞟一眼,闺女们更是远而避之。
那年初秋的一天,一名不知就里的外村妇人背着口袋笑盈盈地走进油坊——槌声、呐喊声戛然而止。男人的领地,闯入了异性,作坊里顿时炸开了锅。热气腾腾的蒸锅边,几个男人嚎啕着,抓了麦草捂住下体,随即传出一阵嗡嗡的呵斥声:“大……大姐——你怎么……”一个油匠结结巴巴地说:“油坊是……是你进的吗?”
“我怎不能进?我换油。”妇人不以为然。暗淡和雾气,她可能未发现里面早已乱作一团,还眨巴着眼睛细瞅。她猛地一怔:“妈呀,你……你们怎们红麻不溜子呀……”甩下口袋,哭叫着,落荒而逃。
昔日得胜堡的油坊还是社队干部请人吃喝的地方,这也是它最吸引人之处。农村没有饭馆,请人吃饭,就在油坊。因为这里有油啊!炒几个萝卜也是香的,再灌上两斤老白干,事情就办成了。所以,得胜堡的油坊,圪佬子里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支个小方桌,摆几个凳子,每天都不闲着。听说有个队长还发明了一种吃法,把窝头用火烤好,往眼里舀点油就吃,不知好在何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愿景不仅适合城镇化,也适合乡村发展的思路。和老油坊一样,乡村还有许多这样的“文化遗产”正在现代化的“侵入”下瓦解、消逝。等到全部都“荡涤”干净,和城市同化得一模一样了。那时,乡村在哪里?内心那一片柔软而悠远的“乡愁”,将何处可依?
同样是“落后于时”的事物,现代化高度发达的欧洲,“磨坊”这个充满文化意蕴和“乡愁”的器物被允许象征性地保留下来。保留下后不但不显得“土气”,反而多了一层现代化与历史感完美交融的韵味。
“老油坊”是一种民俗的标志,可以安放我们愈来愈迷失,愈来愈怀念的“乡愁”。在我们过去的发展史和文化史上,很多东西都是“失去之后才想起再拥有”,然而却无处追寻。站在得胜堡颓垣残墙的老油坊前,我怅然若失、游若浮萍,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根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