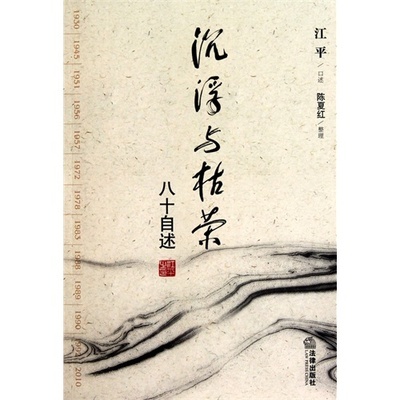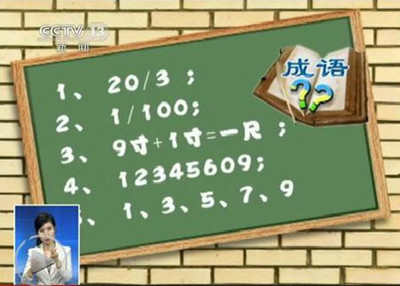[注3] 俞可平
俞可平,一九五九年出生的浙江诸暨农民。高考落第只能在当地的一个中专学校学外语,但很快“开窍”一举骗考上了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三年后论文不合格不能举行答辩,然而早已“开窍”了的他干脆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导师”赵宝煦的“政治学博士生”,然后再挟“北大博士生”之名头“飞过海”到广东中山大学补办了“硕士论文答辩”。一九八八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因可分到三室一厅的房子而混进“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工作”,拿到房子后大肆张扬炫耀了一通,其实他那个位于北京白家庄的房子处在高层顶楼极不象样,下了电梯还得自己再爬一层,相当于是“设备层”改造的货色。俞可平进入“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先蛰伏了一、两年,摸清门道、“打好窝子”后便开始了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拍马行贿、背后下刀子的勾当,而被他拉的人无一不是农民、“草根”出身者,被他打的人则全都是城里人,其中尤以“干部子弟”为主要目标。鉴于中共愚蠢的政治和“中央编译局”既委琐又低级的小环境,俞可平很快就如鱼得水、官运亨通,直至在二零零一年当上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但是在此以后,由于他一方面不遗余力、不知羞耻地到处吹捧自己、企图在现有平台上一举跨入中共高层,另一方面又不顾前后左右地恶毒打击身边每一个有点能耐的人和城里人,甚至能把对他升迁有恩的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整出心脏病来,因此他很快就“自我爆炸”了,变成了在很大社会范围内被人们鄙夷和耻笑的对象,而中共方面亦对他嗤之以鼻、加以防范。
其实,在俞可平把中共骗得团团转、处于步步高升阶段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清楚地指出了他的恶劣品质和下流表现,但本身藏污纳垢且狂妄麻木的中共完全置若罔闻。人们当时就指出的俞可平的一些问题是:
一、俞可平个人政治野心极大,且急功近利,而一圈“理论权威”的光环有利于他的升迁,为此他在国内外厚颜无耻地招摇撞骗,并利用“中央编译局”这一单位的闭塞和本身毛病,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为了在“中央编译局”评上“副研究员”,当上“处长”,造谣杜撰出“南王(指“中央研究室副主任”王沪宁)北俞(指他自己)”的说法,抬高自己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实际上,他在国内学术界(包括他所学的“政治学”专业界)根本没有学术地位,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人提过“南王北俞”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学术上益发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把自己说成是政治学的“泰斗”、“前辈”(他在编译局的绰号就是“先辈”或“鱼鲜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国外社会主义”的“专家”。然而他的文章却经常因“常识错误”等理由被退稿,洋相百出,贻笑大方。每到这种时候,他便同人家吵架直至整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俞可平到“中央编译局”已十二年,没有发表出一篇有影响的、或者哪怕让人留有点印象的作品,编书挣主编费的事情倒是干了不少,而后者又成了他“著作等身”、“著名学者”的证明。十多年看下来,可以说俞可平是从人品上不老实,发展到学术上不老实和政治上不老实,说到底是因为政治上野心太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取得了“国家教委”的出国名额,到德国学习,便用中国的事骗外国人,又用外国的事骗中国人。他在德国吹自己是“江泽民身边的主要几个政治顾问之一”,在政治上蒙骗洋人,利用洋人对他的垂青谋取利益。回国后便吹自己“国际知名学者”;他在德国不过是以“文革”的议题作了“学术交流”,便把自己吹成国外大学的“客座教授”。其实他因为在德国闹讲课费等事情,同德国人以及国内介绍人都弄得很僵,德国该大学学者来“中央编译局”时他都躲着不敢照面。而当胡锦涛当上中共那个仅次于向忠发的最次“总书记”以后,他又向国内外胡吹自己是胡锦涛的“幕僚”、“文胆”,但此时他已很臭,也骗不了什么外国人了。
值得指出的是,俞可平的这种自我吹嘘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强、幼稚好胜,也不是真的想做共产党的忠实幕僚。事实上,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脚踏两只船”:他根本不看好共产党,既要在共产党内拼命往上爬,拼命捞利益,又不放弃同海外势力勾搭,为“将来”铺好“出山”的阶梯。后一类行为被“有关方面”查过多次,“中央编译局”的“领导班子”也不是不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以后,他热衷于在香港等海外民运人物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担任编委等等,努力营造自己“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政治两面派真实面目是十分清楚的。
二、俞可平人性和政治品质都极为恶劣,见权就夺,见利就抢,妒贤忌能,整人成性。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零零一年十多年来,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可思主义研究所”就业,在那里他工于心计,玩弄权术,肆意整人,积怨很深。
为了确保自己从“副所长”升为“所长”,他用种种手法先后挤走了有可能成为竞争者的两个骨干。一个是经济学博士张春霖。张是国内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负气调往“国家经贸委”,后为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另一个是历史学博士李永全,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这两个人的综合素质都远在俞可平之上。俞用以“无法安排”为由不让借调在外的张春霖回归的办法赶走了张春霖,又用“搞小圈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气走了李永全。因不满俞可平而调走的还有银文泉博士、方朝辉博士等,其中方朝辉博士调离前愤怒控诉俞可平。
俞可平在一九九八年如愿当上“所长”后,又盯上了该所的《比较》杂志(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杂志,已办了十多年,与政府重要部门和许多企业有密切联系)。俞一次出国向《比较》索要5000美金未果(只给了他1000美金),他就开始“行动”了。为了把这个赚钱的“金盆”弄到手,他对《比较》的干部拉拉打打,分化瓦解。他以退休问题为砝码,诱迫《比较》杂志老的负责人荣敬本为他搞到了十几万美元的福特基金,然而钱到手后,他立刻就利用所谓“经济问题”搞臭荣敬本,撤了原“处长”、《比较》“编辑部主任”高新军;由于后来的“处长”、《比较》实际负责人肖梦仍然没有让他插手《比较》,他又把矛头指向肖,用各种手段整肖,试图把肖和荣都赶走,达到自己接管《比较》的目的。他甚至反过来又向高新军许愿重新安排以分化《比较》的工作人员,而高则对熟悉的同志说,他已被俞整寒了心,绝不帮他整人。
到一九九八年以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一九九四年以前的“处以上干部”基本上走的走,撤的撤,全部换上了俞可平提拔的人。不仅如此,由于当上“所长”翅膀更硬了,他还把整人的手伸到了所外。例如他把矛头指向当时主管该所工作的“副局长”李兴耕,挑动“当代所”“处以上干部”反对李,直到逼得李难以工作,主动要求退下来。原因也仅仅是在于李曾经对他的一篇关于国外社会主义的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提出过批评,实质问题是他认为李影响了他自吹的“理论权威”形像,是他当局长的障碍。
俞可平不顾前后左右地争权夺利,肆无忌惮地放手整人,终于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三、俞可平心胸极其狭隘,一味以人划线,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凡帮他上台者、吹牛拍马者,必封官。例如,“中央编译局”有名的“小倒爷”、农民出身的李惠斌,因为是他的吹牛拍马者、“铁哥们”,在几年内不仅从一个要解聘者提了“副处长”、“正处长”,而且还要提他当“副所长”,只因被群众投票否决才未实现。李惠斌以往参加“国家教委”的英文出国考试均不及格,又已十多年不接触英文、不搞专业,却在评他当正“研究员”时,让他在“中央编译局”的最后一次职称考试中得了“优”,而俞可平恰是“局评委”。相反,凡是按常识生活的正派人,必受打击扼制。例如,“副所长”罗燕明长期以来忍辱负重地支持俞可平的工作,甚至对他都有点卑躬屈膝,可是为了给李惠斌腾位子,俞到处散布说:罗“老眼昏花、糊里糊涂、身体不好”,直至把罗逼得调离“中央编译局”,而同期《比较》杂志的实际负责人肖梦也不得不选择了彻底离开。
尤其是对考察他当“所长”时没有支持他的本所人员,一个都不放过。由于当时反对意见太大,俞被调去“中央党校”学习,缓冲半年后才任职。任命时的说法是“给年轻干部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然而俞当上“所长”后,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疯狂报复。在职称、提干、出国、评优、分房等所有的利益问题上,俞都紧紧地把持着小圈子的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所里搞“俞天下”,缺乏基本的公正,以至引起所内广泛不满甚至仇恨。对于已经不在位的领导者,他还是严加防范,处处打击扼制,视为头号敌人,甚至对每一个新来的同志都进行“以人划线”教育,搞得一些人连正面接触都不敢。俞可平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搞成了全“中央编译局”人际关系最紧张、人员流动最大、干部队伍最不稳定、内在矛盾最深刻的单位,却还在全局到处吹牛,夸大“当代所”的政绩,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
不少与俞可平同年到“中央编译局”工作(还有的就在同一办公室),亲眼看着这样一个政治品质恶劣、人性卑鄙的小人,在“中央编译局”一天天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尽管这个坏人不断受到群众的抵制,却也能一再“涉险过关”。人们深感到这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中央编译局”的主流领导层在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支持他这样的坏人;俞可平的不可救药是“中央编译局”这个“基本面”很差的单位扶植、包庇和纵容的结果,是在一块毒沼地里培育出来的一颗毒果子;就此而言,应当说“中央编译局”的主流领导层一直是在对社会犯罪、对历史犯罪。
参考附件:俞可平自己组织发表的吹嘘文章两篇,其中既反映出对自我造神的无耻的热衷和执著,也反映出对“智囊”、“文胆”等说造谣破产以后的惶恐、掩饰、诡辩和开脱。
文章之一:俞可平“文胆”辨析
载《瞭望东方周刊》;http://www.sina.com.cn2003年12月08日10:41转载
《瞭望东方》记者张修智/北京报道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过渡
俞可平是近来颇受海内外关注的人物。他的“善治之策DOUBLE_QUOTATION”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
从治理到善治
由于俞可平在英国出席一个国际会议,无法取得联系,《瞭望东方》采访了著名政治学者、原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今年81岁的赵教授,是俞可平的博士导师,在中国政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作为弟子,俞可平与其过从甚密。
他说,俞任副局长的中央编译局,作为中央的直属机构,常常会接到上面布置的一些调研工作,这对于俞的学术研究很有好处。
赵宝煦教授对俞的评价是:“人很好,非常用功,非常勤快,非常活跃。”俞在一九八八年博士论文答辩后,北大政治学系已经准备让俞留校任教,但答辩委员会中的一位来自中央编译局的先生非常欣赏俞可平,竭力推荐俞可平到编译局工作。“北大当时住房条件很差。俞可平到编译局后不久,就住上了三居室的房子。”
对于俞可平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的评价是:“思路开阔,非常高产,既追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又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这也是《瞭望东方》采访的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对俞学术风格的共同评价。
对国际社科前沿学术问题的敏锐捕捉,是俞可平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一九九五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在新的治理定义中,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必须是政府。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统治是政府运用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在国内目前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三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在这个领域里的开拓之功可见一斑。
俞可平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善治的八个分析性标准: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秩序、稳定。一位八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过的知名学者认为,作为一位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俞的学术立场及民主政治理念是相当清晰的。“他主张党内民主,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这位学者说。
“增量民主”
八月二十三日,俞可平发起的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这是中国首家对政府创新实践进行研究、评估和奖励的非盈利性学术机构。
该中心参与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学术机构对政府进行评价的奖项。今年三月十八日,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在该中心(当时还在筹备中)主持下,在北京梅地亚宾馆颁发。这次活动没有邀请记者,一切都在低调中进行。
会后,该中心把这次评奖活动和部分获奖的地方项目,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看罢这本书之后,专门给俞可平写了一封信,说这本六十页的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沃尔芬森的感慨是有其深意的。
国外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政治改革领域则推进迟缓。
俞可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变迁已经发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个进展是: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式宣布,党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机关。
公民社会开始出现。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这些民间组织正在对中国的民主与治理发生重大的影响。
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政企不分是传统的绝对一元化政治模式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的不复存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绝对一元化政治体制。
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这直接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热烈讨论。俞可平进而提出了“增量政治改革”与“增量民主”的概念。他说,这两个概念包括三层基本意义。
首先,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无须完全地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
其次,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
其三,改革和民主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
在谈增量民主的概念时,俞可平对民主程序的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一部规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仅有规定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而没有实际的措施,这些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对于现实的民主政治而言,宪法和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以及实现这些条文的实际程序。”
显然,俞可平并不满足于书斋里坐而论道,他同时也在积极地用行动去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在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网站首页上,俞可平写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对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应当是民主、开拓和创新的政府。”基于这个理念,俞可平领导的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
该奖的评选工作以严格和公正而备受好评。首先是资金来源透明,不向参评者收取一分钱,“是评奖而不是卖奖”;其次是程序公正并能被认真执行。
一些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在获奖之后扩大了影响,例如,湖北广水市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办法,后来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而自贵阳市人大旁听制度和南京下关区政务超市获奖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推出了类似做法。
“当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创新还与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有相当的距离。总体上看,创新还是少数,需要鼓励,这正是我们设立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目的。”俞可平曾对媒体这样表达过设立该奖的意义。
“文胆”辨析
近年来,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文胆”,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中,海内外一些人士普遍给予积极、正面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建议,解读可以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来展开,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是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中不曾冷却的话题。
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皮毛论”最为经典。他说,知识分子是附在皮上的毛,他们没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中,知识分子始终难以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和价值。
对于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俞可平曾做过深入研究。在《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年)》一文中,他这样概括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简单地说,就是游魂无处归。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像一个游魂,飘浮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这种判断,也是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主流声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地位的认知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