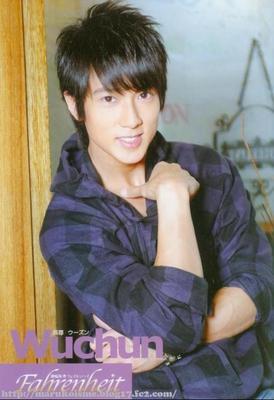不惧一死的瞿秋白为何写下《多余的话》?
如果不写那些话,他的烈士头像光芒万丈,作为中国红色革命两度最高领导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写了——宁可被视为“叛徒”而“归罪”,不愿被人视为“英雄”而钦佩。
对共产党人而言,他当然不是叛徒,因为他没有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贪生怕死出卖战友;然而,他也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维埃战士,因为他在狱中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做了深刻的“罪己”解剖。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这不是一个历史谜团,而是一个从事苏维埃革命的“纯文人”真实告白。比较这个翻译家的众多译作,这恐怕是他唯一可以传世的原创巨作。
本月,我是参读金雁先生的新作《倒转的红轮:苏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后,合读瞿秋白的这本遗作的。对比苏俄知识分子分子的心路历程,本国现代革命史大人物瞿秋白的啼血告别更令我思痛。
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再到别尔嘉耶夫,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及纯文人为何在苏维埃红色革命中,纷纷“掉队”?找到这个历史问题的真实答案,或许可以给今天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各路志士,以更多求真务实的思想突破。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于国民党监狱中,1935年5月23日完成,此书写就不到一个月,即6月18日他就被处以枪决。国共两党的史料都记述承认:瞿秋白临刑时“谈笑自若,神色无异”。还镇定地自选行刑地,非常洒脱说了句“此地甚好”,可谓不惧一死的勇士。
然而,不惧一死的他,为什么坚持写下后世争议的心灵独白呢?他不知道,这本书会给自己“英勇牺牲”的光荣史蒙上“污点”、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不必要的麻烦吗?
读过《多余的话》的人们,有各种不同评价。文革期间,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将其列为“叛徒自白”,而轻贱瞿秋白。而今天的我读后感是:因为此书,对瞿秋白平添敬意,这种敬意比起他的“革命事迹”来,更有历史生命力。
此书开头,瞿秋白开宗明义“不要学我”——“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在很多人包括瞿秋白自己也不否认,在两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只是个名义领袖,所以“一直在演戏”“很滑稽”。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遥控着中共最高权力,当时派到瞿秋白身边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苏俄人米夫,而米夫的背后,是斯大林。书生意气的瞿秋白不会真心佩服这个对中国问题上不懂装懂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不快。瞿秋白在忍无可忍书生气发作时,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种请求自然不会获得斯大林应允,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开始打击瞿秋白,采取“以华制华”手段,选中自己中山大学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取代瞿秋白。
此时的瞿秋白,早已厌倦了这种扭曲人性、戴着假面具表演的政治。他承认和共产国际代言人、王明博古这些人产生了“疏离感”——“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从瞿秋白的最后命运来看,说他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不为过。1934年10月,红军决定“长征”,共产国际代言人不让他随军。而让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继续“战斗”,瞿秋白“不得不留”。党内有话语权、良知敢言的仅有张闻天为瞿秋白请命,结果因“博古反对”无力回天。就这样,把一个曾经的领导、一个手无缚鸡之力、高度近视,肺疾咯血的书生,丢给了压境的国民党大军。被国民党军队抓进监狱后,瞿秋白反倒在精神上彻底解脱了。他要撕掉假面具、痛快休息——“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也许为了突出“滑稽剧要闭幕”的滑稽色彩,瞿秋白在书的最后写下了似乎不着边际、又“十分小资”的那句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最后这句话,与清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临刑表现好有一比(死前对狱卒言: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但与革命烈士的情操似乎格格不入。这就是瞿秋白的可爱之处:率真之书生气。早期共产党人,拥有书生气的不止瞿一人,譬如瞿的前任陈独秀,更是率真敢言,但是他们最后都因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格格不入而成为“掉队者”。
当然,虽然都是率真的书生,但陈独秀与瞿秋白还是有着明显区别。陈独秀在任时率真敢言,敢作敢为;而瞿秋白在任时率真不敢言,软弱盲从。乃至自己都觉得自己取得的是“戏子的成绩”。
从陈独秀、瞿秋白的人生最后时刻的表现来说,他们都是有气节的人,纵然对自己的政治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芥蒂,但绝不突破出卖战友的底线,所以没有达到国民党魁蒋介石“变节”要求,故不见容于本党,也不见容于敌党。难免被弃或一死。
瞿秋白在被捕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言者抛弃的人,而在他牺牲后,地位却又陡然回升,得到烈士哀荣——很想问问当年整瞿的极左,你们所搞的政治是需要对手“必须死”吗?
与陈独秀、瞿秋白同样命运的,不止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大致同时代,苏俄也有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别尔嘉耶夫,写过著名《自由的哲学》的他,曾向往马克思主义。祝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并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21年,他因一起莫须有的案件而被捕,后被释放。次年夏天,他再度被捕,并被驱逐出境,理由是别尔嘉耶夫“已经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在离开祖国时,他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苏俄境内出现,将被就地正法。最后,别尔嘉耶夫客死他乡。
关于陈独秀、瞿秋白和别尔嘉耶夫这些知识分子的“掉队”,队内的一些人喜欢用“动摇革命信念”字眼来形容,斯大林们更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目标是高尚的话,手段就可以忽略不计,恶不能用善去反对,为了善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用道德衡量革命者。
但是,当红色革命成功后,瞿秋白《多余的话》里的文人困惑并没有解决,经历过十年浩劫“脱裤子、割尾巴”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对远离人道、“不用道德衡量的革命”心有余悸。苏联解体后,人文知识分子亦加剧————了这种思考,很多人要求把道德应该回到政治文明原本的意义上。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年轻人,是何等愚不可及”。
正义可以伪装,野蛮无法隐藏,一切扭曲人性的事物终究令人厌倦、引人警醒。《多余的话》最大价值,在于人性的回归,让人性与道德回到政治应有层面,只有文明政治才能创造文明世界,此番要义,于昨于今,一点都不多余。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