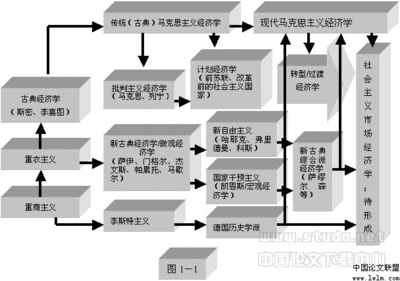一
“恒彧斋鬼话”才写到第二篇,竟然就要用于赶跑本质为鬼的新语丝著名网友太蔟(音“簇”),实在并不出乎我的意料。这只鬼的鬼性实在是太厉害了,厉害到让人看了它的任何发言,都有想吐它一脸唾沫的冲动(中国古代传说:冲鬼吐唾沫,可以制止它继续作恶)。
我和太蔟的交恶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很多人把我和他都视为“新语丝网友”,这当然没错。然而如果以为新语丝网友是铁板一块的集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政治观点,至少可以把新语丝网友分成右派和非右派两大阵营。太蔟是右派阵营的,我自然是非右派阵营的。
起先我以为持有非右派观点、但又赞同方舟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的人是极少数,但上了新浪微博,才知道并不算极少数,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替他们发声,他们自己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愿主动发声罢了。说实在的,我并不介意当这些非右派新语丝网友的志愿发言人,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是事实,不是价值,呵呵):你说的话有多少说服力,有多少听众,很大程度上的确取决于你的身份。既然连极度仇视我的右派理科流氓——“科学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我是“高材生”,那如果我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替志同道合的朋友说说话,我当然当仁不让了。事实上,我甚至以为这是我的一种义务。
我和太蔟以前交恶的原因,我在《凉秋九月,再干太蔟》一文里面写得很清楚,这里不多说。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已经提到了太蔟的两个身份: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这不是我自己查出来的,这是太蔟自己在一本翻译的儿童科普中透露的(这是他到目前为止仅出的科普图书,可惜还不是他自己写的)。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为自己查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而遗憾,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终于用这两个信息,把他的真实身份查出来了。查出来之后,我在新浪微博上说,如果他不再攻击我,我愿意替他保守秘密。
此后太蔟的确并未攻击我(不过也可能是我还没给他留够时间),但是很不幸,“复旦18驴”事件之后,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发言实在是恶心到我了,让我开始反思我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宽宏大量。反思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不赶快揭露他的真实身份,那么我是有罪的。
二
在介绍太蔟教授的真实身份前,先介绍一下“复旦18驴”事件,这也是我在这篇“鬼话”里要讲给人听的“人话”之一。
12月11日晨,复旦大学登山探险协会(以下简称“登协”)纠集了一支18人的登山队(其中10人为在校学生,4人为复旦毕业生,4人为和复旦无关的驴友;18人中有8人为女性),在领队侯盼的率领下,逃票进入黄山风景区东部的未开发区(也就是严禁游客私自进入的地区)。当晚在黄山未开发区扎营。次日中午,黄山下起大雨,因队伍中唯一的GPS进水,登山队迷失了方向。下午4时多,天色变暗,并起了大雾,登山队被彻底困在山中。他们开始拨打电话向黄山派出所求救,但因为雨夜上黄山非常危险,黄山派出所最终拒绝出警。
在这种情况下,队伍中一个叫施承祖的27岁青年给自己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二姨父发了求助短信。这条短信最终惊动了上海和黄山两地的领导。黄山方面听说受困的是复旦大学的天之骄子,连市长都坐不住了,亲自带队赶赴景区指挥救援。在领导的命令下,黄山派出所组织了230多人的救援队伍,以“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接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措施”冒雨进山搜救复旦登协登山队。最终,其中一支队伍通过6个多小时的搜救,在13日凌晨2时多找到了受困者,并连夜下撤。在下撤途中,民警张宁海不幸坠落悬崖牺牲。听说有人坠崖之后,领队侯盼坚决拒绝继续下山,于是50多人在山上的临时营地露营一晚,于13日上午10时出山。
对这样的事情怎么评价,当然取决于各人的价值观。我的评价是:学生和政府都有错,但主要的错在学生。第一,没有足够的水平,就不要“探险”,给别人添乱。第二,逃票故意进入危险的非开放区,本来就是违规行为。第三,如果没有施承祖发短信,也不可能出现政府勒令派出所连夜冒险搜救的事情。这第三点最重要,因为施承祖在给自己“影响很大”的二姨父发短信的时候,没有人表示劝阻(他是用另一个人的手机发的),说明这些人本来就愿意利用复旦大学学生的身份搞特殊。
我们再来看看太蔟教授是怎么评价的:
复旦登山队的事,令人感叹中国道德舆论的可怕。如果那位民警没有牺牲,那将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人类几个鲁莽但富有探险精神的年轻成员把自己弄到尴尬的境地,人类其他成员友情相救。可惜可惜。一点疑问,黄山附近的警察是否受过山地救援的专业训练,有无相关专业器材?那位民警可否不牺牲呢?
对这种说好听点是极端个人主义、说难听点是犯贱的评论,我只想说一点:年轻可以原谅(我本人并不特别苛责那18名驴友中的多数人),但原谅的前提是承认错误。能把错误粉饰成“鲁莽但富有探险精神”,这还真是我希望能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道德舆论”不能容忍的。受不了的话,滚出中国去。
三
“复旦18驴”事件之所以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更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事件本身中“18驴”的错误,而是事后复旦学生和校友的无耻辩护。本来我不想攻击复旦大学本身,但是现在我的确好奇:这个学校的校风是不是本来就不正?
当然,对其中大部分的弱智言论(比如有人指责“最不负责任的是警察”),我看到后顶多是付之一哂,觉得不值得理睬。唯有复旦大学登协的一个前会长在新浪微博上说的一段话把我激怒了。她是这么说的(话中的别字我没改):
看到网上对复旦十八人不负责的登山行为各种指责,作为登协第二任会长,内心很纠结,高风险的户外活动每次出行都有太多的不确定。在野外迷路遇到各种断水断粮困境,一次次克服和超越自我,成为远行的强大动力。媒体们不要忘了北大山鹰社,清华登山队多少次全军覆末葬身雪山,纠着复旦登山事故不放算什么。
这是对北大山鹰社和清华山野协会的污蔑。且不说清华山野协会的正式活动从未出过事、死过人(山野协会曾经有一个叫黄德的会员,2004年在贵州六盘水攀岩时失足跌死,但他是以个人身份前往的,那次攀岩并不是山野协会组织的活动),北大山鹰社也只出过两次事,一次是1999年攀登四川岷山雪宝顶时,一位叫周慧霞的女生坠崖遇难,一次是2002年8月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希夏邦马峰时,林礼清等5人遭遇雪崩身亡。仅仅两次事故,在这位“登协第二任会长”口中,就成了“多少次”,真是恬不知耻。而且,这两次事故中也没有哪一次是“全军覆没”。再说,北大死人是死自己人,也没有连累别人。最后,雪宝顶和希夏邦马峰都是雪山(特别是希夏邦马峰还是一座海拔超过了8000米的山峰),复旦大学登协爬的可是最高峰海拔也只有1864米的黄山啊!这种白痴水平,也好意思和我们北大的山鹰社和清华山野协会相提并论?
话说北大山鹰社后一次山难发生时,我正在北大念大二,在北大的校内论坛未名BBS上激烈批评了山鹰社的轻举妄动。因为在登山界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区最安全的登山季节是春天的5月份,其次是秋天的10月份。夏天的8月份降雪较多,极易诱发雪崩。但是现在看到复旦登协的贱人(还是女性呢!)贱语, 我一下子觉得,山鹰社那次山难倒真的只是“鲁莽但富有探险精神”了。
四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言论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右派言论一枝独大的局面才开始慢慢得到扭转。王小东先生说,这和代际交替有很大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逆向种族主义”招摇过市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那批人中,右派数量很多是必然的;而等到在经济腾飞期的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之后,右派所占的比重下降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太蔟教授的生平,也就可以理解很多问题了。
太蔟,真名孙文俊,男,东北人,1966年5月生,1983年以17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标准的“八@九一代”(不过,他不幸还是我的校友,这让我情何以堪啊)。1990年在北大读完硕士之后(这一点是我的猜测,待考)考取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96年毕业,获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raystructural investigations of chain ordered lipid bilayers.我大概翻译一下,估计翻得不对,大家纠正:《链状排列的脂类双分子层的X射线结构研究》。
毕业之后,太蔟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然后便和我在《恒彧斋鬼话(1)》中揭批的不良媒体人王以超一样,彻底放弃了专业。当时在美国的很多理科生最终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方兴未艾的IT业中,为的是挣大钱,当“中产阶级”。太蔟也不例外,跑到硅谷当起高级IT民工去了。
据其本人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透露,他于2002年应聘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并取得成功。然而,他放弃生物物理学本行多年,去哈工大理学院当然绝无可能。以他半路出家搞IT的水平,去哈工大软件学院也绝无可能。所以他去的是哈工大管理学院,研究的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知识管理”。我笑了:这倒底是理科还是文科呢?
据说他讲的课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可惜,至今都没有评上博导。有一位朋友告诉我,2002-2003年间,正是国内大学开始向“海归”抛出橄榄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海归”要获取教授职称是很容易的,可是到现在都评不上博导,那就比较差劲了。另外,据可靠消息透露,太蔟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所以他在新浪微博填写所在地时,写的是“海外美国”)。
除了上面这些严肃的信息,我还从网上搜到了一则八卦,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据说太蔟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还会说法语,会弹钢琴,写一手好文章,把一个哈工大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的小姑娘迷得要死,说她会的他居然都会,她现在连崇拜他都不想,因为崇拜的感觉太难受了。
当然,我手头还有太蔟教授的照片(自然也是从网上搜来的),如下。平心而论,还算有点帅,怪不得能把人家小姑娘迷得要死。不过据说在近照上已经是白发斑斑了。
五
行文至此,简单解释一下我是怎么了解到太蔟的真实身份的,供大家参考:
首先,太蔟自称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那好,我们可以到ProQuest数据库(国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数据库)去按这个条件来搜,一共搜出来16条记录。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用每一篇论文的作者英文姓名,加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英文名HarbinInstitute ofTechnology,到谷歌上去搜,于是就搜出来了。当然,我的实际搜索过程比这个曲折得多,绕了不少弯路。这个用英文姓名加上哈工大英文校名来搜的办法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上面透露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来自网上的公开消息。比如太蔟2002年到哈工大,就是来自他在新语丝读书论坛发的一篇帖子:
谈到“三个代表”
送交者: taicu 于 2003-03-03 20:11:59:
去年“毅然”期间,曾与一位院长(看咱身价多高!)同桌腐败,席间谈到时事,“三个代表”的话题便冒了出来。院长问我:“你知道‘三个代表’么?”我说:“略知一二。”他问:“怎么解?”我说:“不就是些政治口号么。我没仔细琢磨过。”他说:“脱节了不是!共产党的口号背后是有深刻的含意的,不是随便说出来玩的。”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十六大不是要召开了么?要修改党章。‘三个代表’是为之做思想准备的。你知道现在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么?”我说:“以前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么?工农兵。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变了么?”他说:“与时俱进啦。现在不要无产阶级了,要的是‘官学商’。‘三个代表’就是代表这三个。”我说:“请细解。”他说:“‘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是‘商’,便是大款小款、资本家、企业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便是‘学’,也就是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教授、学者、艺术家、文学家,全在这里啦;‘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便是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了,这些官们不正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么?”
他最后说:“你知道,想在中国做生意,必须要在‘官学商’三条路上都有关系,都搞得通。共产党不傻,知道只要牢牢抓住这三条线,便可立于不败之地。‘三个代表’深入人心后,按之修改党章,再吸收‘官学商’入党,不就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了么?”
再如太蔟把哈工大一个小姑娘迷得要死,这八卦搜起来就更简单了,用“太蔟”加上“哈工大”在百度搜,第一页就有(不过只有网页快照能看),原文是: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发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会议的日程安排和演讲者介绍。Professor Sun的简历是这样写的:He gothis B.S. degree in Beijing University, PhD in Carnegie-MellonUniversity, and w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UC-Berkeley. Dr. Sunhad?worked in IT industry in SiliconValley...没想到他还读过博士后,我又问了师姐,终于意识到原来他比我所了解的还要牛X。我以前说过,这种短暂的相处是最好的,如果我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时间长了,随着更深的了解,也许我会发现他比较爱生气,也许我就不会这么崇拜他了,也许他也不会这么喜欢我了。可是现在,我很不幸地发现我会的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包括我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和我一知半解的东西,而且每一样都比我强。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写一手好文章,他会弹钢琴,还会说法语。随着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不但没开始发现他的不好,还越来越发现他的牛X,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去崇拜他了,因为这种感觉实在太令人难受了。难道我这颗小猩猩就这样被埋没了?
有朋友羡慕我的搜索技巧,我想说,没什么可羡慕的,我愿意授人以渔。你看,人肉就是这么简单。
六
鲁迅在杂文集《伪自由书》的《前记》中说,他的杂文常常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我非常欣赏,而且自己在写杂文的时候也有意向迅翁学习。
如果说我的上一篇“鬼话”是用王以超作为凤凰男式右派理科媒体小资的代表,那么这一篇“鬼话”就是用孙文俊作为“八@九一代”中“双重用脚投票”的“香蕉人”知识分子的代表。所谓“双重用脚投票”,就是先选择离开中国,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完成第一次的“用脚投票”,再选择离开他的新祖国,回到中国来挣钱,挣了钱之后晚年再回新祖国安度残生,完成第二次的“用脚投票”。所谓“香蕉人”,就是黄皮白心、意识形态上完全向西方靠拢的华裔。
这种人里面,很多是很聪明的,只可惜生错了时代。当然,他们自己肯定不会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真正有志于建设中国的人来说,他们首先只能让我们怜悯。当然,对于孙文俊这样的美国人来说,不妨利用他一下,让他继续在哈工大教书。等他老了,就让他回美国去好了。反正他消耗的是美国的福利,这就给中国省下了福利。要是他留在中国,那还真不知道要在这种香蕉人教授身上花多少冤枉钱呢。
当然,这样的做法有可操作性的前提是,他和其他“科学主义者”鼓吹的那一套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中国再也不能兴风作浪。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
2010.12.22-23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