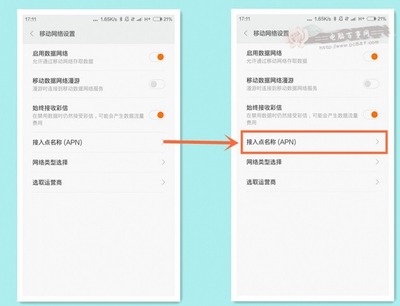心平气和地回顾袁世凯帝制的过程,研究其产生、出笼、哗变,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所做的一切,并不完全出于个人偶然的动机或者私心,这样的结果,是由当时还占据支配地位的封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可以说,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有一个不灭的皇帝梦。袁世凯也是如此。只不过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凯来说,皇帝的梦想指日可待,似乎只要愿意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度,由皇权转入民主代议制度,这当中的过程,绝非只是废除一个皇帝,或者三五年数十年就可以改变的。它甚至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消除习惯和影响。中华民国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当然大快人心。但同时,自然而然地,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会遇到帝制沉没后的很多问题——中国运转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有相应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以及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道德伦理、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现在,皇帝垮台了,那种支离破碎的体系却有强大的惯性,依旧左右很多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天子消失之后,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也仿佛乱了套似的。很快,人们变得不习惯了,不习惯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生活。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以选举方式推举出的国家元首,总是缺少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让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经济的衰败,道德的沦丧,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所引起的人心浮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想而知。让普通民众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乱——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时更为败坏,儒学和道德变得松弛,人们在挣脱封建纲常礼教之后,变得无所适从,社会在短时间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众多没有安全感,对于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竞相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或者沉湎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在他们看来,旧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普通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新建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开张所挂出的一面空招牌,不仅店铺内什么都没变,而且社会秩序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涌动一种渴望,那就是,中国急需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为特征的复辟派应运而生了。袁世凯,这个曾经的激进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后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复辟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新秩序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的时候,重新恢复旧秩序,以稳定社会。一开始,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复辟者,是试图从道德的寻觅中复古的。面对纲常崩溃的局面,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强烈的尊孔复古思潮开始反弹。这些民间组织试图以扶翼圣道为宗旨,力挽当时的道德颓势。袁世凯对于秩序的维护自然持赞同态度,他不仅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亲自参加了好几次祭孔仪式,以示支持。很快,由恢复孔孟之道为宗旨的活动开始延伸——以康有为、劳乃宣为首的孔会,转变成了拥清复辟派,他们开始活动,鼓吹还政于清,进行立宪。“复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但在复辟的对象上,人们表现得并不一样。恢复满族的皇权地位,显然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所不愿意的。虽然大多数人对于拥护满清不感兴趣,但对于帝制本身,依旧有很深的情结。人们都在激越地探讨重新立一个皇帝的可能性。慢慢地,这股潮流越来越大,整个社会一片呼唤帝制之声。人们都把民国之初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问题,归结为没有绝对权威的缘故。中国文化一直是习惯于向后看的,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于过去的时光进行缅怀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也从这种越来越泛滥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鸣。袁世凯本来就一直对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松散局面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共和制的办事拖沓、扯皮忍无可忍。在习惯于专制和集权的袁世凯看来,这种国体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节骨眼上,根本就无法凝聚人心,无法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形成推动力。并且,当时的状态是,各省名义上挥舞着共和制的旗号,但在暗地里,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国当回事。在袁世凯看来,中央政府虽然号称中央,但对于南方各省各自为政,根本控制不了,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诸如人权、财政权、军政权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纵,已很难控制。袁世凯一直不得过问,也不敢过问。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安插人员。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东北,袁才能够行使职权,安排人事。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旧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丰满,不太听招呼了。一个类似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初具雏形。
让袁世凯最为头痛的,是共和国的经济受困于各省的各自为政:据财政部的报告,自民国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实交纳到中央的款项才260万元,而且,这些款项基本上还是北洋集团势力所及的几省所交纳的。不交纳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税收、田赋,用于养兵养政;而吃亏最大的是中央。这同样也说明中央集权的必要。袁世凯当然把这一切归罪于共和制。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开始涌动恢复帝制的愿望。当然,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让它露出一点头来,他担心的是帝制恢复所引起的震动。作为一个老辣的职业政客,袁世凯当然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一项改变的成功,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不可。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一个强大的信号,大战期间,原先被压抑了的各种矛盾,仿佛点燃了导火线似的,变得疯狂起来。一些人开始对民国以来的政局进行反思,并公开发表政见。原先一直蠢蠢欲动的君主与民主之争,一下子成为热门问题。
拥袁世凯为帝,最开始,是湖湘才子杨度奠定理论根基的。杨度曾拜湖湘大儒王闿运为师,后来东渡日本学习政法,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曾经劝杨度参加革命,特立独行的杨度拒绝了。清末时袁世凯倡导立宪,一直视杨度为智囊,亲自题匾称杨度为“旷代逸才”。“五大臣”出洋考察报告,就是由杨度和梁启超共同起草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确立民主共和,杨度一直持有异议。1915年4月,杨度完成论著《君宪救国论》,该文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主立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论述总--统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宪。杨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亡国而已。在杨度看来,共和国必须有很深的民主自由传统,一般意义的共和国,经济强盛,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比如美国和法国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往往会导致政局不稳。至于君主立宪国家,一般都有服从和等级的传统;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来说军事实力比较强大,比如英国德国。杨度还根据中国国民认识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人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因此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以杨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局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仅凭血统继承,这样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变更纷争。很多国家因为共和制所产生的纷争,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此联彼抗,会引起全国性的动荡。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国乘机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离间,那么就会出现如此局面:一是各国瓜分中国;二是各国出兵代中国平乱,最后也是亡国。所以,杨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君主立宪制是救亡图强的最佳方案。
应该说,杨度这篇论述君主立宪制的文章,既考虑到了中国国情,也考虑到了文化传统,并且列举了中国实行共和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单纯从学理角度进行探讨,本来也无可厚非。但这篇文章在中国已经转入民主共和国体的情况下抛出,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引起了一片动荡。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具体实行什么国体,是否共和与立宪,与其说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所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时势的产物。也许,在中国没有选择共和制之前,君主立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中国既然已经选择了共和的道路,那么,这个庞大的古国在负重前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容易,也无法再掉头走回头路了。历史前行中的反复,很容易授人以柄,并引发混乱。这样的情况,就如同一辆负重前行的车辆一样,既然已经行驶了,而且提速度了,又突然转向,那种巨大的离心力,是很容易翻车出事的。这种改弦更张所造成的巨大的后果,是杨度没有考虑到的。
杨度完成这一篇鸿文之后,一方面呈送袁世凯,另一方面,又在军政各界中广为散发,继而又在报章上公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共鸣。袁世凯在读到了杨度的这一篇文章之后,深有感触,一方面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问题,让袁世凯大伤脑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凯一直有君主立宪的情结,对于这种国体相对亲切和熟悉。袁世凯最崇尚的,是德国的君主政治制度。在他看来,中国和德国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对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很少给予考虑。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与它拥有强大专制力量的立宪政治制度有关。只有相对专制的制度,才能保证一个孱弱的国家,去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建设迅速走向富强。
无独有偶,如果说杨度的观点代表一部分国人观点的话,那么,同样在这个夏天,美国人古德诺阐述的理论,似乎更能代表国际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对袁世凯更具参考价值。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政顾问、极富名望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应邀到中国考察一番后,根据考察成果写成《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发表在《亚细亚报》上。古德诺的这篇文章,从纯学理、法理出发,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一进行了评述。主要观点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因为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古德诺所言,也是考察欧美各国的实际情形后得出的结论。在论及中国国体时,古德诺论证道,中国有数千年的帝制,大多数人民智识不高,也没有参政习惯。四年前中国由封建专制一举变为共和,显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难有良好结果。古德诺认为,君主国体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这点不容怀疑。以中国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及其与外国列强的关系状况,采取君主制比采取共和更有利国家的发展。与杨度的看法一致,古德诺认为,君主制还可使中国政治趋于稳定,避免在总统继承问题上酿成祸乱,因为中国人不太懂民主,很难保证在民主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如果这样,中国就会有分裂的危险。如果要保持国家独立,中国必须发展立宪政府。
与杨度、古德诺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认为一个新式国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规则运行的国会;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小学教育之发达。有贺长雄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三大要素,因此还是以“旧式”帝制为好。接着,有贺长雄又写了《日本立宪而强》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如果实行君主立宪,一定会很快强大起来。杨度、古德诺以及有贺长雄之流的鼓与呼,很让中国当时一批政要,尤其让遗老遗少以及旧式知识分子找到了共鸣。很多人从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出发,以为国体一变,只要中国出现皇帝,有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多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当中,最积极鼓吹和响应的,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袁克定这时候已从德国疗伤归来,一直向袁世凯大肆鼓吹德国的先进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为世袭,袁世凯如果当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动下,由杨度领衔,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同发起成立了“筹安会”。时称“六君子”。在这六个人当中,除了杨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刘师培和严复是学术泰斗;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会的骨干,辛亥革命时都是冲锋陷阵的人物,曾经当过省都督。在他们当中,严复的思想较有代表性——在严复看来,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中国最好还是保留帝制,但应进行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找平衡点;况且,民智的浅深与君权的轻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开化的情况下,仓猝实行西方民主,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激变。个性怪戾的严复对袁世凯也有“一针见血”的评价,在严复看来,袁世凯充其量只是帝制时代一个能干的总督或者巡抚,如果要带领国家与列强相抗衡,则太缺乏科学和哲学知识,也太无世界眼光;但严复又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当下中国唯一的强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权,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强国的措施,至少也能尽快结束让人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制止中国走向分裂。
“筹安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一时情感,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后患无穷,也“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止的事例,证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实际。宣言同时表明,筹安会的宗旨,就是以学术团体,“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筹安会”开始的宗旨是对帝制进行单纯的理论探索,但随着事态的进展,很快就发展成为帝制摇旗呐喊的组织了。筹安会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随后,筹安会组织了会员进行国体投票,投票的结果自然是赞成帝制。接着,筹安会发出第二次宣言,准备组织各界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
恢复帝制浪潮就这样越演越烈。在这种形势下,参政院开会,研究处理公民请愿问题。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代表袁世凯发表书面讲话,声称:“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种吞吞吐吐的表态,对于变更国体态度不明,似乎既是赞成又是反对。不过弦外之音显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国人民硬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话,他也会尊重和服从国民的意愿。
袁世凯的半推半就,明显地就是怂恿人们继续努力。人们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谏”了。粤系首领、公府幕僚长梁士诒亲自领头发起和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会长为沈云霈(梁士诒亲信),副会长为蒙古亲王那彦图以及袁世凯的表亲张镇芳。该组织很快成为帝制运动的指挥中心。局面已变得不可控制了,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这当中有将军府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还有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值得一提的,在将军府请愿团中,第一个在赞成帝制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是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以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君主制!
面对如火如荼的请愿浪潮,袁世凯很难保持冷静。最让袁世凯感到压力的,是各地将军和护军使的联合劝进文,在劝进书上签字的,都是各地手握重兵的将军。劝进文铮铮写道:“芝贵等实见中国国情,非毅然舍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长久之治安,是以合词密恳元首,俯仰舆情,扶植正论,使国体早得根本解决,国基早定根本之地位。”在劝进书上签字的北洋及地方军人有:云南蔡锷、广东龙济光、奉天段芝贵、河南赵倜、山东靳云鹏、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宦、江西李纯、云南唐继尧、陕西陆建章、甘肃张广建、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嗣、福建李厚基、绥远潘矩楹以及察哈尔张怀芝等。各地镇守使也不甘落后,也联合搞了一个《镇守使联合呈文》,文中更是肝脑涂地劝说袁世凯改变国体。
即使这个时候,袁世凯看起来尚未表现出对恢复帝制的迫切热情,他的态度一直摇摆暧昧,给人感觉他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袁世凯还是担心国体的改变可能会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巨大动荡。袁世凯对冯国璋等人说:“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即使改为君主,也未必比现在更好!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我对于我的儿子,即使是给他们一个排长的职务,也难以放心,怎么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给他们呢?而且自古以来,君主传不了几代之后,子孙往往遭受到不测之祸,我何苦要把这样危险的事情加于我的子孙呢!”袁世凯的这些谈话,虽然有虚伪的成分,但他绝不是一个愚蠢的笨蛋,当然知道当皇帝的风险。如果以巨大的风险作代价,仅仅换取一个皇帝的名头,这对于一个年届花甲、子孙绕膝的老人来说,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
庞杂的帝制浪潮中,只有极少数人发出不同声音。这当中最为坚决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就跟袁世凯有合作了,当时的清廷洋顾问李提穆太从日本来中国,梁启超还让李提穆太带了自己的近作给袁世凯。袁世凯很快投桃报李,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让袁世凯复出担任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虽没就任,但对袁世凯心存感激,双方也一笑泯恩仇。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盛邀梁启超回国。梁启超回国后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约法会议议员等。袁世凯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都也得到了梁启超理论和实际的支持。此后,梁启超虽然没跟袁世凯唱反调,但对袁世凯的越来越专制,也表示出警惕。袁世凯试图改变国体,梁启超是不赞成的。帝制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梁启超表示,国体的问题,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结果,既然中国已经走上共和,那么,也就不宜人为地改变;如果进行人为改变的话,那么,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遭到历史的唾弃。
应该说,梁启超的眼光是相当独到的,他对中国国体的看法,与其他诸多观点一样,清醒而独到,具有强烈的思辨精神。但梁启超的这点看法,在众人皆睡的情况下,如星光溅出,早已被周围的黑暗淹没。
与梁启超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袁克文是一个才子,也是一个名士,这个享乐主义者一向对政治若即若离,但对底层状况和知识界比较了解。帝制活动甚嚣尘上的时候,袁克文写了一首诗,讽谏袁世凯不要去做政治冒险,诗云: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翻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帝制运动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复杂的群体,就数段祺瑞、冯国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军人了。虽然袁世凯对这些手下大将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缘,但段祺瑞和冯国璋知道,袁世凯一旦称帝,皇位世袭,他们的“总统梦”便会随之破灭,就得终生俯首称臣。从内心当中,这些老部下也是有抵触的。并且,袁世凯自当政后,一直强调“军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军事,各省又另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样的方式,也让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很不感冒。冯国璋因跟袁克定关系一直不睦,对袁世凯的称帝更是心有忌讳。冯国璋在梁士诒等人的联名劝进之下,一直不表态,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段祺瑞呢,袁世凯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徐世昌当国务卿,段祺瑞心中大为不快;袁世凯设立统率办事处,回收军权,段祺瑞就更不开心了。此番袁世凯想当皇帝,更让人难以接受,段祺瑞干脆向袁世凯称病,去西山疗养。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是一场大戏正在上演的话,那么,全社会的人,都自发起参与进来了。起先是围观,然后,一个个不甘寂寞,跃跃欲试想登台表演。他们一边声讨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一边赞颂自己数千年的君主制,武断地把当今社会的一切不妥之处,都归结于没有皇帝的缘故;异口同声地强调如果一日无君,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变得层出不穷:在京城,警视厅通知全市卖元宵的人,改“元宵”为“汤圆”,并在店铺前书写“汤圆”二字,以便利市民叫买。这当中的原因是警视厅自觉接受“社会贤达”的意见,认为“元宵”音同“袁消”,于袁世凯不吉。有人为此撰写打油诗谓:
偏多忌讳触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条。
放火点灯都不管,街头莫唱卖元宵。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也传来消息,父亲袁保中墓旁,已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形的紫藤。颇信风水的袁世凯听后半信半疑,悄悄派袁克定回乡察看。袁克定到达项城后,写了一封信告知袁世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除了这件事外,各种祥瑞现象出现的消息也纷纷传到袁世凯耳中。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大星高照,呈帝王之相,经勘测研究,大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那些居于中南海的家仆们,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有一天,茶童送茶给袁世凯,袁世凯正在睡觉。茶童一不留神,将手中的上等碧玉杯打碎,这只杯子,是朝鲜国王当年送给袁世凯的。袁世凯惊醒后,茶童怕怪罪,慌忙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的大金龙。茶童这样一说,袁世凯自己也变得迷糊了。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又编出很多故事和征兆。还有一次,袁世凯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院内人声嘈杂,一个侍从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跑来——原来,在居仁堂旁边,竟然出现了一条大蛇。袁世凯忙赶过去,果然看到一条大赤蛇,通体呈深红色,正伏在假山的角落里。待袁世凯走近,那条大蛇还朝袁世凯点点头,然后顺着假山慢慢游走,钻入洞穴之中。后来有人认为这条蛇是袁克定等一帮人故意隐匿的,以骗取袁世凯相信天命。也可能,这一条蛇还真的让袁世凯动了心。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因为知识结构的原因,很少有不迷信的。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在私利与幻想中,内心已不堪重负,方寸有点乱了。袁世凯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做事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奇怪,尤其对于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当选大总统后,袁世凯特意请了一位“青鸟大师”,对即将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这位风水大师装模作样地一番测试之后,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于是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选择了个“黄道吉日”搬进了中南海。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找了一位郭姓堪舆家,专程到河南项城去观察袁氏祖坟的风水。郭某看了十处墓地后,认为第七冢袁世凯母亲的墓最不同凡响,他说:“此坟外形,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袁家人听后,皆兴奋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后,袁世凯问“东兴之运”有多少年,郭某心里没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与“阴阳二气”,乃应声说:“八二之数。”袁世凯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虚,只强调:“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袁世凯于是自言自语说:“就算是八十二年,已历三代,我也满足了。”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郭某的预言验证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袁世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边缘,就像一只飞蛾朝着火光在飞舞,越飞越急躁,越走越愚蠢。后来,袁世凯回想起当初的决判,一直觉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乱舞之中,怎么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凯的果敢、坚定甚至铁血的品质,仿佛突然被一阵风刮走,留给他的,只有软弱、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以及听之任之了。这一切,还是因为私利吧?当一个人的心房被私欲充塞之时,他的大脑肯定会凝固,政治智慧也荡然无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愚不可及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各种势力就是如此心怀鬼胎,簇拥着袁世凯,一起走向帝制的祭坛。在帝制风潮中,还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是后来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披露的:袁世凯当时最把握不住的,是日本的态度。因此,每天都要看亲日报纸《顺天时报》披露的有关信息。袁克定为了说服袁世凯称帝,暗地里纠合一班人马,生产了一个假版的《顺天时报》。假版《顺天时报》不断向袁世凯透露日本赞同中国恢复帝制的消息。有一次,袁静雪无意之中发现袁克定的阴谋后,便和袁克文商议,决定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得知后,气极败坏,把袁克定狠狠地鞭打了一顿。但这时候,袁世凯已同意恢复帝制,骑虎难下了。
9月下旬,请愿联合会发动第三次请愿,要求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从日本返回北京,捎回了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国帝制的口信。日本的表态,让袁世凯彻底放松了警惕。这个时候,袁世凯已跃跃欲试,满腹心思都是想做皇帝了。
《晚清有个袁世凯》,赵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年11月11月版,定价:25。00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