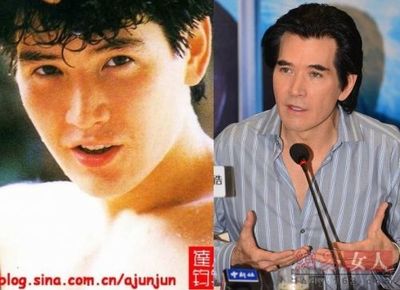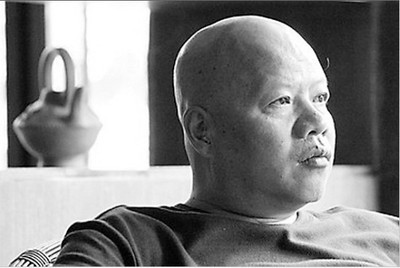
内容提要:于坚始终坚守独立的精神和艺术方向写作,他的诗关注“现场、当下、手边”,执着于事物、世界的澄明,“立场”走低,拒绝升华;出现了许多能够“看得见”的一些叙事性特征,或以物象、事象等事态因子的介入,造成一定的叙事长度和宽度,或为降低对所见事物澄明的干预程度,进行“反诗”的冷抒情;在口语化的探索中推崇语感,拒绝隐喻,为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重建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开辟了新路径。
关键词:于坚诗歌平民化事物澄明叙事学拒绝隐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土高原诗写作,中经“大学生诗歌”、“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一直到如今的“新世纪诗歌”,他始终置身于诗歌创作的潮头位置,即便是诗人们纷纷转场、诗歌最为边缘化的九十年代,仍“穷途不返”,持续写作,并在贫穷中加深了和诗歌的精神联系。显然,于坚不是一过性的“流星”,他在不同时段内均有出色的表现,虽然新世纪后其写作的有效性有所下降,但在创作黄金期留下的大量作品却依然放射着迷人的艺术之光。所以于坚诗歌理应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话题。
只是对于坚诗歌的解读非常困难。说其困难既是缘于于坚的创作几乎贯通了新时期诗歌历史全过程,时间长,跨度大,几经翻新的个性相对驳杂,不易把捉;也是缘于学术界对于坚诗歌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高出于坚诗歌文本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阐释文字,对每位后来者都构成了一种威压,再找出新的介入视角和方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更是缘于于坚诗歌的本质复杂微妙,人们评说起来歧义倍出,意见的反差判若云泥,令普通读者无所适从。我以为于坚无意间说的一段话,“我作为诗人的过程,可以说是不断地从总体话语逃亡的过程,尤其是对所谓‘当代诗歌’逃亡的过程”,⑴为人们提供了一把进入他诗歌世界的钥匙。作为一位有思想主见与理论高度的诗人,于坚时刻都在寻找着自己独立的精神和艺术方向,并且方向感越来越自觉,越明确。对他的诗不宜从技巧的圆熟和对传统的完善方面苛求,而应从反传统的个人化探索向度上去估衡。
一.“一切皆诗”:走“低”的立场与姿态
时至一九八六年,读者已日渐适应朦胧诗的审美习惯。而携着成名作《尚义街六号》正式崛起的于坚,在诗坛引起奇妙骚动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一头雾水。毕竟到朦胧诗为止,虽然从未有人具体规定过什么可以入诗,什么不能入诗,但漫长的诗教传统已在无形中培育出一种习焉不察的集体无意识:诗是相对高雅的,世间的一切存在着诗性与非诗性之分。对这种“诗必然与‘美好的事物’‘过去的事物’,与‘怀念’‘玫瑰’‘乡村’‘大自然’有关”⑵的所谓“真理”,于坚是深为反感并坚决拒绝的。所以在“他们”时期,“世界的局外人”的边缘立场和低调写作姿态,就使他从根本上漠视中心,淡化诗意,不愿以朦胧诗那种英雄式的“类的社会人”身份歌唱,用诗承载什么微言大义,而倾心于“逃离乌托邦的精神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⑶事实上,《远方的朋友》、《作品第39号》、《罗家生》等诗,也的确多以普通人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和世俗生命的的真相,传递“此岸”人生的况味,建构了自己的平民诗学。像《好多年》以众多庸常、琐碎的生活片断连缀,戏谑、反讽生命的平淡和无价值,“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七点/很多年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认识不少上海货”,流水帐、大补丁一般的惨淡扫描,同毫无雅趣的事象、漫不经心的口语搅拌,袒露了凡人生活的真本模样,把人们印象中的诗意洗涤一空。《尚义街六号》更氤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脚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晨排着长队”,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笼罩在拥挤、嘈杂又人气十足的温馨氛围中,一种粗鄙而亲切的真实被堂而皇之地凸显出来,形下的生活场景和形上的精神追求统一,吊儿郎当和正襟危坐并存,温文尔雅和歇斯底里的叫骂比邻,乃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生活灵活现的自画像,也令人觉得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饮食男女等一切事物均可入诗,诗即生活,生活即诗,于坚正是在他人看来最没诗意的日常生活中建构起鲜活的诗意空间,恢复了凡俗的生命意识和存在状态。
若说于坚的平民诗学在重建日常生活尊严过程中,对政治、文化、历史等宏大叙事和虚幻乌托邦的规避还不乏对抗性写作痕迹;九十年代后对诗歌作为“存在之舌”的本质,对诗歌“如何才能真正地脱离文化之舌,隐喻之舌,让话说出来,让话诞生”⑷的悉心参悟,则使他开始为语言去蔽、澄明事物,走向了世界本源的呈现与敞开。在这期间延续《尚义街6号》、《作品X号》时段贴近“存在”走势写下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飞行》、《啤酒瓶盖》、《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鱼》等诗中,诗人的目光仍在琐碎庸常而“无意义”的题材领域逡巡,只是边沿已不断由西南高原、日常生活向外拓展,把调整语言与存在间的关系作为创作的重头戏;并由此使写作变为对事物之上历史、文化积淀的清洗,变为返归事物与生命“原初”状态的自觉行为。或者说诗人是以外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去蔽,在对世界和事物进行着一次次的重新命名。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就具有明显的还原事物倾向。乌鸦在生活和作品中都被视为令人讨厌的丑陋、不祥意象,它会带来晦气和压抑,所以它的命运“就是从黑透的开始飞向黑透的结局/黑透就是从诞生就进入的孤独和偏见/进入无所不在的迫害和追捕……每一秒钟/都有一万个借口以光明或美的名义/朝这个代表黑暗势力的活靶开枪”。而实际上乌鸦只是普通的鸟,无“祥”与“不祥”之说,更和“黑暗势力”扯不上关系,是一代代“语言的老茧”,通过民俗、历史、社会、心理等途径把语词“乌鸦”逐渐文化化、象征化、隐喻化了,使“乌鸦”意象背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与恶名。而诗人“要说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只是一只乌鸦”,他要为乌鸦正名,还无辜的乌鸦以本来面目,并将之看做“也许是厄运当头的自我安慰”,“是永恒黑夜饲养的天鹅”,一点不害怕它被别人视为“不祥的叫喊”“那些看不见的声音”。在于坚笔下,乌鸦抖掉了各种象征、隐喻、臆想的尘埃,从形到质地被回到了它自身,而诗人为乌鸦清污、还原、正名过程中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悯和认同,既是仍未改变的平民立场写照,也不难从中体会出底层生命自由、顽韧的精神意味。再有“女同学”这三个和美丽、清纯、幻想连在一起的字眼,按说应充满诗意,让人浮想联翩,可于坚的《女同学》却把它可能蛰伏的预想粉碎了。“女同学”面容模糊,“是有雀斑的女孩还是豁牙的女孩?”已忘却,甚至名字是“刘玉英李萍胡娜娜李桂珍?”也记不清,留在诗人记忆中的仅有空空的操场。全诗复现的是女同学朗诵、微笑、说话、与自己同桌、碰手,自己对女同学“偷看”、“春情萌动”、想入非非以及男女同学间相互吸引等一些细节、场景、事相的碎片,一些毫无浪漫色彩的平常经历和感受,“生活流”的无序淌动,使小人物平庸而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状态纤毫毕现。于坚新世纪的诗题旨、意趣纷然,或像《唐僧》一样重观唐代和尚金光闪烁影像背后“背着棉布包袱”的“行者”风貌,或如《纯棉的母亲》一样在政治和性别冲突的背景上赞美本色、淳朴的母亲,或似《便条二五八》一样以巧妙的构思洞悉生命存在的本质,但诗人走低的平民立场、为事物去蔽的目标却一以贯之,这也是不少读者一直视于坚为民间诗人领袖的根由所在。
因为于坚把写诗目的定位于事物的澄明,而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彼此间没高低贵贱之分,也无对错良恶之别;所以在他眼中“一切皆诗”,不但都应给予观照,并且该一视同仁。于是,我们发现不论写宏大、庄重题材的《赞美劳动》、《登秦始皇陵》、《读康熙信中写到的黄河》、《哀滇池》,还是写卑微、平凡事物的《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三个房间》、《披肩》、《美丽的女人住在我家楼上……》,都由于有澄明事物、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走“低”立场压着阵脚,能做到拒绝升华,随性自然。如面对许多人心中博大、庄严的故宫,于坚没有顶礼膜拜,而是平和地写到:“皇帝的卧室已经没有皇帝门户大开任闲人参观/大家面对的不是朕而是他睡觉的枕头被窝/许多人仍然觉得双膝在发软忍不住要下跪”(《参观故宫》)。诗貌似在再现故宫场景的一角和带有历史文化色彩的皇权意识;实则表现历史与文化并非它的本意,淡化历史的平视视角,夹叙夹议的反讽笔调,注定其深层意图就是对曾经的皇帝、奴性的观赏者作为普通人个体生命意识和价值的一种关注。而对人们不屑一顾、少文化想象的物件啤酒瓶盖,于坚竟大动诗思,以《啤酒瓶盖》细腻地状绘它的面貌、作用和悲惨际遇,写它从桌上“跳开”即成“废品”,“世界就再也想不到它/词典上不再有关于它的词条不再有它的本义引义和转义”;而“我仅仅是弯下腰把这个白色的小尤物拾起来/它那坚硬的齿状的边缘划破了我的手指/使我感受到某种与刀子无关的锋利”。啤酒瓶盖划破手指意在提醒人们,生活中有些事物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不可或缺,啤酒瓶盖就保证了宴会的热烈和隆重,“意味着一个黄昏的好心情”,人们“不知道叫它什么才好”,又分明是在别致地指认诗歌对事物命名艰难的失语现象、语言的功能与局限,诗的观照对象虽小,包孕的内涵却十分深邃。应该说,于坚这种承继“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传统的探索,是有难度的写作,它在扩大诗的题材疆域、打开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启示:不是拥有宏大、庄重的题材即会气象高远,琐屑平庸的“小景物”、“小事象”中同样能够发掘出大哲学和独到的诗意,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更值得斟酌。
二.澄明存在的“看”的美学
于坚诗歌经常采用“我看见”的视角。按照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逻辑,这个中心视角的高频率出现,绝非随意而为,它的背后肯定隐匿着诗人深度的情绪特质、经验色彩和风格趣尚。的确,“我看见”的视角既是于坚还原存在过程中去蔽求真的具体策略与方法,也是诗人维系自身和世界关系、观察事物的基本途径,这一点似乎已成公开的秘密。问题是于坚为何青睐这种视角,这种视角和于坚诗歌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以为答案应从于坚的身体和精神个性中找寻。诗人曾拥有过幸福的童年,但五岁时由于生病注射链霉素过量落下弱听的毛病,初中毕业后工厂铆焊车间里震耳欲聋的声音更是“雪上加霜”,使他的听力愈发不健全,连蚊子、雨滴和落叶声都听不到了。而每个人的诸种感觉间往往总是靠互补来平衡,一般说来眼睛不好的人听力多比他人敏锐,失聪者则常会训练出过人的视觉能力。于坚的生理疾患和工种对眼睛的特殊需要,决定他“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想当然的,而是看见的”,或者说“把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看”;⑸这与他对着力表现的日常经验“在世界中,与过程、行为、体验、事象、细节、在场等有关”⑹的切身理解遇合,就使他的诗很少涉足未知、臆想的领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抒情诗歌的“非诗”因素,能够“看得见”的一些叙事性特征。
一是大量物象、事象等事态因子的介入,铸就了诗歌一定的叙事长度和宽度。于坚的诗虽不特别排斥朦胧诗成功凭借的意象,但意象相对疏淡,并且疏淡的意象也不是它表现的重心,能激起读者观赏兴趣的更多是一些状态体验中的细节、过程与情节。《那是我正骑车回家》、《春天纪事》、《一只蝴蝶在雨季死去》等就呈这种走向,“小杏在人群中/我找了你好多年/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小杏当那一天/你轻轻对我说/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唱只歌给你听听/我忽然低下头去/许多年过去了/你看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给小杏的诗》)。诗给人的仿佛是一截故事片段,虽有窗帘、星星、泪水等意象,只是读者阅读时会不自觉地跳过这些具体的“词意象”,而去关注它们同其他语汇组成的“句意象”以及诸多句意象连缀的整体事态过程、情境,在对女子小杏的娓娓叙说“对话”中,体悟诗人平实而诚挚的深情和秉性,捕捉诗人思念小杏、和小杏交往的动作(含心理动作)、细节、场景片段,领略阅读叙事性文学的快感。九十年代后的《第一课:“爱巢”》、《在牙科诊所》、《小丽的父亲》、《主任》等,特别是十几首“事件”系列诗歌更把这一倾向推向巅峰状态,它们或纵式流动,或横向铺排,地点、人物、情节、事件等叙事文学要素一应俱全。“从铺好的马路上走过来工人们推着工具车/大锤拖在地上走铲子和丁字镐晃动在头上……按照图纸工人们开始动手/挥动工具精确地测量像铺设一条康庄大道那么认真”(《事件·铺路》)。诗详尽地描写工人们铺路的场面与过程,从场景设置、细节刻划到人物动作安排、事件情节穿插,全有新写实小说味道,当然它只是通过截取的几个兼具时间长度和空间宽度、相对典型的片段、瞬间,有效地抵达了作者还原事象的企图,而没有呆板地恪守叙事性文学的严谨、完整原则,散点透视的笔法也使劳动情境的叙述焕发着鲜活的诗性气息。不难看出,为回到事物与存在现场,于坚诗歌向诗外文体的扩张带来了明显的叙事性,但没有以牺牲诗的品质为代价,它只是合理吸纳了小说、戏剧、散文的一些手段,其叙事基本上仍属于注意情绪、情趣渗透的诗性叙事;并且因之而扩大了诗歌的内涵容量,拓宽了诗歌适应生活的幅度。
二是为降低对所见事物澄明、还原的干预程度,诗人从不同方向进行“反诗”的冷态抒情。诗是主情的、抒情的已成常识,但艾略特对之却有异于传统的认识,他以为“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⑺在这一点上于坚和艾略特有相通之处,他的当代好诗应具备“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⑻观念,即与艾略特不谋而合。“非升华”性的写作性质,决定他很少以主观的介入、扩张重构外在时空秩序,走涵括朦胧诗在内的中国诗歌的“变形”路线,去俘获含蓄之美;而是针对朦胧诗花样百出的意象艺术,十分警觉地提出“反诗”或叫不变形诗主张,希望通过对诗歌抒情性和外在修辞倾向的弃绝,正本清源,“回到事物中去”,使诗最终回到诗自身。
一方面诗人“直接处理审美对象,以‘情感零度’状态正视世俗生活,没有事物关系打破后的再造,没有意象的主观变形”,⑼如《独白》、《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铁路附近的一堆油桶》、《鞋匠》等,将自我欲几乎降低到了没有的程度。“玻璃后面我光滑地看着这场雨/这场来自故国春天的阵雨/在公寓的空场上降落……公寓里的居民都呆在各自的单元里/看着停车场渐渐闪射出光芒/大家心情各异等待着这场雨完结”(《停车场上春雨》),诗人像冷静的记录者,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幅春雨到来时分停车场场景和居民等待春雨停歇的“冷风景”,“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写实,使诗摒弃了主观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不能再具体的凡俗细节,不能再客观的直接呈现,把世界以其没被艺术打扰过的本来样子准确清晰地呈现出来,可在具象性的事态的视觉恢复中,又淡淡地透露出一股孤独和焦灼情绪。再如“我只能说它长得比鸭子更肥些/如果烤一烤加些盐巴花椒味道或许不错可是天鹅啊我虽对你有些不恭的小心眼/但现在我记住了你你不再是纸上的名词”(《在丹麦遇见天鹅》),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等,再也找不到一点“变形”诗的痕迹,曾给人以无限幻想的“天使”般的天鹅,在诗人俏皮幽默的解构后显影,它就是它自己,一只比鸭子更肥些的动物。作者局外人似地超然旁观,感觉不到天鹅之美,“无话可说”,也无法“赞美”,诗人在此不过是记录了一次海外与天鹅遭遇的经历和瞬间情绪波动而已。另一方面以客观叙述做艺术言说的主体方式,辅以第三人称、对话与独白等戏剧手段,强化诗的非个人化效果,如《参观纪念堂》、《0档案》、《他总是在深夜一点十分的时候……》等都带着平民化、生活流取向势必产生的“叙述”烙印。“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在烟囱冒烟的时候/来上班……四十二岁/当了父亲//就在这一年/他死了/电炉把他的头/炸开了一大条口/真可怕//埋他的那天/他老婆没有来/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他们说他个头小/抬着不重/从前他修的表/比新的好”(《罗家生》)。通篇依靠叙述介入下层生存现实,讲述善良的罗家生庸常的人生和死亡的悲剧,塑造出罗家生的“典型性格”,他普通得卑微地活着,“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普通,精通电工技术,有自己的精神想往,箱子里的“领带”即是明证;然而一场意外却使他从人间消失,工友们不悲不喜地谈论着他,生活依然。诗以第三人称的“平视”角度,把一个善良人的悲剧诠释得异常淡泊、平静,舒缓的叙述调式切合了人生的本相,寄寓了似淡实浓的人性悲悯。再如“老儿子 在街头闲逛时常常被父亲喝住/‘弗兰茨 回家 天气潮湿!’……‘他是那么孤独,完全孤独一人。/而我们无事可做,坐在这里,/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黑咕隆咚的;/一个人,也没有盖被子’(女友 多拉•热阿蔓特)/他身上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他默默地亲切地微笑”(《弗兰茨·卡夫卡》)。这首诗的细节叙述更为突出,铺排叙述和罗列性描述结合,相对完整地交待了作家卡夫卡的生命历程和性格遭遇,使一个“苦难的圣灵”形象站立起来,卡夫卡的父亲、朋友、女友的对话、旁白等戏剧性的场景和细节,更从侧面丰富、丰满了主体形象,人间的烟火气息十足,戏剧文体特有的复调性、现场感得以自动强化。
对于坚诗歌的“看”的美学,很多人不以为然,并以“非诗”之名不断地诟病和挞伐,至今它也未获得普遍的认同。其实很多人误读了于坚。冷抒情不是不抒情,不是彻底的纯客观,它是诗人隐藏情感的一种表现技巧;叙事性也非诗的目的,它乃诗人为提高诗歌处理日常生活能力向其他文体的合理扩张,始终和诗性相伴生,像《飞行》、《纯棉的母亲》等就适当地以贴切的意象与情绪配合,不纯粹是“看”的结果。所以说于坚的“反诗”不但没有毁灭诗,反倒保证了存在和事物的还原,对抗、反拨了变形诗歌矫饰浮夸的弊端,为当代诗歌走向大气、为读者更加深入地认知世界提供了新的启迪。
三.语言:从意识自觉到行为拯救
于坚对当代诗歌的冲击和建树是从对语言的不信任开始的。受海德格尔的“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⑽思想影响,初登诗坛的于坚就具有极自觉的语言意识,虽然那时他的兴趣主要在对传统理论的破坏和文本探索上,对语言自身思考尚欠深入,但仍触及到了诗和语言的一些核心本质。他认为诗是“语言自身情不自禁发出的一连串动作”,是“语言的‘在场’,澄明”,⑾作为诗歌栖息形式的语言也是一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创造了诗歌,而不是诗歌创造了语言,优秀的诗应通过语言重新命名世界,让语言顺利地“出场”。从这一标准出发,他看出了朦胧诗语言的局限:有精致华美的含蓄优长,也有过于神秘典雅的贵族之气,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使语言和诗人的生命存在着一种派生关系。那么何种语言能与平民意识相应和,实现和诗人生命结构的同一化?他找到了口语化。因为“口语诗歌实际上就是向纸上的文化以外的‘异域’逃亡,就是对清代以来的那种山林文学、贵族文学的‘心如死灰’”,通过它能“重新回到那种具有创造性的、具有感觉的、具有生命力的语言的本身”,⑿口语的质感、自由、富于创造性,决定它是颠覆书面语的最佳武器。正基于此,于坚八十年代即勇开口语写作风气之先,在诗中广泛使用口语,“你们在/一个冬天读我的作品/大吃一惊/你们说除了你们/于坚就是敌人了……韩东说我们可以聊聊/我们就聊聊/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作品/谈三流的恋爱/至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嘿嘿冷笑(《有朋从远方来——赠丁当》)。诗的语言时而似内心低语,时而似娓娓交谈,轻松自然,平白如话,从语汇句式到口吻语气,和日常口语毫无二致,它们仿佛是从诗人的命泉中流出,是诗人情绪的直接外化,不拐弯抹角,不装腔作势,同朦胧诗的意象与象征语言判若霄壤;但它却直指人心,显示了当代青年特立独行、玩世不恭的叛逆情绪和与朋友惺惺相惜又互为敌手的心理隐秘,以及内心深处的敏感与脆弱。这种语言几乎取消了诗和读者的距离,沿着它即可走进诗人生命本身。
口语诗对诗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即会蹈入口水化的泥潭。于坚卓然不群的秘诀是推崇语感,强调在诗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读者被感动的正是语感”,⒀努力把语感提升为口语化诗歌的生命和美感来源来加以追求,建构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语感诗学。他有时甚至不再把语义传达当作品的终极目标,而迷恋于语感的回味和营构,提倡语感即诗,为淡化、弱化语义,还像对待无标题音乐一样,把不少未给出具体标题的文本编为《作品XX号》。在语感观念烛照下,很多诗的语言一从他唇舌之间吞吐而出,就自动俘获了生命的感觉状态和节奏,带着超常的语感诗性。如“远方的朋友/您的信我读了/你是什么长相我想了想/大不了就是长得像某某吧/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不免有些担心/我怕我们一见面就心怀鬼胎/斟词酌句/想占上风/我怕我们默然无语/该说的都已说过……”(《远方的朋友》)诗中没什么深邃的内涵,但它畅达的语言流却饱含魅力,它仿佛就是诗人生命力的起伏与呼吸、奔涌与外化,自然的节奏挪移中,敞开了一代青年的生存方式和心灵状态,接到朋友来信后诗人思绪中迅速闪跳的几种见面情境虚拟,都既滑稽可笑又合理可能,能让人不知不觉中走近诗人的生命根部。“人活着/不要老是呆在一间屋里/望着一扇窗户/面对一只水杯/不要老是挂着一把钥匙/从一道门进去又出来/在有生命的年代/人应当到处去走走干干……”(《作品67号》)随意、自然、琐屑又不无幽默的语言禀赋,从诗人的心灵喷发同时,就有了直接抵达事物的能量,促使携着“生命有无数形式、活法不止一种”人生哲学的平民形象跃然纸上。可见,于坚诗歌的语感常和日常平民生活接合,附在拒绝带歧义、复杂句式的简单短句中,不时配以词语或句式重复的饶舌,是流动的、整体的,朴素而轻松;诗人借助它实现了诗人、生存、语言三位一体的统一,使诗的指向愈趋清晰确定,易于接 受和把握。
随着写作的深入和理论的自觉,于坚发现:世界最初是一元的,万物的所指与能指同构,人说出一种事物名称的同时就说出了事物本身,可文明、文化特别是隐喻介入后,文化在人和事物之间的阻隔,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分离,则使诗和世界成了隐喻和被隐喻的关系,谁都很难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人说不出他的存在,他只能说出事物的象征、意义而说不出事物本身,语言由存在的居所变为意义的暴力场,诗歌也逐渐对存在严重失语。而要实现为世界去蔽、重新命名事物的目的,仅凭口语化、语感强调远远不够,因为口语本身也沉淀着一定的文化成分,要从本质层面完成“词语性创建”必另寻出路;于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于坚对诗歌语言的兴趣遽增,在一九九二年提出并践行极具冲击力的“拒绝隐喻”主张,企望回到语言的最初状态,以扼制诗坛意象、象征与隐喻泛滥之风,拯救病入膏肓的诗歌语言,从而掀起了一场诗学革命。接受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理论启迪的“拒绝隐喻”主张,是对中国诗中隐喻功能蜕化为陈词滥调现实的有力反拨和拒斥,其目的是再度激活隐喻、使诗重获命名的功能。在这方面,抛开言此意彼的意象、象征思维路线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堪称范本,它使乌鸦穿越厚厚的偏见屏障,回到名词乌鸦状态。《正午的玫瑰另一种结局》、《被暗示的玫瑰》等几首玫瑰诗也都对玫瑰重新命名,使玫瑰“进入‘玫瑰’”,“苍蝇出现在四月发生的地方/我要把‘玫瑰’和‘候鸟’这两个词奉献给它/它们同时成为四月的意象……它不是诗歌的四月不是花瓶的四月不是敌人的四月/它是大地的四月”(《关于玫瑰》);“作为园子的主人”,“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运走垃圾/铲除杂草石子拣尽把泥块弄松/然后我浇水依着锄头看云等着它来”(《正午的玫瑰》)。玫瑰不论在中西方,还是热烈的红色纯洁的白色,都喻指美好的爱情,可前诗中,正如苍蝇就是苍蝇、候鸟就是候鸟一样,玫瑰就是客观存在的植物玫瑰,它摆脱了各种文化知识和哲理的缠绕,身上没有诗人主观情志的渗入,更没施与任何象征的内涵,它和四月媾和也只是同自然的时令相遇而已,仍是纯粹植物学意义上的“花”,不带任何隐喻意向;后诗的玫瑰也和爱情没关系,玫瑰单纯的愿望就是进到园子里,不管它怎样丑陋,而诗人运垃圾、除草、拣石子、松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只是在尽园丁之责,诗使玫瑰这个词在它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切断、堵住了玫瑰可能引发的幻想之维,而对隐喻和想象的放逐,控制了主体意志对客体世界的扩张,客观至极。《赞美海鸥》、《上教堂》、《声音》、《狼狗》等解构性作品,也都体现了“从隐喻后退”的文化立场,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事物的真实面目。
当然,隐喻是诗性的,它与诗歌距离最近,也是所有民族、国家诗歌中必不可少的艺术支撑,若想从诗中完全剔除隐喻十分困难,于坚也不例外。休说他后来在文章中承认早期的《罗家生》尚是隐喻性作品,就连最能代表他九十年代成就的长诗《0档案》、《飞行》,也不乏象征与隐喻的光影浮动。《0档案》将档案的文体和语式栽植诗内,通过客观化的“冷漠”方式揭示语言对人类个体的暴力摧残、体制对人性的物化和扭曲,“8日记/x年x月x日晴心情不好苦闷/x年x月x日晴心情好坐了一个上午……某日冷/某日等待某某/某年某月某日新年某日某生某日节日”,仅刻写日常生活的第八节日记机械呆板、千篇一律的叙述记载,那形式本身先定的僵死冷漠氛围,就足以外化出档案乃一切活人视而不见的活地狱的真相。它充满口语的率性,也少象征痕迹;但其深层仍潜藏着隐喻思维,“‘0’是一个伟大的隐喻,它象征着围城;是原点,也是终点;没有方向,却向四周发散,处处是方向”,⒁诗中类型化、物化的“他”也可理解为当代中国人形象的缩影和代指。经典之作《飞行》,虽在朴素叙事背后增加了跳跃性,表面看去也有局外人的冷静,但也接受了整体象征技巧的援助,“飞行”是诗人在万米高空飞行的实指,更有形而上思想飞行的深意,琐屑、飘动的臆想同生命、时间命题的思考遇合,酿就了诗歌虚实相生的多层结构,而绾结形下描写和形上指向的就是贯通全篇的象征意识。这种整体象征也有联想再造空间,但所指与能指关系相对直接确实的限定性,则使读者的理解不会过于宽泛与随意。或许诗人意识到完全拒绝隐喻不可能,所以在提出“拒绝隐喻”两年后写下名为“从隐喻后退”的文章,将自己的主张修整得更为严密、辩证和科学了。从语感强调到拒绝隐喻的转移,是于坚对传统诗学更强悍的挑战,它为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重建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开辟了新路径,并因观察角度的复杂化而更富包孕力,进一步激发了语词的潜能和活力,形成了于坚近二十多年来以混杂的长句替代纯净利落的短句,“倾向于客观与对结构和节奏的理想把握”⒂的写作风格。但转移后的于坚诗歌材料、结构由简明趋于芜杂,过度压抑自我也弱化了诗的感动力,所以新世纪后不像以前那样受人关注了。
于坚诗歌的缺点非常明显。它对日常生活的贴近和倚重,在无意间让一些琐屑、庸俗的因子混入诗中,降低了诗的精神高度;事态少节制的铺排叠加,则使诗意自然地蹈入浅淡和表象,密度减弱;在写作中形式感是第一的理念支配下的技术操作也多有失误,口语化追求不时滑向口水化,“拒绝隐喻”成了诗人无法彻底实现和超越的命题;诗人某些诗学理论的偏激,也不无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嫌。但是,于坚乃新时期大诗人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他执着于当下、手边、在场的平民立场,赋予了诗宽阔的言说视野和一种下沉的力量,他回到生存现场和事物本身的叙事诗学在扼制诗坛玄秘浮夸风气同时,打开了诗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他的语言探索达成了诗人和语言的同构,在一定限度内祛除了文化对事物的遮蔽,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使他三十余年间始终坚守着自己独立的方向写作,每一步转型都指向着沉稳与大气,一边输送着文本经典,一边为诗坛提供着经验和启迪的质素,影响中无数的后来者,这就是于坚在当代诗坛的位置和他不可替代的价值。
注释:
——————————
⑴于坚:《答<他们>问》,原载《他们》第6期,《于坚诗学随笔》16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
⑵于坚:《答<他们>问》,原载《他们》第6期,《于坚诗学随笔》16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
⑶于坚:《棕皮手记》23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⑷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⑸参见于坚、谢有顺:《真正的写作都是后退的》,《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于坚、陶乃侃:《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底》,《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⑹张大为、于坚:《于坚访谈录》,《诗刊》2003年第6期,上半月刊。
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⑻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诗歌报》1988年7月4日。
⑼罗振亚:《后朦胧诗整体观》,《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⑽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45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⑾于坚:《从隐喻后退》,《作家》1997年第3期。
⑿于坚、谢有顺:《诗歌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南方文坛》2003年第5期。
⒀于坚、韩东:《现代诗歌二人谈》,《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
⒁王晓生:《于坚诗歌的“意义”》,《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3期。
⒂于坚:《答<他们>问》,原载《他们》第6期,《于坚诗学随笔》15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
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爱华网
爱华网